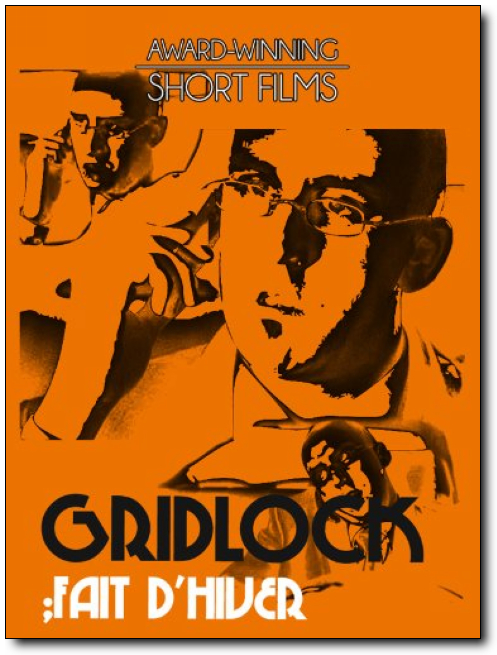2016-10-11 《交通阻塞》:我听到了金属世界的回应

电话是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但是当电话被接通,在电话两端的人是不是可以面对面,是不是会零距离?只是不论是送出的那句“喂”,还是听到的那一个“是我”,都把真实的声音变成了金属般的声音,它以一种变声的方式连接起了两个世界,而连接本身就是一个歧途,因为“喂”和“是我”都是没有任何所属的词语,它们是礼貌用语,是问候回答,可是,如果拨错了号码,搭错了线,所有的场景都可能走向一种错误。
男人拨通电话的时候,其实没有说出那个“喂”,因为他拨打的电话就指向自己的家里,接电话的人当然是熟悉的家人,妻子或者女儿,当那边的声音以一句“爸爸”回应的时候,通话便开始继续。男人进入到自己设想的家庭生活里,于是问女儿,妈妈在哪。而女儿也把对方当成了还没有回家的爸爸,于是告诉他,妈妈在楼上,和威姆叔叔在一起。本来即使妻子缺席在电话机旁,如果男人认识威姆叔叔,并且威姆叔叔是一个不带误会的朋友或亲人,那么男人就不会有任何异议,甚至电话在一些日常的问候之后可能结束。
|
| 导演: Dirk Beliën |
 |
这是真实发生的场景?女儿在电话里冷静地说着发生的一切,敲响房门、女人下楼,男人出门,甚至女人倒在地板上,都在女儿的视野里发生,而电话这头的男人是无法看见的,而到最后,女儿在电话中说,威姆叔叔已经走了,我想他死了,死在游泳池上。顺着女儿的目光望出去,窗外是一个积满雪的游泳池,池面上是一个人的印子,保留在那里,成为这个事件最后的结局。女人大约在浴室里滑到死去,男人大约掉在游泳池里死去,在女儿所在的世界里,两个人失去了生命,而女儿没有大喊大叫,她依然冷静地向电话那头的爸爸说起发生的一切。
|
|
| 《交通阻塞》电影海报 |
在隔着电话的冷静叙述中,一切都在真实地发生,可是,那不过是一种想象,甚至就是一次错误,男人最开始问的是“威姆叔叔是谁?”后来问的是“什么游泳池?”这是他问女儿的两个问题,却也是两种疑惑,所以在疑惑中,那个在他知道的家里,是不应该有威姆叔叔,当然也没有游泳池,那么,从这两个线索判断,男子打错了电话,电话那边不是自己家,接电话的人也不是自己的女儿。错误在何时发生的?男人在堵车的时候,打开了刚买的电话机,然后说了一句:“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好?”所以自始至终,男人对电话机也是存疑的,拨了电话,本来应该指向唯一的地址,抵达唯一的终点,但其实是向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刚好有一个和电话机旁一样的女儿,刚好好和自己一样没有回家的爸爸,刚好有在家里等待丈夫的妻子,所以在搭错了线的时候,一切都没有被怀疑,而女儿在接电话的时候,那个家里的电话机曾经从桌子上掉落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隐喻,不管是女儿,还是男人,都在一种错误的场景中制造了一个死亡事件。
悲剧仿佛是意外,仿佛是巧合,但是悲剧却像真实发生一样,而实际上,用电话沟通,用电话交流,本身就隐含着某种不确定性,这是金属产品,这是技术工具,它有时候并不是拉近彼此的距离,而是在人与人之间重建了一种隔阂状态,它是冷漠的,是变声的,也是虚幻的,她无法抵达真实的家,无法实现零距离的交流和沟通。那端的“爸爸”问候,这端”妈妈在哪里“的问话,其实都是一种泛化的交流方式,而在整个对话中,只有”威姆叔叔“是一个特称,是具体的名字,不管是爸爸、妈妈和女儿,都不具有特制性,也就取消了唯一性。所以这个偶然和错误意义上发生的故事,更像是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伦理悲剧。
唯一指向的电话,在错误中反而揭示了真相,反而具有了普遍意义。男人是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拿起电话,当时他被堵在一条无法前进的路上,这是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且,这个男人总是打开瓶子服下药片,总是敲打方向盘不停地骂人,他是焦虑的,是不安的,甚至是神经质的,所以他才会怀疑电话会不会有问题,才会在女孩说妈妈和威姆叔叔在楼上的时候,大叫“他妈的”,才会教女孩上楼帮自己做一件事,而这件事无非是另一个谎言:”我听到爸爸的车声,爸爸回来了。”而电话那头的女孩,其实也一样,在爸爸没有回来、妈妈上楼的夜晚,只能抱着洋娃娃,只能听楼上的呻吟;而威姆叔叔和那个女人,关着房门行苟且之事,也是因为缺少一份真正的爱,所以在听到男人回来之后,会慌忙跑进浴室,会匆忙离开,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男人的焦躁,小女孩的孤独,以及威姆叔叔和女人的背叛,是无数个家庭可能遇到的悲剧,只不过当可能的悲剧真实地发生之时,当他人的错误糅合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悲剧便不再是偶然,不再是随机,不再是巧合。
这边和那边,是真实和想象,是巧合和错误,最终一定是隔阂,道路被封闭被堵塞,家庭是空虚和孤独,感情是背叛和逃离,而被隔阂的世界除了无法消除的冷漠,除了意外造成的死亡,便是永远没有温情的金属回应:“喂,你好,是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071]
思前: 《我就不》:用理智战胜恐惧的手
顾后: 《默剧女子》:自我也是一个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