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0 《阿甘正传》:一根羽毛的启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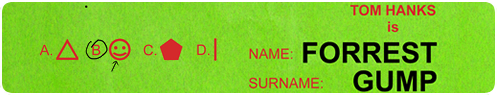
一根羽毛,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羽毛,是抓在手心、夹进书页里的羽毛,是随风而动、自由飞翔的羽毛,它洁白,它灵动,它独立,在风中飘飞就是珍妮曾经的梦想:要做一只会飞的鸟,在高处自由飞扬,但是它却以落在脚边的方式回归,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自由破灭于脚下坚实的土地,而当一切回归之后,它又从阿甘的脚边飞起,它以俯视的方式看见坐在那里的阿甘,看见这个城市,看见这个世界。飘飞而俯视,一根羽毛似乎已经变成了上帝,而阿甘也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两种命运,三种形态,一个羽毛绘制的运动轨迹就是人生所走过的路线,就如曾经阿甘站在珍妮的墓前。对成为逝者却依然在心里的爱人说:“我不知道是妈妈对,还是丹中尉对,我不知道,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有,注定的命运,还是我们的生命中只有偶然,像在风中飘。但我想:也许两者都有吧,也许两者都在同时发生着。”
命运的降临对于阿甘来说,就像是那根起先在空中飞翔却遥不可及的羽毛,一个智商只有75的弱智孩子,一个爸爸永远在“度假”的孩子,一个用脚撑才能将像问号一样的身体拉直的孩子,无论如何对于阿甘来说,都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缺憾,这种缺憾构成了他命运的残缺性。智商只有75,意味着他无法进入要求智商必须80以上的绿荫县中心学校,意味着他在人生的起跑线上失去了第一次机会;爸爸在度假,意味着他人生中“父亲”之一角色时缺席的,意味着父爱是不存在的;用脚撑来拉直身体,对于他来说,不仅是智力问题,甚至身体也存在着某种残缺,也正是由于此,别人叫他傻瓜,校车上的孩子几乎没有会把座位让给他,那些骑着自行车、开着疾驰的车子的孩子会把他当成是歧视和可以欺负的对象。
残缺性是阿甘命运的第一种属性,而这种残缺性并非是人生意义上真正的缺失,只不过在所谓的主体和主流文化中,阿甘无法成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被评价的规则之外的异类,就像中心学校的校长所说,之上80的人才能进入这所学校,否则只能进特殊学校。这种特殊性的命运安排当然是一种无法进入主流的歧视,但是残缺性而被歧视,却在另外一方面为阿甘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那就是自我性——主流文化拒绝阿甘,阿甘无法进入其中,意味着当那个世界打开的时候,阿甘同样可以拒绝那些所谓的主流文化,那些歧视他的人,那些智商在80的正常人,他们同样也无法进入阿甘精彩的世界。
|
| 导演: 罗伯特·泽米吉斯 |
 |
阿甘的自我意识来自于母亲,也正是这个伟大的母亲,成为阿甘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她生下了他,她照顾他,她鼓励他,她把阿甘看成是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人,所以在阿甘的嘴边,常常引用母亲对他说的话:“妈妈总是对我说,每天都会有奇迹。有些人并不同意,但这是真的。”“妈妈说过,要往前走,就得先忘掉过去。我想,这就是跑的用意。”“妈妈说过,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注定要做的一件事。”“妈妈说”构成了阿甘人生的一种态度,而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妈妈说,人生就像一颗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人生是一颗巧克力,有着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味道,一方面意味着命运的同等性,不管形态和味道如何不同,但都是相同的一颗巧克力;而另一方面,则是人生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偶然,正是这种未知和偶然,意味着可能的奇迹发生,当那根羽毛终于掉落在地上,终于降落于脚边,或者就是人生从真正自我出发看见了不一样的巧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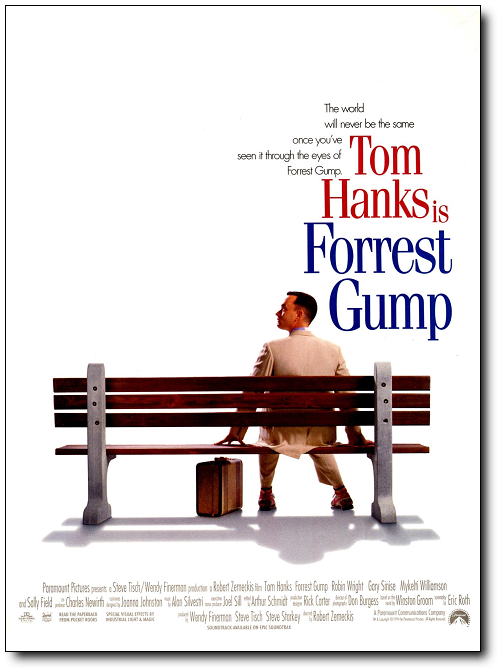 |
| 《阿甘正传》电影海报 |
所以对于阿甘来说,母亲的意义是一种亲情的存在,更是一种自我的存在,母亲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她实际上成为阿甘的“精神之父”,合二为一对于阿甘来说,是弥补了那种缺失的爱。而在母亲的启示下,他也终于以自己的方式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当那个脚撑卡在下水道里的时候,母亲和他用自己的努力化解了困难,这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对于别人规则消解的开始。脚撑是为了拉直那个像问号的身体,其实是为了一种迎合所谓的主流价值观,但是当那些骑着自行车的孩子们开始追着欺负阿甘的时候,他终于开始不顾脚撑的直立性,大脚迈开向前奔跑,脚撑散架了,对于奔跑向前的阿甘来说,意味着彻底抛弃了一种束缚。
背后是珍妮的声音:“福雷斯,跑!”从此,“福雷斯,跑!”这个声音一直萦绕在阿甘的耳边,它从“像一个天使”的珍妮口中喊出,从橄榄球比赛的拉拉队口中喊出,从越南战场上最好的朋友布巴嘴里喊出,跑步是阿甘第一次突破规则,也从此发现了自我,而在发现自我的过程中,他的残缺性一一被解构,在亲情、爱情、友情的世界里一直向前,从不后望。母亲的亲情之外,珍妮是第一个给了他自我意义的人,那辆校车上,当所有的孩子都鄙视他而不给他让座的时候,只有珍妮用甜蜜的声音让他坐在身边,和他一起聊天,从此形影不离,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爱情之路。他们一起爬树,一起读书,一起认字,一起倒挂着看夕阳,而小时候的珍妮“成为我唯一的朋友”正是一种爱的萌发,她给了他一个正常人的感受,也让他有了一个男人爱的权利。
尽管对于珍妮来说,理想是成为一个名人,是像一只鸟儿一样能够自由飞翔,阿甘对她的爱经受了离合的痛苦,但是似乎对于阿甘来说,这第一次的让座,第一次的甜蜜的声音,第一次“福雷斯,跑”的声音,都变成了永恒,当一起坐在树上看夕阳的时候,他说“她是我唯一的朋友”;当雨夜的性启蒙之后,他把她当成了肉体中的唯一女人;当他进入军校看见了色情杂志上珍妮的照片,在孟菲斯的酒吧演出中看见了全裸唱歌的珍妮被人调戏的时候,他依然不改初衷,对她说:“我爱你。”当他从越南战场上回来,参加反对种族制度的时候,对珍妮说:“我想成为你的男友,你是我永远的女友。”当他成为亿万富翁却在一个人的夜晚孤独的时候,他总是想起珍妮,而当珍妮回来他问她的是:“你愿意嫁给我吗?”第一次的微笑永远留在心里,看夕阳的记忆一直保存在心里,拉巴特湾的捕虾船命名为“珍妮号”,珍妮对于阿甘来说,是一个永远的符号,渗透进生命中,成为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终于在那个雨天,珍妮走进了阿甘的房间,睡在了他的身边,也终于她为他生下了一个名叫“福雷斯”的孩子,终于身披婚纱成了他的妻子,当珍妮病逝之后,阿甘在大树下的墓前对她说,你不用害怕,我就在你身边,一直在你身边。
这是永远执手的爱情,不断的分离只是为了不断的重聚,不断的拒绝只是为了最后的相守,所以阿甘的爱情也和他的人生一样,残缺性的背后是走向自我,走向一个完整的自我世界,而这种自我性却也衬托了珍妮迷途中的残缺性,她是受伤的,她也是反叛的,要变成一只鸟的梦想,要成为名歌手的理想,对于珍妮来说,自由却变成了另一种束缚,她被学校开除,她的裸体登上了花花公子杂志,她全裸在酒吧里唱歌遭受客人的调戏,她四处漂泊结交不同的男友,在放纵的生活里吸毒酗酒性交,她痛苦地爬上阳台想要以坠落的方式结束生命……
她或者也爱着阿甘,但是似乎远方有着更吸引人的理想,在出走中她却迷失了自我,这就是一种青春的残缺,所以当她重新回来的时候,当她看见一直等待她的阿甘的时候,阿甘反而成为他人生最后的终点,回归自我的终点,当在病床上的珍妮问阿甘在越南打仗害不害怕,阿甘想说有时候害怕,但是他却对珍妮说,“我看到在越南有时候雨停得久了,夜里有星星出来,天空一闪一闪的很好看;我看到太阳下山前的海湾,水面上有千万片闪光;我看到那山中之湖,水好清澈,就像有两片天,一片叠一片;然后在沙漠,日出的时候,我看到天之涯地之极,美极了……”
自然之美,也是自我之美,因为自我中有爱情,也因为自我中有友情。当阿甘成为一名士兵的时候,他坐上那辆车上,几乎和珍妮让座的情况一样,那个名叫布巴的黑人给了他一种尊严,这个喜欢捕虾立志要成为捕虾船船长的布巴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训练一起上战场,一起背靠着背在夕阳下休息。当突然之间的袭击发生之后,阿甘听到的也是“福雷斯,跑”的声音,但是第一个跑出丛林的阿甘终于再一次返回现场,去寻找已经受伤的布巴,每次进去总是背出一个受伤的队友,当最后在空袭中背出布巴的时候,布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回家。”最喜欢捕虾的布巴死在了永不能回来的越南河边,所以只是在屁股上受伤的阿甘在回国之后,找到了布巴的家人,出钱买了一艘捕虾船,这种看起来傻乎乎的行为在阿甘那里却是崇高的,因为她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不能让死去的布巴留下遗憾。
而这种对友情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对丹中尉的态度上,这个世代有着上战场杀敌光荣传统的中尉,在越南战场上失去了双脚,他本来的理想是战死,在他看来这是作为一个军人的莫大荣誉,当阿甘冒着生命危险将他背出危险地带时,他的理想破灭了,于是在医院里他愤怒,回国之后更是开始沉沦,他嘲笑命运,嘲笑上帝,“我看见了耶稣了吗?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这一切全是狗屁!”坐在轮椅上,失去了双腿,没有像阿甘那样的荣誉勋章,对于丹来说,的确是一种命运的羞辱。而这也成为他在理想破灭之后的残缺人生。但是阿甘却以自我存在的方式启示他,他为了承诺买了捕虾船,虽然每次只能捕到五只虾,但是却依然没有放弃,终于丹成了捕虾船的大幅,终于在一个和暴风雨抗争的夜晚之后收获了大量的虾——他和阿甘一起收获了成功,从此他们开办的“布巴·甘捕虾公司”不断壮大,而阿甘和他也成为了百万富翁。在那个平静的湖面上,丹在说了一声“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之后,跳入水中自由游弋,享受着人生的惬意,“他和上帝和解了。”而在阿甘的婚礼上,丹带着自己的未婚妻来参加,而他在战场上失去的双腿也变成了铝合金的支架,像阿甘小时候的脚撑,成为一双“魔鞋”,而这样的重塑也意味着丹在阿甘的友情中重新开启人生之路。
不管是珍妮还是丹中尉,在阿甘收获的爱情和友情中,他看见了自我,也让他们看见了自我,而这种自我就是对于残缺性的弥补,甚至高于一切的所谓理想,也就是说,当这一切以真实可触的方式成为人生注解的时候,阿甘其实已经握住了那一片本来高高在上的羽毛。而只有拥有这种自我性,才能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高度,那就是让羽毛再次飘飞的超越性。阿甘是一个弱智者,是一个世人所称的傻子,但是在他诚实、守信、勇敢的态度里,在他善良、温馨和真实的感情里,他却成为天才,成为英雄,成为传奇。
因为无所顾及地跑,他跑进了橄榄球场,跑进了自己的大学,他成为橄榄球主力,并成为全明星队员;他由于超凡的专注力,进入军校之后打破了装枪的记录,被教官认为是智商达到160以上的天才;在越南战场,它无与伦比的速度使得他能冒险救出受伤的队员,只在屁股上受伤的他成为越战英雄;在受伤期间因为“目光不离开球”,使得他学会了乒乓球并且成为乒乓球代表来到中国开展乒乓球外交;因为他的执着和运气,他的“珍妮号”捕虾船在拉巴特湾捕获了大量的虾,他成了百万富翁,在丹中尉的打理下又成为了亿万富翁;因为他无可匹敌的跑步速度,使得他在穿越了美国之后,成为全国名人,大量的拥趸使得他成为一个传奇。
橄榄球巨星、越战英雄、乒乓球外交使者、亿万富翁、跑步健将,这一些名誉使得他成为传奇人物,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接见,成就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但是这种辉煌只不过是他自我性的一种升华,也就是说,对于他来说,所谓的传奇只是在接近一个真实的自己,就像他在跑步时,电视采访他闻道:“先生,你为什么要跑?你是为了世界和平吗?你是为了无家可归者吗?你是为了妇女权利吗?为了保护环境吗?”为了世界和平、为了流浪者、为了女权运动,为了保护环境,这些都是被赋予的意义,而其实,在阿甘看来,跑步就是跑步,它是一种真实自我的反应:“他们就是不相信,有些人跑步,什么都不为,我只是想跑。我只是想跑。”
他们和我之间建立的就是这种不相同的价值观,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阿甘被认为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他却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回归自我。当他成为全美明星队的时候,受到了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接见,当肯尼迪问队员们“感觉如何”的时候,阿甘却在握手时说:“我想尿尿!”当以越战英雄的身份被当时的总统约翰逊接见的时候,总统问他伤口在哪里?在电视镜头前阿甘脱下了裤子露出了屁股;当阿甘成为乒乓外交的代表人物受到尼克松接见的时候,尼克松问他你住在什么酒店,阿甘告诉他的却是酒店的设施坏了。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乒乓外交代表,都是一种国家形象,而且接见的是美国最高领导,而且是在全国观众看见的电视上,但是对于阿甘来说,所谓的荣誉,所谓的名声,都是不真实的,也不是自己追求的,他只是偶尔成为英雄,“我要尿尿”、脱下裤子,以及告知酒店的问题,对他来说,才是最真实的。
阿甘永远回归着自己的本性,而这种本性也解构着所谓的主流文化,颠覆着传统观念,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以及电视里新闻中的福特、里根,越战、黑人运动、女权主义、猫王、列侬,等事件和人物,构筑了一种历史,而用阿甘串联起美国的这一段历史,似乎是一种戏谑,也像是在个体命运中反衬国家命运,刺杀、丑闻的背后,是阿甘真实自我的展现,这样一种对比,就是为了揭示一种反英雄的英雄情结:也就是说,阿甘的弱者、愚笨、一根筋以及偶然命运,都在解构英雄,但是他却成为另一种英雄,就如母亲给他取得名字,就是以3K党的英雄命名,但是在阿甘那里,却以解构的方式成就了一个个传奇,成为那一根最终可以俯瞰城市和世界的羽毛。
残缺性不是一种人生的失败,在自我性构筑的人生里,在亲情、爱情和友情的巨大力量下,他以超越的方式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虽然是一种理想主义,是美国精神的重建需要,但是在阿甘身上,无论最后如何超越现实,超越命运,人生最后还是一种回归,回到母亲身边,回到爱人身边,回到朋友身边,回到自己那个永远的家,回到那个永远叫“福雷斯”的孩子身边,正如他在华盛顿反战集会上的讲话被破坏者拔掉了麦克风的插头,那底下的观众无法听见的声音,其实在影片的隐秘处,其实是这样的:“Sometimes when people go to Vietnam, they go home to their mommas without any legs. Sometimes they don't go home at all. That's a bad thing. That's all I have to say about that.”
如上帝的启示,迷失的人,喧闹的人,为了名誉的人,想做英雄的人,其实是无法听见的,而上帝的其实就如最后的羽毛,从脚底下飞起,从大地之上飞起,变成一种在高处的启示录,无论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还是可以改变的奇迹,无论是必然还是偶然,都是人生,都在发生,“但我想:也许两者都有吧,也许两者都在同时发生着。”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7302]
顾后: 《七夜》:一切近的东西都将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