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22 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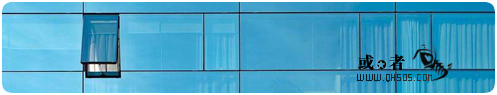
我们居于一个世界,
但为了更加舒适,
使用玻璃墙
将它分成了两个。
——马林·索雷斯库《玻璃墙》
回来了,昨天。当初离开是个及物动词,现在回来依然是个及物动词,而在离开与回来,过去与昨天,甚至昨天和今天之间,在及物动词的不同指向上,永远隔着一块透明却穿越不过去的“玻璃墙”。
那时的雨是淅淅沥沥地下着,坐上G1870高铁上的时候,雨仿佛只下在了身后,即使密集,即使狂暴,即使绵长,也都在我看不见的身后。像是遗忘了正在发生的故事,当到达终点的时候,雨完全变成了一种想象,即使它出现在我手机的天气主页上,似乎也与我无关了。置身在开封的夜里,即使有沉沉的云压着,也是和离开的城市不一样了,看见却看不见,一块玻璃墙就隔开了两个城市,两种状态,两段天气。
而在此后的几天,这种被隔开的现实又加速了某种巧合,18日,开封小雨转大雨,19日,开封大雨转阵雨,手机天气总是以预报的方式告诉你两个小时后雨会停,但是被预知的时间永远不是现在,永远不是此时此刻,它还在下雨,它就在下雨,无休无止,无始无终,虽然有过短暂的停歇,但是整个城市完全被淋湿了,无论是在高峰论坛的会议室里,还是外出考察的行程中,无论是在白天的端坐中,还是在夜晚的入睡里,雨声不绝,甚至完全进入了湿漉漉的梦境中。
可是,此时此刻的雨,在隔着玻璃墙的另一个城市,却是一片蓝天,18日,临安多云转阴,19日,临安阴转多云——依然是手机天气上获取的信息,却不再是两个小时后的预报,它就是不变的此时此刻。而在此时此刻的现在,隔着两个不同世界的玻璃墙,我从来不在场。于是,就在这晴晴雨雨、雨雨晴晴的分隔中,世界在同一时间的此时此刻说着各自的故事,而我仿佛在相异的空间,南北的城市里,完全抽离成了一个符号——哪里是真实的?哪里是想象的?哪里的我更牵挂在场的时间?
甚至当用及物动词的回来,慢慢构筑现在,却仍然有一种虚幻的感觉,是不是天变了,是不是城换了,是不是人走了?“在这里,时间是盲目的。”还是想到了这句话,这一次的引用如果只是放在“昨天”这个发生了空间转换的时间维度,我或者可以安然地抽身而出,因为在晴和雨,南与北的相异中,那只不过是暂时演绎的一个梦,而我必须面向的是拆离了玻璃墙的“一个世界”,一条路,一所房子,一爿天空,一个今天,都是触手可摸的,都是可见可闻的。
因为这就是现在,把昨天搁置在那里的现在,把过去遗忘的现在,用及物动词回来的现在,“那什么时候才是现在呢?一个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时间的现在,将会颠覆时间,不会维持时间,只会解构时间,尤其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文本之外来自严格杜撰的故事中的‘现在’,求助于那些能使之重新取决于可实现的最后。”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延续的终点,它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晴是现在的晴,雨是现在的雨,即使作为预告的形式,它也不再是一个分叉到玻璃墙之外的时间,就像有人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先知只有一个回答:“今天。”
此刻就是今天,此刻便是此刻,且永远是此刻,“没有什么可以等待,即便等待是一个义务。”所以回来不是为了等待而回来,今天不是为了等待而走向今天,在时间的维度里,只留下现在,只留下此刻,昨天和过去看起来是一个托辞,其实毫无意义。于是,颠覆和解构就是玻璃墙的拆除和毁灭,它在那里发生了,即使无人经过,也一定是按照自己的秩序轰然倒地,然后在“可实现的最后”,用自己的方式使世界变成一个整体。
而其实,作为相异时间的症结,只是因为我们命名了可能的现在,在回忆中我们把过去当成现在,在展望中我们把未来当成了此刻,向后看或者向后看,唯一没有真实地把自己放在不变的在场里。命名是一种写作,是一种说话,舌头在柔软地舞蹈,它制造了可变的声音,或轻或重,或粗或细,或真或假,或叙述或抒情,但是那些书写和话语,早就已经违背了规则,即使它不可更改,也不在时间“可实现的最后”里成为真理——所谓背叛,就是用一块玻璃墙的命名,隔开了两个世界,透明着,却永远不能穿越。
回来就好,那一座大宋的城池已经在背面晴晴雨雨,一切都和我无关,我只在此刻:此刻出门买点早饭,此刻打开小说阅读,此刻躺在沙发午睡,此刻听到外面隆隆挖掘的声音,此刻看见云朵又少了一些,“他曾经写作,无论这是否有可能,但是他不说话。”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980]
思前: 汴梁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