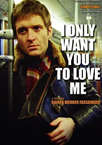2020-07-24《我只希望你们爱我》:像鲜花一样的暴力

他喝了啤酒,然后喝了白兰地,一种酒比另一种酒更烈;他听房东说起一个富有的犹太人,说起“钱生钱”的规则,他听到房东骂进来的儿子不工作是个“寄生虫”,一种生存比另一种生存更冷酷;终于,他拿起了本来要给父亲打电话的电话机,狠狠砸向了鄙视儿子的房东,没有挣扎就这样死了,一种谋杀比另一种谋杀更暴力——他本来无数次构想的场景是砸死自己的父亲,当作为他人的房东成为了他暴力的牺牲品,他不是在面对无爱的家庭,而是指向了没有爱的社会。
当被宣判10年有期徒刑,当面对采访他的女记者,彼得说了一句:“我想给父亲打电话。”但是他没有打电话,他随后说的一句话是:“那不是我,那就是我。”一个既肯定自我又否定自我的忏悔似乎就指向了把房东作为假象的父亲而谋杀的缘由:杀死了房东,自己不是以房东的儿子名义杀死他,房东何辜?所以这不是自己应该犯下的罪,但是那却是自己必然要做的事,代替房东的儿子,代替每一个没有爱的家庭,甚至代替无权无钱的儿子向父权发起的反抗。但是,“那不是我,那就是我”在另一个意义上却是对自我的怀疑,夹在自我和非我之间,彼得肯定模糊了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还是一个施害者的身份界限。
把房东当成自己的父亲,用电话机狠狠砸向他,这是彼得无数次在想象中完成的暴力场面,当他的暴力目标指向父亲,就是对这个没有爱的家的一次反抗。父母到底给他造成了怎样的伤害,使得彼得要萌生杀人的想法?从一开始彼得从床上醒来,站到窗口是那些吊着的手指牌,似乎就证明他的生活中缺少人文的关怀:他一个人喝汤,一个人粉刷墙,甚至一个人造好了房子,当父母进来,参观了这幢正在建造的房子,然后给了彼得一些钱——仿佛彼得就是一个被雇佣的建筑工人,在邻居议论他为父母造房子很有爱心的时候,母亲却对着满身沾着建筑水泥的彼得说:“你不该把工地的灰带进来。”而当房子造好之后,父母告诉他的是,他可以先住在客厅,然后自己出去找公寓,或者去找其他工作,言下之意,这个房子从来不属于他——字幕打出来:“房子造完之后,父母似乎忘了造房者是彼得。”
自己花费了精力,房子却没有自己的份,父母还嫌弃他将灰尘带进来,还要让他自己出去找工作找公寓,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体现了无爱的现实,彼得自言自语地说:“我觉得我母亲并不爱我,或者只爱一点点。”爱在这里被异化了,彼得认为自己付出了全部,但是得不到父母的赞赏,甚至把她当成是外人,这从小时候彼得被父母毒打可以看出这种原生家庭的异化:小时候的彼得站在客厅里,畏缩着,手上拿着一束花,但是脸上却有某种笑容,邻居埃梅里希夫人告诉父母的是,他偷了花园里的花,于是在邻居走后,父亲没有说什么,但是母亲抄起一个晾衣架,让彼得爬在凳子上,然后狠狠地打在他的屁股上。
这是彼得关于爱之异化的启蒙教育:他为了证明自己对父母的爱,从邻居的花园里偷来了花,一种盗窃的行为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宽容,反而演变成了对他教育的暴力——一束花,是爱的符号,还是不爱的象征?这也许是从此以后萦绕在彼得心中永远难解的谜:一方面,他从此被父母认为是没用的人,即使长大之后为他们造了房子也被赶出了家,另一方面,这种教育是不是必然对彼得造成了伤害,或者说,这是不是彼得只是自己对于爱的偏狭理解?看起来,在彼得和父母之间,的确表现得很冷漠,这是一个并不缺钱的家庭,彼得只要张口向父母要钱,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他索要钱财,父母总是很机械地掏出钱来,像是一种施舍,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彼得内心的自卑感,他会认为自己没有用,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工作,所以他为了要证明自己,主动离开了父母,去往法兰克福的建筑工地谋生。
| 导演: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
彼得的倔强其实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自卑,内心的自卑又让他滋生出某种力量反抗父母,但是这又向着彼此冷漠的道路上行进,一次他和妻子艾瑞卡回来,在迫于生计的情况下,艾瑞卡想让他像父亲提出借钱的想法,但是在晚餐上,母亲和父亲发生了争吵,母亲骂他在外面招妓,彼得无法像父亲开口,他对艾瑞卡说:“我要羞愧而死了。”父亲的不检点生活让彼得蒙羞,但是艾瑞卡却又让他无论如何开口借钱,在第二天父亲主动给他钱的时候,彼得也没有犹豫和拒绝,这一种转变似乎在证明,彼得拿到的钱只不过是被看不起的父亲在道德之外的某种补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站在了道德的高度,只是手拿钱的举动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一种卑微。
所以,彼得对于无爱的家庭的态度让他走上了一条让爱异化的道路,离开父母外出谋生,彼得是要证明自己,但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面对家庭日益加重的开支,他陷于困境,但是他把这种从困境里挣脱出来而拼命赚钱的方式命名为爱的付出,在远远大于自身承受能力的爱面前,他反而将自己异化为一种牺牲品。女人艾瑞卡让他在家庭之外得到了爱,“你像我养的一只狗。”在结婚之前,艾瑞卡曾经这样形容彼得,但是这句话并无贬低,因为这条名叫“格里芬”的狗是艾瑞卡最喜欢的一条狗,但是,对于彼得来说,这种爱却慢慢变成了一种影子般的存在,彼得拿着鲜花说“嫁给我吧”,艾瑞卡欣然同意,从此他开始了为艾瑞卡的爱奉献自己所有的努力,但是很明显,他想用爱来驱逐无爱的现实,注定让这份爱承担了太多,而已让爱变异为一种自我的牺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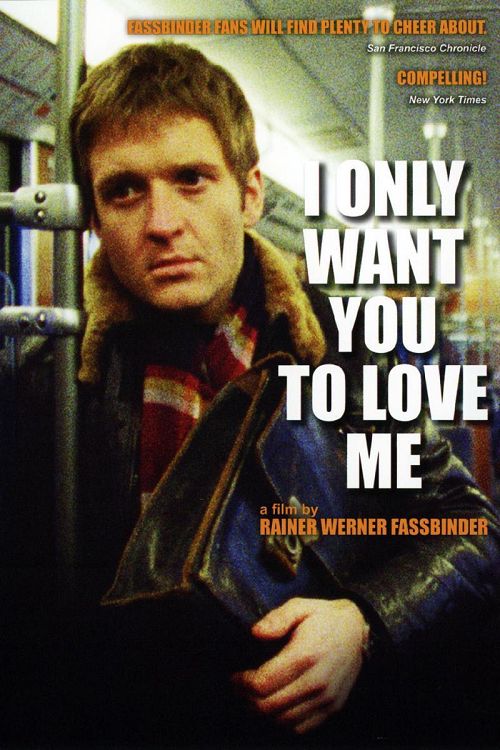
《我只希望你们爱我》电影海报
他在法兰克福的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从此以为可以独立自主,以为可以让艾瑞卡享受自己的爱,但那只不过对于父母鄙视的一种报复,只不过对于爱的一种消费式理解:艾瑞卡随后也来到了法兰克福,为了让艾瑞卡有家的感觉,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来了成套的家具,分24期付款无疑变成了沉重的负担;工地里刚给他加了工资,他便拉着艾瑞卡去商店买外套,艾瑞卡觉得178马克的衣服有点亏贵,但是彼得还是坚持着付了钱;看到老妇人手里的黄金项链,彼得又想给艾瑞卡买,但是即使按照工资分期也不够,他甚至动了歪脑筋,最后艾瑞卡发现了,让他还掉了600马克的钱;艾瑞卡的生日,他又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给她买了缝纫机,送给她一份生日惊喜……即使这些物品并非是生活必需品,即使艾瑞卡希望节省着用,但是在彼得看来,这不是单纯的钱,而是爱的证明,“我想让你开心,别人有的,你也要有。”
彼得无疑沦落在自己构筑的消费主义陷阱里,用购物的方式证明自己对艾瑞卡的爱,不是爱的无私表现,而是想让爱摆脱自己无爱的过往,所以彼得越陷越深,他无休无止地加班,“他会过劳死的。”工头曾经这样说,并且允许他度假,但是彼得只休息了几天就又返回了工地,而艾瑞卡希望向父亲借钱缓解压力,彼得说:“我宁愿接私活也不要他的钱。”或者,“我宁愿倒下也不愿借钱。”于是为了在艾瑞卡面前证明自己可以赚来更多的钱,他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工作,工作,工作”中疲于奔命。甚至后来他其实失去了那份工作,但是他还是白天出门晚上回来,告诉艾瑞卡自己加了工资,其实这一天他只是空坐在地铁上,游走在街道上,甚至他跑去向艾瑞卡的奶奶借了100马克,然后回来扔在桌子上告诉艾瑞卡自己发了工资——彼得就是在这样自我虚构的生活中,在爱与被爱的谎言里。
而鲜花成为彼得爱的符号,无论是他出现在母亲的面前,还是去看望艾瑞卡的奶奶,或者是在艾瑞卡的爱面前,他总是手捧一束鲜花,不仅证明着他对他们的爱,也传递着自己希望他们爱的渴望,但是正如小时候的暴力一样,鲜花其实早就被异化了,它是道德败坏的证明,是消费主义的自我欺骗,是暴力的折射,直到彼得走投无路,他还是在自欺欺人中让爱继续——即使自己再也无法承受,他买了一把枪,在一个人的房间里拿出枪,对准镜子里的自己,他也许能杀死的只有那个镜像里的自己,但是他没有开枪,在必须维持的爱的世界里,他连自己杀死自己的勇气也没有——而最后用电话机砸死房东,他也并非是向父母表达一种绝望,房东以及房东的儿子成为他的另一个虚构,他的报复,他的反抗,他对于无爱的愤怒,都在这被异化和虚构的世界里上演,连同自己,都成为了不在真实的存在,因为,“那不是我,那就是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