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4《变形记》:“我陷入困境”的三重视角

电影片名就是卡夫卡小说的原名;电影只有55分钟,属于短片,和小说的“短篇”相对应;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其中有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内心活动,电影也是在第三人称叙事中有格里高尔的独白;小说从格里高尔醒来变成甲虫开始,到他死后一家人乘坐电车开始新的生活,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也未做变动,“电车到站时,格蕾特首先起身伸伸懒腰,像是认同了父母最新萌生的美好憧憬,至少在她的父母眼中是这样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忠实”于原著的电影,甚至被称为“小说电影”,但是文字表达和影像表达天然的不同,尤其是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性和象征性只有文字的丰富语义才能表达,即使电影情节上始终没有从小说结构中“溢出”,但扬·涅梅茨的电影必然是一次重构,甚至是异构。
而且这是涅梅茨主动寻求突破的一次异构,这种异构就突出表现在影像视角的多变之上,而多重视角的呈现就基于故事最核心的一句话:“我陷入了困境。”当格里高尔睁开眼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他以为这只是一个梦,当确定周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时候,梦破碎了,他被推入到了令自己不解甚至害怕的困境之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变成了一只爬行的甲虫,再也不能出去工作,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和家人生活,再也无法获得“人”的地位。但是从人变成甲虫的灾难性降临并不只是形体上的变化,格里高尔更面临着家人对他的态度:他以前是家里的劳动力,当变成甲虫就再也无法赚钱。当打开门母亲见到他便晕倒过去,父亲极为不解,妹妹惊讶,这是人面对一个变异世界的本能反应,但是当生活依旧,曾经对他的照顾慢慢转变为一种冷漠,继而是嫌弃,父亲向他扔苹果皮,格里高尔甚至被苹果皮所伤,负责他饮食的妹妹也不再热情,甚至认为,“人和这样的动物怎么能生活在一起?”母亲也不再理睬他。随着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他独自关在房间里,而房间里也慢慢堆满了各种废物,最后格里高尔在孤独、痛苦、饥饿中死去。
而“我陷入困境”并不在于格里高尔没有死之前的恐惧,在他死后,家人搬离了公寓,在电车上开始畅想明天的生活,这不仅是对死去的格里高尔的抛弃,而且也把“非人”的异化变成一种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所以“我陷入了困境”在涅梅茨那里也绝不是格里高尔的个人感受,所以从这个核心主题出发,涅梅茨通过影像构筑了三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电影最大的亮点,它通过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主观视角呈现了他所看到的人类世界,低机位、摇晃的镜头构成了强烈的主观性,通过这一视角,一方面格里高尔看见了外面的世界,看见了家,也看见了家人,这当然是一个让他不适、陌生的世界,床是那么大,椅子是那么高,他可以爬到吊灯上,可以沿着墙壁越过自己的那张照片。而另一方面,格里高尔的视角是动物的视角,它在爬行,它在观察,它在呼吸,它在逃避,从床上下来,从桌子上去,或者爬到那本巨大的账本上,或者沿着吊灯在上面观察,或者在桌子底下躲避。
| 导演: 杨·涅梅茨 |
格里高尔的主观视角是摇晃的,是变形的,这种摇晃和变形的效果正是表达了他“我陷入了困境”的强烈恐惧。而且,他所看到的世界,世界也在看他,或者说,他所看到的正是他被看的世界,看与被看形成了第一视角的互动关系,但是这种互动带来不是新奇,而是另一种畸形:他面前的家人都变成陌生人,一开始他们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和他说话,之后则变成了不屑,最后是冷漠、嫌弃,甚至憎恶,他们对格里高尔的看构成了格里高尔的被看见,被看见又转变为看见,这也使得困境变成了一种双重叙事。除了家人,还有公司代理人对他的看,在看见格里高尔之后,他不断后退,最后逃离;还有疯癫似的女佣,她对格里高尔的看完全是对动物的看,她甚至叫他“蜣螂”;还有三位租客的看,当母亲准备了烤乳猪,他们大快朵颐,格里高尔就躲在暗处,“他们在我快要死去的时候却大快朵颐。”他们终于在满足了食欲之后看到了格里高尔,于是在惊异中提出不再支付租金,然后纷纷离开。格里高尔被看见,也通过他的视角看见家人和社会的畸形目光,正是这种看和被看的主观视角,呈现出影像本身具有的失重感、摇晃感和荒诞感。
这是涅梅茨异构的最大亮点,而除了格里高尔的主观视角之外,涅梅茨还使用了平稳叙事的客观视角,尤其是在格里高尔不在场的情况下,家人的生活就是通过这种客观视角得以表现。客观视角是平稳的正常视角,它也让叙事变得正常,但是涅梅茨通过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交替的方式形成了一种视角上的变化,从而表达出两种生活带来的张力。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甲虫的时候,是主观视角,而在讲述门外的家人敲门、开锁、疑惑时,采用的是客观视角,当不同的视角交替出现时,主观世界的不安、恐惧就更为明显。而在这两种视角之外,还有第三种视角,它在格里高尔死去之后出现,女佣把红色的尸体丢进了箱子,然后让他的家人和租客们看,之后又关上了箱子,而父亲决定将租客赶出公寓,同时解雇了女佣,在整个过程中,镜头一直是这种视角的体现:它是摇晃的,它是变形的,它跟拍着女佣处理尸体、租客开门下楼等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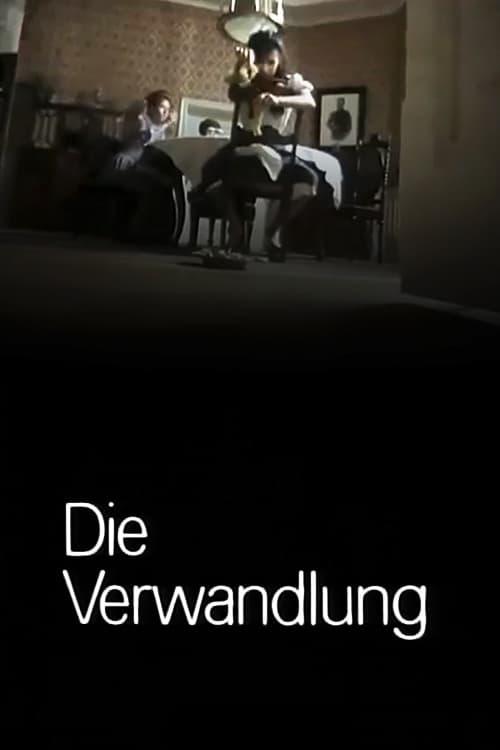
《变形记》电影海报
主观镜头表现了格里高尔的“非人”存在,客观镜头则表现了人本身的冷漠,涅梅茨为什么又要采用第三种视角?既不是非人的视角,也不是人的视角,却变成了既是非人的视角也是人的视角,这种叠加使得故事的荒诞性更为强烈:以为的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非人的存在,以为的正常生活其实就是异化的生活,以为的客观叙事从来不是客观的——当涅梅茨把卡夫卡的悲剧变成一幕充满荒诞感的喜剧,这不正是这种视角带来的变形、夸张效果?这部电影通过三重视角完成了对卡夫卡小说的“异构”,三重视角也构成了“困境”的三重叙事:这是格里高尔从人变成甲虫的困境,最后的死去是社会异化的悲剧;这也是卡夫卡生活的困境,他通过小说揭露了这个唯利是图、金钱膜拜、压抑的社会;这更是涅梅茨的困境,1966年他就提出了把卡夫卡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但是被捷克国家电影局否定了,1974年他被迫流亡德国,最终完成了这部电影,这也是“布拉格之春”后他流亡德国的第一部电影,在接受采访时,涅梅茨说自己是流亡而不是移民,
1974年,他们原打算把我关进监狱,却给我留了一条“活路”,跟米兰·昆德拉一样。他们告诉我们:只要以工作合同而非政治抗议为由申请合法离境,刑事起诉就可撤销。我接受了条件,合法离国,因此还持有捷克护照两年。但这并非旅行——我一旦回国,护照就会被没收,刑事程序会从头再来,我也就进了监狱。两年后,他们剥夺了我的国籍。所以我既未“移民”,也从未申请政治庇护。我成了“无国籍者”,没有国籍,也没有任何合法身份。
这难道不是另一个“变形记”?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