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9《春江水暖》:展开而断裂的人生画卷

最后一个长镜头:富春江面上,康康正在靠近江边的水里嬉戏;再往上,是正闲坐着看着江面的奶奶;再往上,是顾雪和江一站在树下谈着天;一层一层向上之后,再横移过去,镜头里是郁葱的树,是苍茫的江面,以及最后的星光点点。当字幕打出了“卷一完”,这种自下而上自左而右的镜头语言分明勾勒出一幅画卷,它在展示,它在延伸,既是对剧中人物生活还将继续的一种交代,也是对于顾晓刚计划中“千里江东图”三卷本电影的一种暗示。
镜头在延伸,故事在延伸,最后的长镜头徐徐展开,是一种结构上的风格呈现,就如顾晓刚所说,从形式上看,这部电影就像中国山水画,以卷轴的方式展开,当观众跟着画面里人物进入其中,这种游观有一种分镜头的感觉,“中国的绘画一直在营造一种宇宙观或叫宇宙感,就是要营造一种无限的时空,并借这种长卷的方式,不停地去调整空间上的统一性。”而不光是最后的长镜头,顾晓刚在这部“卷一”的山水画中,的确紧紧扣住剧情的空间化来处理人物故事,从下一代的康康、顾雪和江一,到上一代的奶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富春江勾连在一起,他们看见的是江景,他们被看见的是生活,而在长镜头展示的看见和被看见的结构里,这个发生在富豪村江畔三代人的故事就如画卷一般,呈现出丰富的人间烟火。
但是当画卷最后被展开,人物的命运其实经历了波折:奶奶已经去世,而且是孤独地去世,顾雪和江一虽然已经结婚,但是不管是爱情还是婚姻,他们都遇到了太多的世俗阻力,而康康则是唐氏综合征的患儿——当最后的三代人在富春江畔成为看见和被看见的存在,是不是这个结尾有意避开了什么?那就是中间至关重要的一代的缺失,他们是奶奶改嫁之后生下的四个儿子,他们也是顾雪、康康的父亲,当他们缺失在最后的长镜头里,这种抽离是不是顾晓刚故意为之?实际上,这一幅画卷中最重要也是体现人间烟火最充分的一代正是兄弟四人,当他们夹在下一代和上一代的中间,也成为这个时代经受着考验的一代,而当他们的影像最后从长镜头中抽离,似乎意味着某种断裂。
既要像书画长卷一样展开,又抽离了最重要的一部分,顾晓刚似乎人为在破坏这种同一性,又或者是在思考人生画卷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如果将下一代和上一代的故事设置为背景,那么四个兄弟的故事则是这幅长卷的真正主干,他们所呈现的生活正如一年四季交替的冷暖变化一样,统摄了喜悦与悲苦,积极与无奈。老大余有福开了一家饭店,顾雪是他们的女儿,虽然在生意场上背负了压力,但是生活总体上来说是富足的;老二和妻子阿英一直在船上打鱼,江上的颠簸让他们的生活颇为不易,但是随着老房子因为地铁建造拆迁,他们的生活似乎一下子有了奔头,儿子阳阳马上那个要结婚了,他们用手中的钱为阳阳购置了市区的一套好房子;老三余有金的生活则落魄了许多,命运似乎也将他带到了一个不堪的地步,前几年老婆离开了他,而儿子康康则患有唐氏综合征,有一次因为出现了后遗症送到重症监护室才捡回一条命,拖着病重的儿子,余有金混迹于赌场,因为欠下了一屁股赌债,他常常被人追债,因为无法还钱还被债主浸在水里;老四已经38岁了,但是还没有女朋友,单身一人的他成为老母亲和几个兄弟的牵挂。
四个兄弟,组成了人生的四季,不管是成家立业,还是单身光棍,对于他们来说,生活中都有不顺心的事,即使四个人在老母住院的间隙一起打篮球,即使在节假日聚在一起,但是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着烦恼,尤其是老三,因为家庭的不幸,也因为赌博欠债的缘故,得罪了许多人,甚至连老大和老二也骂他是“畜生”,而且老三不思悔改,不干正经事,总是希望在赌场上打翻身仗,甚至还学会了出老千。而老四因为长期找不到心仪的女人,婚姻之事搁置着,既然兄弟几个不放心,也让老母亲时常牵挂。相对来说,老二家的生活平和一些,他们因为拆迁得到了补偿款,儿子阳阳和女友微微的关系也没有多少波折,接下去就是为他们准备新房办理酒席。而老大虽然开了饭店,生意也兴隆,但是老三赌博的事和老四没成家的现实,让作为大哥的自己不安心,有一次老三的债主王威因为找不到老三,竟然要老大替他还钱,当老大拒绝的时候,他们甚至砸了他的店。
| 导演: 顾晓刚 |
四个人各自又各自的烦恼,但其实,这一代的存在,必然会牵扯到上一代和下一代:上一代的老母亲是在大家给她做七十大寿的时候突然倒下,本来想让寿宴冲冲喜,不想却患上了小中风,从此失去独立生活的她需要四个兄弟轮流照顾。这个责任首先落在了老大身上,老大也是义无反顾,媳妇凤娟虽然心有怨言,但还是尽心尽力。老太太得了小中风,四个兄弟应该轮流照顾,但其实出院之后这个任务基本上是老大和凤娟承担下来:老二因为家里被拆迁了,所以和老大商量暂时让老母住在大哥家里,“我可以出钱。”老三自己还要照顾生病的康康,而且长期混迹于赌场也没有时间处理母亲的生活问题,老四是单身一个,自己的生活问题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和母亲住在一起。所以当上一代的照顾问题落在老大和凤娟身上的时候,天平就已经倾斜了,在照顾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生意上太忙碌,他们后来把母亲送到了养老中心,这种对上一代的简单处理,使得已经身患疾病的老母亲更陷于孤独的境地。
除了上一代的问题,还有他们必须面临的下一代的生活,老三只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康康,不仅康康的智力不正常,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一次老三就对顾雪说,“要不是你奶奶在,我早就把康康扔到水里淹死了。”这或许是气话,但是老婆跑了、儿子患病,对于老三来说压力的确太大了;老二拿到了拆迁款,他们一心只为儿子阳阳结婚的事忙碌,2.3万每平方的放价他们也没有多少犹豫,而买了房他们依旧生活在小船上,依旧到江上捕鱼,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阳阳不要像顾雪一样,在婚姻问题上惹父母不高兴。阳阳并无多少波折的婚姻,当然在和顾雪的对比中体现出来,而这一代和下一代最大的矛盾就体现在顾雪和父母在婚姻观上的冲突,凤娟一心希望顾雪能找到一个有地位的男朋友,那天参加老母70岁寿宴上他们认识的汪主任便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汪主任有一个28岁的儿子,但是顾雪喜欢的是在学校里教书的普通教师江一,这让凤娟大为生气,在中秋节甚至赶走了江一,还因为这件事住进了医院,而顾雪的爱情观就是“一辈子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和江一走到了一起,在江上江一父亲的沙船上举行结婚仪式,顾雪的父母都没有来,而看着这场并不隆重婚礼的只有站在江边的老三,在顾雪看来,三叔是世界上最重情义的人,在老三的目送中,顾雪走进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天地。
这一代和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在代际之间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冲突,在如画卷展开的故事里,他们就是表现了宏大叙事下的人间烟火:富春江泮的富阳,因为要迎接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新城建设正热火朝天的展开,这种冲击对于长期居于此的普通市民来说,生活的确发生了改变,但是顾晓刚并不是要展现时代变迁中的家族故事,其实略去这些所谓的背景,每个人的故事也都会在纠葛中上演,而这正是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非消失点散点透视”手法,在琐碎的故事里,在市井的生活中缓缓讲述,而在镜头运用中,那些长镜头似乎就是和这种传统手法形成了呼应:有一处长镜头是顾雪和江一在富春江边约会,江一和她打赌,自己游泳比她走得快,于是在江一沿着江边游泳中,镜头一直跟随着他,直到顾雪站立的河边,然后江一上岸,然后两个人又聊到了这条江,聊到了学校生活,聊到了参演的戏剧《跳墙》——在这一长达10分钟的长镜头里,不仅江一在游泳时镜头像长卷一样缓缓拉开,岸边坐着的人,垂钓的人,散步的人都在移步换景中被呈现出来,又在两个人畅快的交谈中体现着爱情的力量。而在另一处长镜头中,镜头语言的寓意更加丰富,那是在老太太出走之后,老三去找算命的卜算母亲何时回来,而老大和凤娟则买了鱼到江里放生,镜头从他们放生开始,然后横移过去,是一个背着鱼篓和钓竿的钓鱼人,他正走在道上寻找最佳的钓鱼点——钓鱼者似乎正在解构放生时的祈愿,而这一镜头的运用似乎正把老母的命运推向了未知中;在镜头横移的过程中,是另一个站在岩石上的垂钓者,似乎那条刚刚放生的鱼要被他捕获;再横移过去,是逐渐宽阔的江面,江面上漂浮着一条小船;镜头逐渐拉近,小船上佝偻着一个穿红衣服的老人,她是那么无助,那么孤独,而这个红衣老人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老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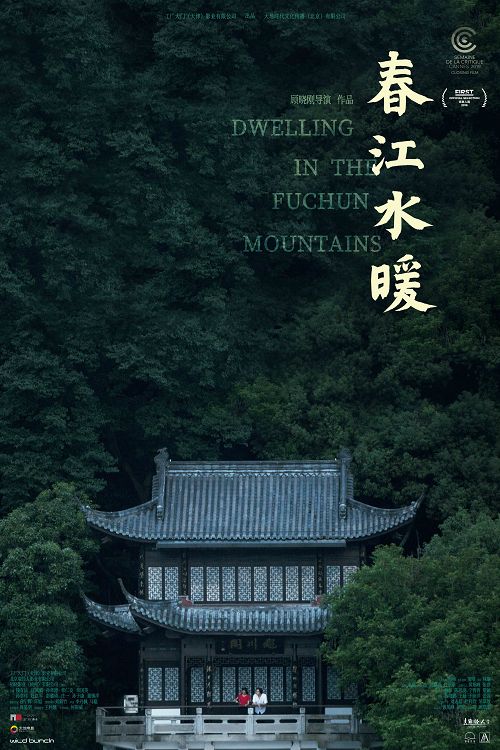
《春江水暖》电影海报
长镜头如长卷展开,当侧面横移在发生,镜头变成了一种运动,它收纳了那些景和人,包容了故事,营造了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人物的悲欢离合似乎都一一呈现出来。但是在这个“非消失点散点透视”的美学运用中,顾晓刚显然在制造延伸性的同时,讲述故事中却陷入了某种断裂中。最浅显的突兀在于语言风格上,据说顾晓刚在挑选演员上进行了“家族总动员”,大部分的演员是顾晓刚的亲戚,他们就是用本土的富阳话来对话,作为观者来说,这种纯自然的语言运用起到了一种地缘的亲近感,仿佛这些故事就发生在你我之间。但是在这些业余演员之外,顾晓刚也选用了专业演员,奶奶、顾雪和江一三个角色就是启用了专业演员,暂且不论专业演员和业余演员在表演上孰优孰劣,在语言上很自然被甄别出来:业余演员用的是本地化,而专业演员用的则是普通话,当一种吴侬软语遇上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断裂感产生了,凤娟在老大因为饭店客人而喝醉了酒的时候,发出了感慨,“要不是你,我和你老爸早就离婚了。”而顾雪接上去的话却是没有任何口音的普通话,仿佛他们不是母女,语言天然隔开了他们之间的融合感。
语言本来是电影的一大特色,但是业余和专业的分野使得语言成为最大的败笔,而这种败笔更体现在三代人之间的断裂上:顾雪作为下一代,讲一口普通话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同为下一代的阳阳讲的却是本地化?下一代讲普通话,这一代全部讲本地话,但是老母亲为什么也讲普通话?三代人之间在观念差异之外,浅显的语言差异并不是预设,而是本身犯的一个逻辑问题。相关的逻辑问题还体现在老母亲和儿子经历的隔阂上,四个兄弟似乎都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的言谈举止显得很普通,但是,作为母亲,上一代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范,那时的顾雪送给奶奶笔记本,让奶奶在上面写点东西,而当老母亲去世之后,在墓地上儿子用本地话读起了母亲曾经写下关于富春江上七月十五放水灯的情节,那种遣词造句,那种抒情味,完全是个文艺青年的笔调。
不仅仅只是语言间的隔阂,也不仅仅只是书和写之间的差异,其实奶奶这个形象完全被架空在世俗层面之上,她的出身和改嫁,被放在了隐秘的历史中,她的患病则成为和现实无关的人,她的出走是迷途,更是一种逃离,这样一个人物完全无法融进这个家族故事里,她更像是一种遥远的传说,和山水画卷独特意蕴的存在一样,顾晓刚似乎想寻找到一点世俗之外的存在,但是将老太太如此别扭地安放在这一长卷中,只能产生强烈的断裂感,而人间烟火也在断裂中变得缥缈起来——昔日孙权故里,达夫家乡,如今针灸赌场,火罐泡汤,这一条春江在历史与现实,传奇和生活的错位中,似乎也走向了无法融合的断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