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6《故事新编》:向“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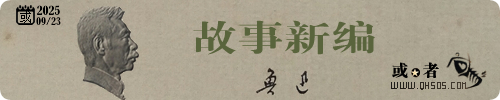
待到上午,清道的骑士才缓辔而来。又过了不少工夫,才看见仪仗,什么旌旗,木棍,戈戟,弓弩,黄钺之类;此后是四辆鼓吹车。再后面是黄盖随着路的不平而起伏着,并且渐渐近来了,于是现出灵车,上载金棺,棺里面藏着三个头和一个身体。
——《铸剑》
灵车上,金棺里,三个头和一个身体,无以分辨出哪个头是楚王,哪个头是眉间尺,哪个头是黑衣人,如“一个人玩不起”的把戏,在三头合一中,所谓复仇,所谓葬礼,所谓“憎恶了我自己”,也都三者合一,于是,在众人迎送中,似乎也走向了太平,“这歌舞为一人所见,便解愁释闷,为万民所见,便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之前,是十六岁的眉间尺要报杀父之仇,“铸剑”便是从父那里延续而来的宿命,天下第一的铸剑师,将工具都卖掉了救穷人,这去除了武器的行为像是为了天下太平;但是当二十年前王妃生下一块抱了铁柱之后受孕的铁,当楚王将这块纯青透明异宝让干将铸剑,“想用它保国,用它杀敌,用它防身”便又走向了杀戮之地,整整三年,用“井华水”铸成两把剑,干将也无非是在铸剑本分上做了这一件事,而且还将这“纯青的,透明的,正像两条冰”的剑埋在了地下,更是一种对杀戮的拒绝;但是既然能铸剑,便也逃脱不了宿命——当被楚王杀害,仇恨便延续到了眉间尺身上,而眉间尺暴烈的脾气,在母亲看来,并不能承担复仇的使命,“你从此要改变你的优柔的性情,用这剑报仇去!”
憎恶老鼠,又狠狠地将它踩死,怎么就没有复仇的性情?从洞穴里挖出纯青透明的剑,更是一种杀戮的回归,即使眉间尺提着剑向南走避开可能杀人的城市而选择南门外,也是在等待着复仇上演。父的影响在眉间尺的身上,眉间尺是有着不可逃避的宿命,但是黑衣人出现,却让眉间尺去掉所谓的仗义,所谓的同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都是“受了污辱的名称”,但是既然是为父复仇,黑衣人却能成全他,但是必须给黑衣人两件东西,一个是那把剑,一个则是眉间尺的头。复仇被转移,对于黑衣人来说,只不过是杀戮中多增加了一个人头,或者两个人头而已,因为黑衣人就是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
把眉间尺的头提到楚王面前,便是结束了眉间尺的宿命——一方面是对着死掉的嘴唇,接吻两次,“并且冷冷地尖利地笑”;另一方面则在楚王面前演绎“歌舞”:“于是放下孩子的头去,一到水沸,这头便随波上下,跳舞百端,且发妙音,欢喜歌唱。”这是一个人玩不起来的把戏,需要在金龙之前摆上金鼎,然后注满清水,然后用兽炭煎熬,眉间尺的头在随波上下,而且还欢喜歌唱:“彼用百头颅,千头颅兮用万头颅!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一头而具有千头万头的功用,这的确不是一个人玩的把戏,但是真正需要一起玩的则是楚王的头,于是在楚王靠近鼎镬时,在望见“似曾相识”的头时,黑衣人用那把青色的剑砍下了楚王的头,连个头在沸水里,眉间尺的头咬住了王的耳轮,在二十回合的死战中,两个头都受了伤,最后是王更狡猾,咬住了眉间尺的后颈窝,“这一回王的头可是咬定不放了,他只是连连蚕食进去;连鼎外面也仿佛听到孩子的失声叫痛的声音。”
在两个头的鼎镬里,谁向谁复仇?谁又向谁回击?而黑衣人的头也落入水中,一口咬住了王的鼻子,眉间尺的头就趁机挣脱,反过来又咬住了王的下巴,三个头混合在一起,复仇的头,回击的头,杀戮的头,不是一个人玩的把戏,早就模糊了最先单纯的复仇故事,而这个在鼎镬里不止的争斗制造了另外的看客,“鼎里的水却一平如镜,上面浮着一层油,照出许多人脸孔:王后,王妃,武士,老臣,侏儒,太监。……”照出了看客的脸,便是示众:分不清谁是王谁是眉间尺谁是黑衣人,分不清谁是暴力的人谁是复仇的人谁是杀戮的人,当然也分不清什么是仗义什么是同情,示众于一段舞一段歌以及一场把戏,解愁释闷,便是天下太平——只是在“爱一头颅兮血乎呜呼!”中,“铸剑”的轮回并没有被这场把戏消融。
让王宫里的人被一一照出来,让百姓在解愁释闷中迎来太平,消除了仗义和同情,真的只是一场无分敌我的把戏——这是一种庸俗?背负大义的复仇变成了庸俗的把戏,这是在示众中的死,而《起死》中的那个死了五百年的髑髅是不是也成了一种死的示众?庄子去见楚王,路上看到一个空髑髅,还有头的样子,于是想象他是如何死的?“您是贪生怕死,倒行逆施,成了这样的呢?还是失掉地盘,吃着板刀,成了这样的呢?还是闹得一榻胡涂,对不起父母妻子,成了这样的呢?您不知道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吗?还是您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成了这样的呢?还是年纪老了,活该死掉,成了这样的呢?还是……”一个人会有不同种可能的死法,或者因为贪生怕死,或者因为躲避灾祸,或者因为无以见妻子父母,或者是因为贫穷落魄,但是庄子在不停的“橐橐”中把他的死只看成一种选择:自杀,为了解答自己的问题,要求司命“复他的形,还他的肉,给他活转来,好回家乡去”。
司命说他“不安分”,是因为既然已死在示众中何必让他回到活的痛苦状态中,而庄子以“庄周梦蝶”为喻,将生与死融合在一起,“这样看来,又安知道这髑髅不是现在正活着,所谓活了转来之后,倒是死掉了呢?”这是庄子所谓的“圆滑”观,所以司命作为神不必太迂腐,于是髑髅活了过来,是死了五百年后活了过来,“我不过在这儿睡了一忽,什么死了五百多年。”所以要赶着去探亲,要穿起衣服,拿起包裹,“我没有陪你玩笑的工夫。”甚至气愤地叫来了巡士,说庄子偷拿了他的东西,庄子说是救了死去的人,怎么变成了抢人家东西,巡士似乎也嘲笑庄子,说自己的局长就喜欢他的《齐物论》,“什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真写得有劲,真是上流的文章。”最后把他带到局里“歇歇吧”。而对于死去的髑髅变身为活着的汉子,巡士也不相信,当汉子要去探亲,要拿回自己的“二斤南枣,斤半白糖”,甚至要和巡士拼命时,巡士摸出警笛,狂吹起来,“不要捣乱了!放手!要不然……要不然……”
庄子如梦见蝴蝶一样看见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状态,那梦便是《齐物论》的文本,但是当从五百年前的死中活过来,当探亲成为汉字当下的生活,却又在生的状态下失去了“圆滑”的一样,那象征秩序和规则的巡士既要把庄子带回局里,又用警笛压灭了汉字的需求,“起死回生”终于变成了另一种庸俗,何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何来五百年前的死是当下的生?何来“上流的文章”、正经的事?这是被巡警示众的活,和眉间尺报仇而变成把戏的示众的死一样,被消解了“圆滑”和“庸俗”,甚至圆滑和庸俗也都成了一种罪——当女娲醒来,在双腿间出现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便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便只剩下”庸俗“在跋扈了。
女娲补天,《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如下:“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墬(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烘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当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水火成灾的时候,女娲像一个英雄,“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终极灾难,去除混乱,恢复秩序,建立规则。但是在《补天》中,女娲醒来,是感觉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从天地间走向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还有浪花溅在身上,不由地下跪,掬起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以为是自己做的,有疑心原在泥土里,“然而这诧异使伊喜欢,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直到天崩地裂的声音传来,女娲才醒悟到先前的小东西在喊救命,“救命……臣等……是学仙的。谁料坏劫到来,天地分崩了。……现在幸而……遇到上真,……请救蚁命,……并赐仙……仙药……”
天缘何会崩?“颛顼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讨,战于郊,天不祐德,我师反走,……”无非是“天降丧”,于是女娲开始补天,和天一色的纯青石是没有这么多,去寻些零碎的又遇到了冷笑和痛骂,甚至还被咬了手,只好搀些白石,凑上些红黄的和灰黑的,补天有些累了,那声音又出现了:“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也是“天降丧”,也是让女娲成了道德的补救者,而在最后补好天之后,“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女娲死去,天以不丧,但是却让老道士开始寻找长生不老之法,只是女娲未曾真的成为道德补救者,于是,“所以直到现在,总没有人看见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发见了若干野蛮岛。”
女娲只是醒来,女娲只是惊异于浪花,女娲只是好奇于小东西,女娲只是圆滑和庸俗,天降丧和她无关,“不道”和她无关,“失德蔑礼败度”也和她无关,却最后在道德补救中死去。“补天”终究不是一个“认真”的故事,但那小东西倒背如流的声音却在回荡,有人说《不周山》为佳作,就是不庸俗,因为“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而这“惟禁”是对另一种声音的回应,“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但是女娲两腿间出现的小丈夫,终究如浪一般是“失德蔑礼”的——不是“博考文献”的历史小说,不是“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是自甘“庸俗”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将《不周天》从《呐喊》中移除,并改名《补天》,便是向“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女娲的两腿间“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是为庸俗;背负复仇之使命的眉间尺在沸水里“跳舞百端,且发妙音,欢喜歌唱”演绎了把戏,是为庸俗;庄生把五百年死去的髑髅“复他的形,还他的肉”写成另一篇“上流的文章”,是为庸俗……庸俗在跋扈,油滑作开端,只取因由,随意点染,冷暖自知,向“魂灵”回敬当头一棒便是将“故事新编”之用意——“故”和“新”构成了一种解构式的油滑文本,神话、寓言记于古书之上,就像穿古衣冠的小人,最终却在这庸俗的新编中出现在女娲的两腿间。《奔月》中对于整天吃乌鸦炸酱面感到厌烦而奔月的嫦娥,之所以选择离开,是因为后裔已经“四十五岁”,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她上月还说:并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而后羿这老人,便是被逢蒙攻击的,“那是逢蒙老爷和别人合伙射死的。也许有你在内罢;但你倒说是你自己了,好不识羞!”《出关》里的老子本就像一段呆木头,“性,是不能改的;命,是不能换的;时,是不能留的;道,是不能塞的。只要得了道,什么都行,可是如果失掉了,那就什么都不行。”对孔子说了这一段话,孔子倒失魂落魄,“恰如一段呆木头”,几个月也是未识得变化,“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老子终于出关,五千字《道德经》是离开“上朝廷”的那个世界,“我的是走流沙”,即使五千字行文,也无非是如孔子一样的呆木头;《非攻》中的公孙高说:“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曹公子说:“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对于回应,墨子对公孙高说:“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对曹公子的回应是:“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而对于公输班,则阐述了自己的“油滑观”:“我用爱来钩,用恭来拒。不用爱钩,是不相亲的,不用恭拒,是要油滑的,不相亲而又油滑,马上就离散。”但是墨子之“于民有利”、“兼爱无父”、“互相爱,互相恭,就等于互相利”,最后还是遇到了遇到了“认真”的人:“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采薇》里的伯夷叔齐,把“乐器动兵”看成不合王道,把变乱旧章看成是“以下犯上”,于是住在养老堂里,于是去了首阳山,于是食薇而拒绝周粟,最后死在那里,小丙君一语道破了遗老的悲剧:“都是昏蛋。跑到养老堂里来,倒也罢了,可又不肯超然;跑到首阳山里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唉唉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儒家的魂灵,似乎是保存着尊严,似乎是对抗着庸俗,似乎是恪守着秩序,似乎是“认真”地活着,可是,《理水》中,当“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时,那些学者们却坐在“文化山”上研究着学问,看不起禹是因为有着血统论,“阔人的子孙都是阔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这就叫作‘遗传’。所以,鲧不成功,他的儿子禹一定也不会成功,因为愚人是生不出聪明人来的!”还针对乡下人,说他们也都是愚人;那些考察的官员们无视灾害,“一大阵独木大舟的到来,是在头上打出疙瘩的大约二十多天之后,每只船上,有二十名官兵打桨,三十名官兵持矛,前后都是旗帜;刚靠山顶,绅士们和学者们已在岸上列队恭迎,过了大半天,这才从最大的船里,有两位中年的胖胖的大员出现,约略二十个穿虎皮的武士簇拥着,和迎接的人们一同到最高巅的石屋里去了。”那些无知妄说的人,认为榆叶里面是含有维他命W,认为海苔里有碘质,可医瘰疬病,认为“含一点黄土,饮用之前,应该蒸馏一下”——把禹看成是一条虫,或者大猴子,都是另一种“示众”,只有将“湮”改为“导”的禹是实践派,是改革派,是民生派,“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和稷俩给大家有难得的东西吃。东西不够,就调有余,补不足。搬家。大家这才静下来了,各地方成了个样子。”而最后对于这水灾的成因,便是对天的敬重,“做皇帝要小心,安静。对天有良心,天才会仍旧给你好处!”
无论是油滑,还是庸俗,所反对的无非是以“魂灵”的名义恪守的旧礼教,无非是以“认真”的方式拒绝革新,无非是血统论、温柔敦厚、为艺术而艺术,而最终扼杀了人的存在,于是“故事而新编”,油滑而庸俗,让他们不死,“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