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17《华盖集》: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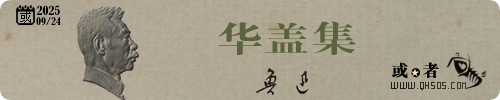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导师》
不是导师,更不是鸟导师,从新文化运动中走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早就说过,自己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不会是不主张消极的主将,只不过要大嚷起来,让铁屋子里的青年不至于“从昏睡入死灭”,从而在醒来之后“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但是当否定自己捕捉“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不为青年寻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便是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如朋友一般“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或是勇猛或是悲哀,或者可憎或是可笑地“呐喊”。
否定自己是导师,而且预言青年们“将永远寻不到”导师,不仅要让青年在路上寻找方向,也是让自己不断摸索,或是身林,则可以辟成平地,或是旷野,可以栽种树木,或是沙漠,可以开掘井泉,在荆棘塞途的老路上,需要的不是有人指点方向放置出口,而是自己去发现适合自己的路,也而看见自己身上的生力——“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青年必读书》)”对导师的否定,对方向的否定,对道路的否定,鲁迅当然也是青年,当然也是不像“鸟导师”一样高高在上的青年,曾经的梦想是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虽然鲁迅说自己没有余暇心开意豁,理论也缺少公允欠妥,在地上只不过是沾水小蜂,在你图上爬来爬去,即使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既不是平正通达的“正人君子”,也不是洋楼中的“通人”,而只是一个活在人间的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而已。
顶上的有华盖,如和尚便是交了好运,因为那时成佛作祖的兆头,但既然不是飞空,不是高高在上的“鸟导师”,俗人还容易被“华盖”罩住,甚至会碰钉子——这对于可以和青年们一起行动的人来说,倒也看见了这活着的人间的苦痛;而且那艺术之宫里立着禁令,倒不如不进去,便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甚而觉得那时一种“花纹”,却是超越艺术之宫中的美——这是苦痛的美,这是战斗的美,这是大笑大叫大骂的美,只有将它们注入到生命之中,何须遮盖,何须惧惮,“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而且对于别人来说,一样走在这风沙中,在这荒漠中的人,也是容易感受到的,因为,“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活在人间,走在路上,站于沙漠,依然是战士,“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即使战士死了,有苍蝇发现了他的缺点和伤痕,还“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以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但是,“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战士是有着“营营地叫着”、自以为得意的苍蝇存在,才成为战士。那么,那些苍蝇是如何营营地叫着?如何自以为完美?它们是那些鬼画符的人,说什么:“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又说什么:“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还因为有人生疮而他是中国人于是中国人都生疮,还因为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而中庸的太太则提笔为精神文明做明哲保身的格言:“中学为体西学用,不薄今人爱古人。”又或者是那些嘴上说摆脱了传统思想束缚而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或者叫“思黛儿”,或者叫“雪琳娜”,或者Gogol姓郭,Wilde姓王,Holz姓何;Gorky姓高,再者也可以将奴隶改成“弩理”,或是“努礼”……
名为维新,实为守旧,名为改革,实为复古,更是一种听天命,更是一种“中庸”,“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通讯》)”继而又回到“反改革”的浓厚氛围里,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还将人家活埋了,那种《新青年》时的“思想革命”都成了空话——他们在“咬文爵字”,他们在制造更多“鬼画符”,他们在用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造了更多的长城,就如那些书,“满本是密密麻麻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原本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不见了,上下的天地头也没有了,于是“不留余地”的空气了,人的精神也被挤小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忽然想到》)”而康圣人不是主张跪拜的吗,因为在他看来“否则要膝何用”。如此,现在是中华民国,则还是五代,还是宋末,还是明季,“但保古家还在痛骂革新,力保旧物地干:用玻璃板印些宋版书,每部定价几十几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汉时已入中国,其古色古香为何如哉!买集些旧书和金石,是劬古爱国之士,略作考证,赶印目录,就升为学者或高人。”
主张跪膝,主张中庸,主张国粹,主张“不留余地”,所以这国民性是不会改变的,那些破例复生的希望,那些改革者的慰藉,“也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而且“古已有之”。所以鲁迅瞀乱的神经开始感到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但是涂饰得太厚,废话太多,即使通过密叶投射到莓苔上面,那月光也只是点点碎影。营营叫着的苍蝇,太多了,而战士呢?终于站起来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战士对战士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战士开始行动,“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战士冒着大危险,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但要反抗,要扑灭,“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而不是导师的人,是要将青年从牢狱里印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
路上的危险是什么?是暗器,是毒药,是流弹,是病菌?那些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或者并不需要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杂感》)”真的愤怒果然来了: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风潮发生,迁延数月未能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种种黑暗情况,请求将杨荫榆撤换,不发表宣言,同年四月,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由拒绝学生请求,并于八月将女师大学生殴曳出校,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迁回原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并非孤立事件,它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而作为同情、支持学生的教员,鲁迅目睹了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也参与其中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除了杨荫榆、章士钊,还有陈西滢等人,于是,鲁迅便和青年们成了在一起的战士,在营营的叫声中,“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
风潮发生,鲁迅第一次发声便认为国民性是两样东西的混合:凶兽和羊,是凶兽样的羊,是羊样的凶兽,“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凶兽和羊是国民的二重性表现,“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发表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言论,还趁“五七”之际,在饭店请人吃饭,又开除了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是家庭关系,那校长和学生是怎样的关系?母女或者婆媳?鲁迅在学校教书,是不是也等于在“杨家坐馆”?“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碰壁无非是鬼打墙,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鲁迅说不是,“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
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的作者在《女师大风潮》中说,女师大学生迭次驱杨的“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又说“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陈西滢也在《闲话》中说女师大是“臭茅厕”,“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并不想以骑墙和阴柔来买人尊敬的鲁迅则抨击道:“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而对于陈西滢讽刺的某籍某系,鲁迅反讽道:“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但并非被流言所吓,“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
当章士钊将鲁迅免职,鲁迅在《答KS君》中说,“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当陈西滢说:“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鲁迅却讽刺他:“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当陈西滢说鲁迅没有“学者的态度”时,鲁迅反问:“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硬派我做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点不知道。”不是学者,因为不是理想的奴才;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迁回原址,陈西滢又开始攻击,鲁迅发表“碎话”:“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杨荫榆和章士钊攻击说学潮只是“少数人”的把戏,鲁迅在《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中说:“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当章士钊压迫北京大学,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放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之后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为此鲁迅在《我观北大》中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是历史中形成的北大精神,而在当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由此鲁迅认为北大就像时下的青年一样,“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北大是活着且生长的,青年是活着且生长的,而那些制造“流言”的人,攻击是“蛆虫”的人,却是那些死了的人,《十四年的“读经”》中鲁迅便将章士钊看成是开倒车的“读经派”,“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读经派自视为“正人君子”,其实是卫道士,“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反正会健忘,而对于中国来说,便成了衰老的国度,“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在《这个与那个》中,鲁迅又回到了古已有之的国民性中,有人说读经还可以“救国”,鲁迅说不如去读史,“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有人说中国人被旧习惯和旧道德压下去的,鲁迅却说中国人自讨苦吃却是因为捧,“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中国人从赛马中得出妙法,“不为最先,不耻最后”,但是不做前驱和闯将不做改革,最后只好用了阴谋和手段,“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中国人喜欢等待,但是,“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这个与那个”,这个是读经,那个是读史,这个是捧,那个是挖,这个是最先,那个是最后,这个是流产,那个是断种——这个和那个,便也是战士和苍蝇的分野,而在北京女士师范大学风潮之外,则是另一事件:五卅惨案——当上海学生声援工人而被英国巡捕逮捕,当群众要求释放学生而早枪击,这无疑是“文明和野蛮”的一种颠倒,自诩为文明人的英国人在野蛮的捕杀中揭下了面具,而文明之于古老的中国呢?是不是也揭下了假面具?“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枪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梁启超在《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五分钟热度,是义和团式的爱国,不是真正的国耻纪念,那么真正的国耻纪念是什么?是金人用狼牙棒时宋人用“头盖骨”?是一战时西方用枪炮中国用公理?——“公理战胜”的牌坊,立在中国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群众和学生曾经欢呼,但是这是胜利?鲁迅说,“实际上是战败了”,“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所以当爱国学生变成“五分热”,患病的不是学生,而是全民的耻辱,“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来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
“流言”如营营之声,“公理战胜”如营营之声,“五分热”更是营营之声,“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而战士不做鸟导师,不是读经派,不是凶手和羊,是有着记性而战斗的人,“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520]
顾后:我站于光阴的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