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26《三闲集》: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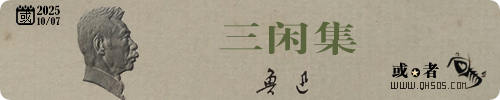
那么,这一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
——《“醉眼”中的朦胧》
“武器的艺术”落在谁的手里,便知道“中国的最近的将来”,这“武器的艺术”只有在手里才能成为最高的艺术,但是当最近的未来还没有到来,“大时代”还在显得遥远,鲁迅的疑问和未知在现实意义上便指向了两种境遇:一种是“武器的艺术”只是在“非革命武学家”那里变成玩意儿——有几种“笑迷迷”的期刊便是“武器的艺术”;另一种则是“艺术的武器”,以艺术为武器进行着所谓的革命文学,甚而扯起大旗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学”。一种是“笑迷迷的期刊”变成“武器的艺术”,一种是以“艺术的武器”进行革命文学,这两种都不是最高的艺术,当然,也不能知道中国最近的将来。
但,不管是“艺术的武器”,还是“武器的艺术”,似乎都在接近革命文学,甚至都在“为革命而文学”,革命文学终于笑迷迷玩起来了,所谓的醉眼陶然便也消失了?但是创造社冯乃超所说的“醉眼陶然”在鲁迅看来,却还是现时的,“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这当然不是革命,只是朦胧,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但都是有着这一个共同点。这朦胧似乎显示的是文艺的特色,一种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有些瓜葛,又为了表示和气,不是用铁锤和镰刀,也不是对主子的恭维,于是朦胧既是遮羞也是表达态度;另一种是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已无瓜葛,而且想要笔下雄赳赳了,但是在指挥刀下的傻子总是不多的,于是留着一些朦胧。
朦胧是艺术,但武器大约是看不清了,这或者就是那些所谓革命文学的样子,而在中国,更朦胧的一点是,即使有态度,即使要批判自己,即使要拿起指挥刀,但是最后都变成了“武器的艺术”,知道目前的情状,但也觉得“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于是,这革命和文艺,这剥去和抗争,在鲁迅看来,变成了“咬文爵字”,而不是“直接行动”——创造社揭起了“革命文学”的旗子,批评家成仿吾离开了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开始要去“获得大众”,终于要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鲁迅发声道:当他们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根性,当他们拉大众做文章的材料,“你去不去呢?”
鲁迅问“你去不去呢?”似乎是问自己在面对揭起旗子的革命文学:“你去不去呢?”不止是成仿吾,李初梨在《文化批判》上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无论出生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大有一种只要有无产阶级意识的大众都可以去从事无产阶级文学,但是,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鲁迅,就会问一句“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不是以阶级为评判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却又制造了阶级论,那么自然鲁迅这个被他们称为“语丝派”主讲和倡导者的人,自然是没有资格去的,“你去不去”就是将鲁迅排出去了,这和成仿吾的论调一致,因为成仿吾对于“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发出了切齿之声——三个“闲暇”当然不是大众,也不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人,而有人批评鲁迅的小说,“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有人把革命看成是“杀,杀,杀,”——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鲁迅这个“老头子”要用“杀,杀,杀”来制造革命,便是将刀对准了可怕的青年。
“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里面是成仿吾的切齿声,“杀,杀,杀”里则是杜荃对于封建余孽的咒骂声,而“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里则是对于批判的批判,三个闲暇,三个杀,三个冷静,不同的声音都指向了对于鲁迅的质问:革命文学,“你去不去?”——甚至去都不是鲁迅该有的资格,于是醉眼还是醉眼,朦胧还是朦胧,革命也都是他们的革命——无论是艺术的武器,还是武器的艺术,都让鲁迅变成“不革命”,而“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于是,一九二八年的鲁迅“便将于八时间工作之暇,坐在黑房里,续钞我的《小说旧闻钞》,有几国的文艺也还是要谈的,因为我喜欢。”
似乎还是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分开来是革命,是文学,是革命如何用文学表达,是文学如何阐述革命的理念——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写什么?“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时的苦闷和悖反并没有消解,从厦门到广州,从革命到反革命,既不是沉默也无法开口,既需要充实也感到空虚,但是,那血管里流出的血大约是有些干涸了,“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写什么成为一个问题,并不在于是用血还是用墨,而是应该写下什么?在鲁迅面前是两本刊物,一本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做什么》,一本是孔圣裔主编“革命文学社”编辑发行的《这样做》——两本刊物以问和答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命题,甚至有人说它们都是鲁迅离开厦门南来之后“向后创办”的,“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鲁迅的疑惑是:这两本如此大相反的刊物,怎么都因我南来而创办?“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新来且灰色,其实在拒绝《做什么》,也在否认《这样做》,于鲁迅而言只有一个唯一的问题:写什么?“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鲁迅其实是清醒自己的立场,是革命还是不革命,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或者是革命者还是“有闲阶级”?从厦门到广州,鲁迅的轨迹似乎在循着革命的意义,但是并不是对于加入某一党派的渴望,即使关于革命,也不是盲从,“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革命似乎不如一杯牛奶,所以革命诗人的理想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在鲁迅那里便成为一种幻觉,“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而这种态度又被人认为是“躲避”,宋云彬警告鲁迅说: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写什么”还没有找到答案,各色人等,各种刊物似乎对鲁迅下了定义,于是,索性从香港的《循环日报》上摘录了“匪笔三篇”“某笔两篇”,“匪笔”便是“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那篇撕票布告、致信女某书、诘妙嫦书也都是和陈涉帛书、米巫题字、义和团传单、同善社乩笔一样,“也都是这一流”;而“某笔两篇”是“熊仲卿榜名文蔚”,是“征求父母广告”,这些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在鲁迅看来,“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当然也比革命文学丰富的多,甚至,匪笔和某笔里的“社会相”更是接近革命的主体——大众,看起来是闲人所造的文化,是适宜于闲人的艺术,但“文化之兴,须有余裕”。
所以在鲁迅看来,文艺与革命,革命与文学,并不如创造社、太阳社等派所说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扯起旗子就可以完事,他们的做法看起来只不过是“输入名词”,“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扁》)”它只不过是某某主义,所以,“在文艺批评上要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无产阶级文学在上海的文艺界已经很热闹了,但是问问黄包车夫却并不知道,“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有人看到了鲁迅,说他在上海某咖啡馆里,于是被人嘲笑是“革命咖啡馆”,鲁迅反讽说:“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如我者,在《战线》上就宣布过一条‘满口黄牙’的罪状,到那里去高谈,岂不亵渎了‘无产阶级文学’么?”
革命文学不是“输入名词”,不是挂起匾额,不是某某主义,“冬芬来信”表达的就是刺中忧虑,“在现在,离开人生说艺术,固然有躲在象牙塔里忘记时代之嫌;而离开艺术说人生,那便是政治家和社会运动家的本相,他们无须谈艺术了。”所以他问鲁迅:“热心革命的人,尽可投入革命的群众里去,冲锋也好,做后方的工作也好,何必拿文艺作那既稳当又革命的勾当?”文艺有自身的价值,戴上革命的冠冕是不是一种梦呓?鲁迅回信说:“各种主义的名称的勃兴,也是必然的现象。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虽然有许多在受难,但也有多少占权,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但是现在所自称的革命文学家,是把革命看成是超时代的斗争,挂起革命的招牌,就是变成了永远的文学,鲁迅讽刺这一种革命观:“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而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文艺只是一种宣传,“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
革命里有口号,有标语,有布告,有电报,有教科书,这些都是革命文艺,但是只是在宣传上挂了招牌,“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不敢正视,像《申报》上的记事:“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用“太平歌诀”来躲避危险,就像革命文学家,“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不敢正视,倒变成了投机者,还是《申报》,一段《长沙通信》上说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革命反被革命,是因为投机者潜入,是因为内里蛀空了的革命,“但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包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铲共大观》)”
不敢正视的革命者何来革命的勇气?那“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Y”写给鲁迅的信里也是不敢正视现实的痛苦,但至少比挂着革命文学的旗子的人更真实,“‘革命!革命!’的叫卖,在马路上呐喊得洋溢,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但是现实依旧是欺诈、虚伪、阴险,“不错,没有希望之人应该死,然而我没有勇气,而且自己还年青,仅仅廿一岁。还有爱人。不死,则精神和肉体,都在痛苦中挨生活,差不多每秒钟。”生命已经被革去了,被毒害的青年找不到出路,更不知道革命是不是能改变生活。鲁迅在回信中说:“革命而尚不死,当然不能算革命到底,殊无以对死者,但一切活着的人,该能原谅的罢,彼此都不过是靠侥幸,或靠狡滑,巧妙。他们只要用镜子略略一照,大概就可以收起那一副英雄嘴脸来的。”所以需要革命,但是革命并不是做了革命文学就可以成功的,革命文学只不过是于人的文字,而且“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于自己而言,也不是所谓的革命家,也不是为青年指明道路,真正的革命是一种超越,是一种进步,“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
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这是鲁迅的自谦,也是对于进步的渴望。当不是革命家打破了“革命文学的牌坊”,当革命文学不应该只是名目,其实对于真正的革命文学乃至无产阶级文学,鲁迅是保持着某种怀疑的态度,而这种怀疑论在和文人的论战中表现得更为对立:和顾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的笔战升级为“法律解决”;创造社的“文艺的分野”和弱水的“醉眼”,演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由“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蒋光X拜帅”的《太阳》,“王独清领头”的《我们》,“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和《战线》,“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这些在“革命文学”主战场上挥动旗帜的刊物和“落伍者”之间的战斗;针对“革命文学家”张资平的流氓论、新月社批评家的“思想自由”的讽刺……在论证、论战甚至诉讼中,落伍者的鲁迅一直在反对超阶级性的革命文学,“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上的讲演《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则清晰地表明了他一贯的态度:文学由环境应运而生,当今的环境,只有政治上的革命已经开始,无产阶级文学只不过是一个题目,“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
巨大的革命到来了吗?只不过是巨大的口号和巨大的攻击;革命文学出现了吗?只不过“杀杀杀”的可怕声音;革命文学家诞生了吗?只不过是揭了旗帜、拉了所谓大众、拿了“艺术的武器”的人,而对于“有闲阶级”的鲁迅来说,即使到了一九三二年写作《序言》和《鲁迅译著书目》的时候,也依然没有看见真正的革命文学,只是在革命文学家那里,他变成了他们口中的“没落者”、杂感家、封建余孽、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革命似乎更急于革鲁迅的命,要在“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中棒喝鲁迅,要在“杀,杀,杀”中杀死这个“老头子”,而鲁迅呢,从广州到上海,在距离《而已集》四年之后继续编写着集子,做着“有闲阶级”,而这种有闲在鲁迅看来也变成了“武器的艺术”,“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一番话。(《鲁迅译著书目》)”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