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07《新浪潮》:你被一只死蜜蜂蛰过吗?

“你被一只死蜜蜂蛰过吗?”理查总是问侯杰这个问题,一边又一遍,但是侯杰始终没有回答,他以沉默的方式对应;当他最后和妥拉托·法佛理尼伯爵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且他做出了回答:“一只死蜜蜂会像活着一样蛰你,因为它死于愤怒……”在一个问题面前,他是被回答者,沉默不是沉默,是未知;在另一个问题面前,他是回答者,答案指向了已知——被回答和回答,沉默和自问自答,以及未知和已知,一只死蜜蜂构筑了两种可能:蛰过或者未蛰过,而两种可能也指向了两种经历:死于愤怒和像活着一样满带愤怒的报复。
实际上,这是一只死蜜蜂和另一只死蜜蜂、一种死和另一种死的对立。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戈达尔无疑是在寻找对立的答案:是趋向于将两种对立置于永远无法对话的境地、还是寻求对立之间的同一性?以《新浪潮》为名进行影像实验,戈达尔镜头下的“新浪潮”当然不是指涉那场电影叙事的革命,而是在“新浪潮”的形态中追问二元论背后的可能——实际上,答案已经在一句话里显露出来,当侯杰和妥拉托·法佛理尼伯爵夫人一起从湖边回来,那时的侯杰还是侯杰,但是已经不是原先的侯杰,他是“另一个”;妥拉托·法佛理尼伯爵夫人也不再是和身份有关的妥拉托·法佛理尼伯爵夫人,她已经是艾琳娜,在他们都成为了另一个之后,戈达尔给出了一句画外音:“他们感到崇高,沉静,超越了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如同不同的波浪认同同一片海洋……”波浪是前一个波浪或后一个波浪,是近处的波浪或远处的波浪,是掀起了高度的波浪或奔腾之后湮灭的波浪,但无论有着怎样的不同,它们都属于同一片海,只有海包容了一切,只有海收纳了一切,只有海消灭了差别,在同一片海里,不同的波浪就是同一片波浪。
不同的波浪无非是对立的可能,但是在同一片海里它们具有了同一性,这就是戈达尔“新浪潮”具有的象征意义。但是怎样的浪潮会成为“新浪潮”?就如同侯杰如何变成了另一个新的侯杰?妥拉托·法佛理尼伯爵夫人如何又成为新的艾琳娜?在新之前,他们就是不同的波浪,就是拥有了过去和现在的波浪,就是在二元论中可能对立的波浪。戈达尔从一开始并没有构建了这个无法逃离的二元论,反而营造了一种崇高的、沉静的单一世界。电影开场,旁白的声音响起:“这是我要完成的一种叙述:外在世界没有任何事物来干扰我的记忆,我像远远地听到了地球温柔的呻吟 ,从那里出现了一道光芒,它撕裂了地表,阴影让我满足,一株独一无二的白杨木哀伤地立在我身后……”没有外在世界的干扰,没有被湮没的记忆,一道光芒,一株白杨树,尽管哀伤,但它们的单一都属于我,或者说,我属于这个单一的世界。
在旁白中,画面是两匹在树林中的马,之后是一只伸出的手,是一片水草,甚至是一个清洁工,一切看上去都是沉静的,连哀伤也是如此。戈达尔构筑了这样一个诗意的世界,强调的是一种人类出现之前的童话世界,但是,那里有了一个我——我是谁?旁白的声音又代表谁?当我的记忆是完整的,外在的世界是不是已经做好了进入的准备?还有那只手,为什么不是两只手?一只手伸出、张开,它一定在等待着另一只手,等待着另一只手握住。开场的旁白,唯美的画面,其实为那个闯入进来的二元对立世界留出了位置,有人要进来,外部世界要进来,甚至穿透树叶照下来的阳光也要进来。
因为留着位置,所以进来,实际上戈达尔已经将一个童话世界带入了现实,甚至这个现实不是闯入进来,而是主动打开的:庄园,仆人,汽车,《财政日报》,忙碌的生活……一旦世界打开,二元论再也无法避免,一片波浪和另一片波浪变成了不同的存在:它们是富人和穷人,伯爵或者夫人拥有的是富庶的世界,伯爵夫人的父亲还是部长的朋友,他们拥有公司的股权,而那个老仆人一直在练习端盘子的女仆面前强调:“我们是穷人,不要忘了。”这是一种观念的固化,当后来女仆打掉了杯子被嘲笑时,她愤怒地喊道:“我必须学着讨厌你们!”我和你们,嘲笑和讨厌,就是富人和穷人永远的对立状态,因为,“这是一个富人和穷人的时代。”它们也是富人之间的对立,关于股票的涨跌,关于股权的份额,成为这些富人的日常,他们或者在那里争论,或者在私下较劲,他们的世界也是对立的;或者还有朵乐西和丈夫之间的对立,一个在写作,一个在说话,一个在虚构,一个面对现实,在他们谈论股票暴跌的时候,朵乐西写下的那句话是:“我们说和平,但实际上往往是战争……”
| 导演: 让-吕克·戈达尔 |
富和穷,得利和失利,写和说,都在对立的世界里,它们展开,它们侵袭,而真正的对立在戈达尔的世界里,似乎只有两种:男与女,生与死,或者戈达尔正是从这两组关系里探讨从对立趋向同一的可能。一开始的一只手,终于在后来变成了两只手,两只手最后握在了一起,也许这个过程太过直接,并没有如绘画中上帝给予亚当生命的一指那样成为救赎,它仅仅是相遇,仅仅是邂逅:侯杰在路上跌跌撞撞地行走,在戈达尔故意用一堵土墙的前景“遮挡”中,侯杰遭遇了事故,他倒在一棵树下;这时候艾琳娜开着车从路上经过,她发现了倒在那里的侯杰,于是停车、倒车,当她扶起侯杰的时候,看到了他身上的那个十字架项链,“你受伤了吗?”伸出手,接受另一只手,当两只手握在一起,这是女对男、生对死的解救。
但是,“谁会付钱给一个将死的人?”这是戈达尔发出的疑问,这个疑问背后的对立逻辑纷纷展开:“一个女人无法毁掉一个男人,是他自己招来所有的悲剧。”或者是:“她能杀了他。”或者是:“他没有死,是一些人死了。”一只手和另一只手的叙事从此走向了男人和女人的暧昧,生与死的模糊,而这种暧昧和模糊无法建立和爱情、和生命有关的同一性。一只手变成了两只手,他和她在一起,在那个随着戈达尔的摄像机可以移动的不同房间里,在那个被人看见也不被看见的世俗社会里,“在做出承诺之前,我们早已经不忠。”协西勒小姐的话说出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困境,在一起的最后结果就是不能在一起:两只手分开,两只手重新变成了一只手,甚至一只手也不再伸出。
他们在湖边行走,他们钻进了树林,他们划着船出游,艾琳娜跳下水去游泳,但是侯杰却在船上,她喊他下去,他却拒绝了,她伸出手,他也许也习惯性地伸出手,但是他掉了下去——一个是游到了河里,一个是掉进了水里,之后的位置发生了置换,艾琳娜已经坐在了船上,而侯杰却在水里,大约这一片水不属于他,大约他根本不会游泳,在他的挣扎中,她没有伸出那一只救援的手——曾经在他将死的时候她救下了他,现在将死的时候她拒绝救他,于是只有在水面之上伸出的那一只手。死了?也是一种道德的和世俗的力量将他推下了水,也是找不到爱情的力量的脆弱杀死了他,也是“他没有死,是一些人死了”,或者正如朵乐西所写的那样:“我们说和平,但实际上往往是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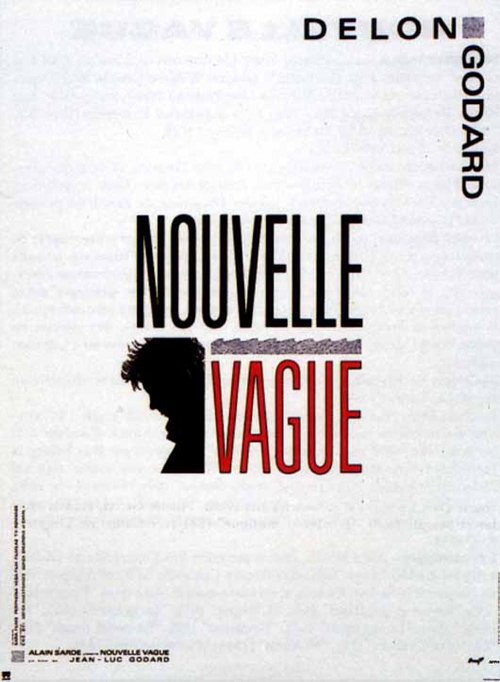
《新浪潮》电影海报
对立的世界无法消弭,是外在的世界闯入了进来,它解构了地球温柔的呻吟,它取消了撕裂地表的那束光芒,它砍掉了那棵独一无二的白杨木:交易还在交易,生意还在生意,签约还在签约,当然不忠还是不忠。在一种社会层面的对立被凸显出来后,戈达尔让理查问了那个问题:“你被一只死蜜蜂蛰过吗?”被问者是侯杰,死去的侯杰?悲剧的侯杰?一只手的侯杰?或者是那个复活的侯杰,已经是国家科学研究院的秘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从死去到复活,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呈现,它在戈达尔的寓言里成为另一只手的游戏:交易还在交易,生意还在生意,签约还在签约,不忠还是不忠,侯杰听到艾琳娜在说:“我没有看到你,我不会被迫去爱你,在拯救我生命时,你偷走了我的身体,我对你,用爱情来招待。”这真的是复活之后的爱情?当侯杰现身的时候,艾琳娜用那块白布蒙住了他的嘴,在艾琳娜吻向他的时候,他不是用力挣脱了?而当他们再次划着船出去,艾琳娜却被他拉下了水,她在挣扎,她在呼救,但是他的那只手始终没有伸出来,当水终于没过了她的头顶,死亡的一幕再次发生。
他死了,她死了,他没有死,是一些人死了,她没有死,也是一些人死了,就像蜜蜂,在愤怒而死中蛰了人,它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和死具有了同一性。但是这死蜜蜂不再是以前的那只,连问题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在这个从对立走向同一的过程中,戈达尔找到了一个代言人,那个清洁工看见了一切,言说了一切,他其实就是戈达尔自己:他说:“永恒的光超过了时间和空间。”他说:“一座花园不曾被盖得像散文一样,它总是需要修改它的图样和颜色。”他说:“允许事物听到他们自己,只有在沉默中,才像他们真正听到的。”他说:“这里的草地都属于我吗?没有我还是草地吗?”他自言自语,他自问自答,他是话语的出发点也是回归点,他是问题的起点也是问题的终点,他就是自己,是一道光也是一片阴影,是一只手也是另一只手,是一片波浪也是另一片波浪,就像真理,就像爱情,就像生命,超越过去和现在,超越生与死,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男人和女人,如同不同的波浪认同同一片海洋,而且,“这不是同一个,这是另一个……”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744]
思前:“无人称”的秋天正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