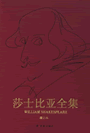2022-10-07《莎士比亚全集》: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演戏本来是一片假,列位看官不用惊诧怎么那各地的人民都讲着同一的方音,这为的是观听便利,不是俺们失于算计。
——《泰尔亲王配瑞克里斯》
它是全本集合的一种汇聚:根据1974年版和1997年版《河滨莎士比亚全集》为据,收录已发现的莎士比亚全部作品,共39个剧本和长诗、十四行诗以及书情书,包括“河滨版”1974年收入、曾经引起学界争议的《两个高贵的亲戚》《爱德华三世》及一首长诗,以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段,包括被认为“不训雅”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这是文本厚度的一种展示,八册“全集”的修饰语是:真正全集、硬壳皮面精装、70g胶版纸印刷、内芯线装加固……4272页,摆放在桌子上基本上抵达了书柜最底部的横板,不是天花板却已经占满了书桌向上的可能空间,这也是近年来读过的最厚实的文本;这是对喜剧高峰的一次观礼,他是“英国戏剧之父”,本·琼斯称他为“时代的灵魂”,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被称为了“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
高度是写作者的高度,也是阅读者的高度,可能穷极一生都应该在这文本和人文的世界里反复阅读,但粗略的阅读在一次性完成时,只是花费了国庆假日的七天,虽然也是全天候,但是这七天的进入和抽离是不是可以走近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或者时间本身作为标记在写作和阅读的差异性中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即使返回到文本本身,返回到舞台本身,16世纪的莎士比亚不正是在封闭的戏剧文本和戏剧舞台之上创造了不断被压缩和扩张的时间?时间作为道具的存在,正是莎士比亚用想象力创造的结果,所以,文本并不只是被汇集成固定高度和可计算页码的文本,舞台当然也并非是让演员出演、打开和落下帷幕作为戏剧开始和结束标志的舞台。
于是英国14世纪的诗人约翰·高渥作为长诗《情人的自白》的作者进入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并以解说剧情老人的身份参与了戏剧的演出,“ 从往昔的灰烬之中,来了俺这白发衰翁,唱一支古代的曲调,博你们粲然的一笑。”高渥在朗诵着自己的诗歌,又在为莎士比亚解说戏剧,14世纪和16世纪合二为一,而时间便在这种合一中成为了舞台的一个道具:《泰尔亲王佩瑞克里斯》是莎士比亚晚期传奇剧的代表,和早期浪漫喜剧不同之处,除了戏剧的基调、剧情的安排之外,就是时间的处理,浪漫喜剧的故事只是发生在几天或几个月,只要相恋的人终成眷属,喜剧便在喜庆中结尾,但是在高渥解释的这出传奇剧中,故事覆盖了近六十个年头,剧终时不仅女儿已经长大成人,而且也到了婚配的年轻。这种时间上的不一致正是对古典主义的一种颠覆,“三一律”已经明显不属于莎士比亚后期戏剧所追求的原则。
《冬天的故事》作为莎士比亚悲喜剧的代表,也完全打破了“三一律”,它的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间竟隔了十六个春秋,“十六个春秋早已默无声息地过度,这其间白发红颜人事有几多变故;我既有能力推翻一切世间的习俗,又何必俯就古往今来规则的束缚?”这句话或者就是莎士比亚面对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所发表的宣言,和《泰尔亲王配瑞克里斯》一样,莎士比亚引入了与高渥一样的解说者,这不过这个出现在第四幕的引子里的解说者不是诗人,而是被扮演的“时间——时间不仅仅是舞台上的道具,而且是被扮演的“演员”。除了作为“演员”的时间在述说之外,还有赫美温妮的“雕像”也在戏中说话,并缓步走向了神坛,让读者体验到的不仅仅是惊喜,更为夫妇、母女的团聚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泰尔亲王配瑞克里斯》的六十年,《冬天的故事》中的十六年,都是莎士比亚打破古典主义“三一律”规则的实践,而这种打破更是对于剧中人命运的一次解说,“她此后的命运不久时间便会显明。”或者从这条时间线索可以阐释莎士比亚对戏剧变革的巨大意义:一方面是对形式上的打破儿开始的解构,另一方面则是对命运出路进行的建构——而这一切完全可以从收入全集的第一部戏剧《错误的喜剧》中找到诸多的线索。首先,这是莎士比亚在25岁时写的一部喜剧,当时的他从故乡来到伦敦不过两年,莎士比亚模仿了罗马喜剧家
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并采用其他一些材料,创作了这部具有英国味成分的喜剧。在这部喜剧中,莎士比亚按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意见遵守“三一律”:剧情保持一致性、发生在同一地点、在一天之内——可以说,这时候的莎士比亚还是一个传统的古典主义者。
但是正因为从传统的起点出发,莎士比亚完全有更大的空间完成对传统的变革甚至颠覆,这便是莎士比亚对“舞台论”的解构和建构。在《仲夏夜之梦》这一焕发着梦幻色彩的喜剧中,莎士比亚在形式和主题上完成了对“舞台论”的实践,它采用的事“戏中戏”的结构,在公爵和公爵夫人结婚的晚上,众人表演了一出插戏,戏的名字是《最可悲的喜剧,以及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最残酷的死》,这是奥维德《变形记》里的故事,故事直接讲舞台变成了仲夏夜的森林里,小精灵、小仙女展示着曼妙舞姿,舞台变成了充满魅力和魔力的世界。不仅舞台变换创造了另一个场景,戏中的人物也具有了双重身份,昆斯是木匠,在戏中戏中饰演念开场白的人,波顿是织工,在戏中戏中饰演的是皮拉摩斯,还有那些补锅工、裁缝、修风箱者,都摇身一变成为了戏中戏中的墙、月光、狮子等,将奥维德的《变形记》在舞台上实现了“变形”,更是完成了对于命运的一种解读,忒修斯说:“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最坏的只要用想象补足一下,也就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那么不管是戏剧本身还是戏中戏的演绎,都指向了人生,而这人生在这里便成为自己的主宰,“这出粗劣的戏剧却使我们不觉打发了冗长的时间。好朋友们,去睡吧。我们要用半月工夫把这喜庆延续,夜夜有不同的寻欢作乐。”
《皆大欢喜》被哈兹里特誉为莎士比亚“最理想的”一部“田舍剧”,在这部喜剧中,莎士比亚则通过“收场白”这一形式丰富了表现手法,戏中的罗瑟琳说:“要是好酒无需招牌,那么好戏也不必有收场白;可是好酒要用好招牌,好戏倘再加上一段好收场白,岂不是更好?”在这个“收场白”中,莎士比亚借罗瑟琳的口又说到了戏剧扮演的意义,“假如我是一个女人,你们中间只要谁的胡子生得叫我满意,脸蛋长得讨我欢喜,而且呼出的气味也不叫我恶心,我都愿意给他一个吻。”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只要善良无私,只要忠于爱情,就是最好的人生之戏,所以罗瑟琳所说的打破伊莉莎白时代舞台上女角皆用男童扮演的做法,即使对舞台演出的丰富,也阐释了戏剧最理想的男女关系,即“皆大欢喜”,“为了我这一慷慨的奉献,我相信凡是生得一副好胡子,长得一张好脸蛋,或是有一口好气味的诸君,当我屈膝致敬的时候,都会用掌声向我道别的。”
从《仲夏夜之梦》的戏中戏结构,到《皆大欢喜》中收场白对于角色的置换,从《亨利五世》中剧情解说人的出现,到《亨利八世》中“插曲式结构”的运用,从《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展示暴力过程的“残酷戏剧”到《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像电影蒙太奇式的时空转变,莎士比亚对于戏剧形式的突破和变革,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但是“舞台论”并非仅仅是形式意义的:舞台是戏剧演出的舞台,是展现故事的舞台,是演员扮演角色的舞台,但是舞台不只是舞台,它以更具内涵、更有开拓性、更富象征意义而成为一种人生甚至人性的解读。《裘利斯·凯撒》的真实性是基于“舞台不过是舞台”这一原则,但是当凯撒作为权力统治者的暴君最终遇刺而倒毙在舞台上的时候,舞台不再是舞台,因为自由和解放成为人们的期待:舞台上扮演勃鲁托斯的演员说:“照这样说来,死还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都是凯撒的朋友,帮助他结束了这一段忧生畏死的生命。”凯撒的思如何是一件好事?他弯下腰去说:“让我们把手浸在凯撒的血里,一直到我们的肘上;让我们用他的血抹我们的剑。然后我们就迈步前进,到市场上去;把我们鲜红的武器在我们头顶挥舞,大家高呼着:‘和平,自由,解放!’”此时扮演布鲁托斯的演员和扮演众党徒的演员将手浸在血泊中,血是故事中的血,也是舞台上的血;扮演凯歇斯的演员说:“好,大家弯下身去,洗你们的手吧。多少年代以后,我们这一场壮烈的戏剧,将要在尚未产生的国家,用我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表演!”布鲁托斯的那句话还在舞台上,还在故事里,但是凯歇斯的话则将故事变成了舞台的一部分,或者将舞台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他提到了戏剧,提到了表演,正是这种间离的效果既把凯撒的历史搬上了舞台,又让舞台变成现实的存在,之后的勃鲁托斯也进入到舞台戏剧中,“凯撒将要在戏剧中流多少次的血,他现在却倒毙在庞贝的像座之下,他的尊严化成了泥土!”凯歇斯继续深化舞台论:“后世的人们搬演今天这一幕的时候,将要称我们为祖国的解放者。”
| 编号:H78·2200218·1629 |
舞台不过是舞台,舞台却不再是舞台,刺杀了凯撒,暴君覆灭,手浸在血泊之中,这一切将舞台隔离在历史和故事之外,当戏剧指涉了戏剧,舞台是现实之一种。译者朱生豪将此看做是一种“幻觉”,尤其是对于观众来说,“这时剧场四壁悄然后退,时间的河道拓宽了,淹没了舞台,吞噬了观众席;观众的心越过时空阻隔同古代英雄一起搏动,他们平凡琐碎的生活得到了升华,变为历史的一个瞬间。”所以他认为这种超幻觉的逼真效果和写实主义的真实,“是不依赖模仿的真实,是以‘假’为真的真实,是莎士比亚式的真实。”舞台变成了假的真实,莎士比亚的真实,超幻觉的真实,它也成为了戏剧指涉现实、指涉命运、指涉人性的真正舞台。而看得见的舞台以及戏剧本身则提供了一面关于人性、权力、命运的镜子,在莎士比亚的镜子中,照见的就是人生,“最好的戏剧也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缩影”。
而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一类戏剧直接呈现了“镜子”的功效,那就是历史剧。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的代表作便是两个四部曲:以最早创造的《亨利六世》上中下三篇加上《理查三世》构成了第一个四部曲,《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两篇加上《亨利五世》则是第二个四部曲——但是从历史本身来看,第二个四部曲所描写的历史出现在第一个四部曲之前,《理查三世》写了亨利四世篡夺王位、理查二世被废黜的历史,接下去才是《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再接第一个四部曲的《亨利六世》。除了两个四部曲之外,莎士比亚还创作和了大历史有关的《约翰王》《亨利八世》《爱德华三世》,它们共同构成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序列,也以历史为镜像,折射出现实中的戏剧矛盾和冲突。
《亨利六世》分上中下三篇,约完成于1592年,上篇描写的是大将塔尔博特在法国奋勇征战的情况,两个家族的不合导致救援不至,使这位战功卓著的大将战死沙场,上篇一开始便突出了葛罗斯特公爵和温彻斯特主教之间的矛盾,而在公园一幕中我们看到了“玫瑰战争”的来龙去脉,此剧结尾时,萨福克带着玛格莱特来到英国,亨利沉湎于她的美色,毁掉婚约,娶玛格莱特为后,这样就导致内部矛盾的复杂化,为第二篇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中篇所烘托的是葛罗斯特的失败和约克公爵的胜利,葛罗斯特早已成为那些觊觎王位的人特别是约克公爵的眼中钉,葛罗斯特妇人甚至还求神弄鬼一心想让丈夫戴上王冠好让自己成为第一夫人,最后导致了葛罗斯特的覆灭,雷纳和他徒弟的决斗,凯德的叛乱、萨福克与王后的恋爱,红衣主教和葛罗斯特的敌对等戏剧冲突的安排都注定了葛罗斯特的失败和约克的兴起,第一幕第一场中约克的独白道出了他的野心,也暗示了戏剧的走向;下篇将“玫瑰战争”推向了高潮,两大家族开始进行力争我夺的战斗,尤其是第三四幕写道十年战争,正义全无,荒淫、狡诈、残杀无辜,使得整个英国陷入了极大的混乱,此时的葛罗斯特脱颖而出,他就是后来的理查三世。
《亨利六世》虽以约克家族的胜利结束,但王权的问题并未解决,兰开斯特家族的势力犹在,新王即将由怪物理查取而代之,他的血腥统治不可能维持久远,更大的动乱又在酝酿之中。在《理查三世》中,莎士比亚赋予这个脱胎于中世纪道德剧中的“邪恶”角色更多光彩和美丽,朱生豪认为,“这个角色穷凶极恶,但绝不脸谱化。他极丑,但机智聪明,胆识过人,性格丰富,是莎氏笔下最成功的角色之一。”在这个复仇戏中,对玛格莱特王后的设计也是一大的亮点,莎士比亚改变了历史上她在法国的记载而将她送到了英格兰,并成为复仇女神的代言人,使得她在本剧中的杀戮和《亨利六世》的冤仇连成一片,她的寓言式诅咒让一连串谋杀变成了报应,尤其以第五幕的冤魂戏作为终结,又和《亨利六世》三部连成一体,形成了完整的戏剧结构。在第二个四部曲的《理查二世》中,莎士比亚塑造了矛盾复杂的君王理查二世,他在前期是昏庸暴虐的君主,后面则让人同情,连篡位的亨利四世对理查之死变大了痛心,“从我这罪恶的手上涤去血迹”。莎士比亚的处理显示了他的人文主义观点,理查的软弱、伤感、敏感和带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也注解了亡国之君的惨痛人生。之后的《亨利四世》上接《理查二世》,下接《亨利五世》,从波令勃洛克篡夺理查二世王位成为亨利四世,至哈利亲王继承王位为亨利五世,远征法兰西取得阿金库尔战役胜利,娶法国凯瑟琳公主做王后为止,四部曲所描写的是政权得失和民心相悖的关系,正如哈利亲王斥责王冠的话,“你吞噬了戴上你的人”,一句话点破了一切封建王朝面临的这个无法解开的死结。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更像是史诗,作为伊丽莎白时代英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亨利五世在与法国人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当时的英国还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所以亨利在莎士比亚的心目中是一位“理想君王”。
君权、欲望、爱情的争斗,以及暴虐式的君王、理想型君王,都反映着莎士比亚的创作观,两个四部曲的“历史剧”,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镜子”重要的载体,对历史的重现,舞台就是一面镜子。而除了“历史”事件之外,历史也是舞台的一种延伸,尤其在《亨利四世》下篇,莎士比亚运用了更多的戏剧象征,比如剧中有演员叫“谣言”,他的身上绘满了舌头,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记》记述的谣言形象是个满身眼睛、耳朵、舌头的怪物,莎士比亚将这一形象具象化,“造成这误会的是谁?我,只能是我。谣言是一只风笛,吹响它的是臆测、妒忌和猜想。”谣言在舞台之上如此表达自己。此外还有“狭陋”“影子”“肉瘤”“菲薄”“赛聋士”,它们或者是抽象的存在,或者是一种象征,莎士比亚都让它们走上舞台变成了演员,从而将历史舞台化,最后则是由舞蹈演员跳舞来饰演更为抽象也更具有舞台性的“尾声”,而且他最后就是向观众说话:“我的舌头累坏了,腿也累坏了,我祝诸位晚安。”
实际上,在这里,历史已经退到了后面,而舞台则提供了隐喻性传达的空间,这是“镜子”的一种丰富,历史是最原始的一面,舞台则折射出更戏剧性的一面。在《亨利五世》中,对历史剧形式的革新则是出现了剧情解说人士,“啊!但愿能如火焰一般升腾的缪斯女神,带领我们登上光辉灿烂的想象的天堂!以王国为舞台,由君主们来演出,让帝王们来观看那宏伟的场面!然后,那英勇善战的亨利,才会显出他的本色,以战神的姿态出现;在他的脚后跟,是饥馑、刀剑和烈火,像用皮条系着的三头猎犬,蹲在那里只等他下令出动。”剧情解说人解说着法兰西的辽阔战场,解说者将士的头盔,解说着英格兰,通过解说完成了场景的转换,实现了剧情的推进,更是通过解说表达了戏剧创作、戏剧演出等属于本体论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这些与这个伟大故事相比非常渺小的人,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吧。”解说者似乎在释放着观众的想象,“凭借想象的翅膀,我们的场景飞也似的转移,动作的速度就跟思想一般快捷。”最后也回归到和观众的互动中,“那段事,本剧院常常演出,承蒙观赏,盼此剧也能得到诸位赏光。”《亨利八世》也一样,除了历史的再现之外,莎士比亚运用了“插曲式的结构”,当然还有解说者,他所说的也是关于戏剧本体的:“我上台可不是想逗诸位一笑;因为这出戏内容严肃、十分重要,庄严、崇高、感人,充满壮丽和悲伤,高贵的场面能使人热泪盈眶。”
历史为戏剧提供了一面和历史不一样的镜子,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最后也回到了和《裘利斯·凯撒》一样的“舞台论”中,它解构了“舞台就是舞台”的封闭性,在超幻觉的逼真效果中达到了不依赖模仿的真实,实现了以“假”为真的真实,成为莎士比亚指涉比历史更广泛的人性、命运、权力。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这种以假为真的创作观是对戏剧手段的突围,更在于对主题的阐述,历史和现实,舞台和故事,就像两面,它从来不是截然分来的,它是现实的历史化也是历史的现实化,它是故事的舞台化也是舞台的故事化,它是我也是非我,它是他者也是自己,而莎士比亚几乎完美地将两者契合在一起,即使可以分开来是两面,也可以合一成为对真实命运的写照。
再次回到《错误的喜剧》这个原点,从这部剧中可以看到莎士比亚此后很多创作手段和主题的影子。公爵对叙拉古商人伊勤说:“自从你们为非作乱的邦人和我们发生嫌隙以来,你我两邦已经各自制定庄严的法律,禁止两邦人民的一切来往;而且有谁在以弗所生长的,要是在叙拉古的市场上出现,或者在叙拉古生长的,涉足到以弗所的港口,就要把他处死,他的钱财货物全部充公,悉听该地公爵的处分,除非他能够缴纳一千个马克,才可以放他回去。”两邦之间是死对头,所以矛盾从一开始就走向极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族矛盾就是如此;但是只要叙拉古商人缴纳一千个马克就可以被放,这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要以“一磅白肉”作为惩罚手段,也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当然,在这个剧中,最重要的则是“孪生性”,大安提福勒和小安提福勒斯是伊勤和爱米莉亚的孪生子,大德洛米奥和小德洛米奥则是侍奉安提福勒斯兄弟的孪生兄弟,“说来奇怪,这两个孩子生得一模一样,全然分别不出来。”孪生性具有的相似性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具有的便是反射意义,是自己照见了另一个自己,也是另一个自己照见了自我。
因为“全然分别不出来”,所以寻找的过程就像在大海里的一滴水,“结果连自己也迷失了方向”,戏剧中的怀疑、猜忌、误解甚至嫉妒全由此展开,更重要的是,迷失了寻找的方向,就是迷失了自己,大安提福勒斯在旁白时说的话可以看做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一个线索:“我是在人间,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是睡是醒?是发了疯?还是清醒?”因为自己被别人当成了别人,包括爱人、包括朋友、包括亲人都对他指责,所以大安提福勒斯开始自我怀疑: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是睡着还是醒了?是自己还是别人?“我是我自己”甚至成为了一个难以确认的主题,于是一切进入到了公爵最后的疑问中:“这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另外一个的魂灵;那两个也是一样。究竟哪一个是本人,哪一个是魂灵呢?谁能够把他们分别出来?”
谁是本人谁是魂灵?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解读为:如何才是自己?如何才能确定是非我?于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化或者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就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面具论”,另一种则是“鬼魂论”,它们都是在面对迷失中的自我拯救,都是为了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驯悍记》作为莎士比亚早期喜剧之一,男主人公披特鲁乔以悍制悍,驯服了脾气很坏的大小姐凯萨琳娜,和她成婚,而妹妹比恩卡则温柔娇嫩,几个男青年向她求婚就用了乔装改扮的方式和她接近,这里就有了“面具”,它也是以“演戏开始”的戏中戏形式出现的,特兰尼奥对少爷卢生梯奥说:“大概这里的人知道我们来了,所以要演一场戏给我们看,表示他们的欢迎。”而卢生梯奥利用演戏为自己戴上了面具,“所以我想这样:你就顶替我,代我主持家务,指挥仆人;我自己移名改姓,扮作一个从佛罗伦萨、那不勒斯或是比萨来的穷书生。”在《维洛那二绅土》中,这个戴上面具的人则是让爱人回到自己身边的裘丽亚,“为了避免轻狂男子的调戏,我要扮成男装。”裘丽亚也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第一个女扮男装的勇敢女性;《无是非中》中,关于爱情中的善和恶、真与假都在一场戴面具的舞会上展开,机智、开朗的贝特丽丝表面上认同独身主义,她也想在假面舞会上装扮成希罗对那些少年公子进行反击,但没想到自己也获得了爱情,一切的阴差阳错造成了希罗的死,但是希罗的那句话却也指出了面具论的意义,“当我在世的时候,我是您的另一个妻子;当您爱我的时候,您是我的另一个丈夫。”
“面具论”当然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真正变成了一出悲剧,两个世代为仇敌的家族,当然不会允许爱情发生,所以他们成了戴面具的人,那场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爱的舞会就是一场假面舞会,假面舞会开启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必须戴着面具,“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演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控制着这面具的是家族的权力,是父母的嫌隙,甚至只是简单的一个名字:朱丽叶在罗密欧面前说:“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不管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这名字的背后就是无法逃离的命运,但是他们也努力摘掉这个面具呈现出真实的一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也不愿再姓凯普莱特了。”他们秘密约会,他们吃下毒药昏迷,就是为了逃离命运的操控,就是为了能最后在一起,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看起来是偶然,却也是必然,“嘴唇,啊!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
“面具论”是自我迷失的写照,是命运被束的无奈,是权力控制的人生,莎士比亚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进一步的表现则构成了他的“鬼魂论”:哪一个是本人?哪一个是魂灵?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似乎都在鬼魂的世界里寻找自我,却又都在鬼魂里失去了自我。《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在丹麦城堡厄耳锡诺中遇到父亲的鬼魂,是具象的鬼魂,而且父亲告知了篡权和乱伦的秘密,于是哈姆雷特开始了“复仇”,“上帝啊!上帝啊!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这种复仇带着哈姆雷特自身对命运的悲剧性看法,“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这是对母亲的看法变成了对女人的诅咒,“ 丹麦是一所牢狱。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是对丹麦的谴责变成了对世界的抛弃,最后在“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中,哈姆雷特选择了极端性的复仇,看起来这是哈姆雷特对命运的一次操控,但实际上却是失去了掌控,使得命运以更加非理性的方式发展成为了一出悲剧。
哈姆雷特对于命运无力的那句话就是:“我也知道你们会怎样涂脂抹粉;上帝给了你们一张脸,你们又替自己另外造了一张。”上帝造了一张脸,上帝就写好了每个人的命运,但是自己又另外造了一张,这不是对命运的把握,而是最终失去命运,甚至生命。那剑中含着毒药,在刺向仇人也刺向朋友和自己的时候,哈姆雷特也变成了无法主宰自己的鬼魂,鬼魂只有一个名字:疯狂,“既然是这样,那么哈姆莱特也是属于受害的一方,他的疯狂是可怜的哈姆莱特的敌人。”《奥瑟罗》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份有关,“异族人”,即使他立下了战功,他的这一身份无法被忘记,也无法让自己忘记,所以妻子苔丝狄蒙娜的那块手帕轻易变成了嫉妒的理由,旗官伊阿古是坏人,如果伊阿古不这样做,奥赛罗一样也会成为自己疯狂的牺牲品,正如伊阿古所说:“一方面那样痴心疼爱,一方面又是那样满腹狐疑,这才是活活的受罪!”因为奥赛罗本身就带着面具,因为奥赛罗本来就看不见自己,因为奥赛罗本身就是疯狂,当最后妻子死去,“我的勇气也离我而去了,每一个孱弱的懦夫都可以夺下我的剑来。可是奸恶既然战胜了正直,哪里还会有荣誉存在呢?让一切都归于幻灭吧!”而那一剑将自己刺死,也是最后撕下了面具,但是又有何用?
《李尔王》是被戴着面具的两个女儿所迷惑,不戴面具的科迪莉娅没有说出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只是爱本身,“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义务,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却被李尔王认为是不孝的人,剥夺了她该有的那份财产。而也是在这样的迷惑和误解中,李尔王也变成了戴着面具而迷失了自我,他问弄人,“这儿有谁认识我吗?这不是李尔。李尔是这样走路,这样说话的吗?他的眼睛哪里去了?,他的知觉衰退,要么他的神志麻木了。”这个关于“我是什么人”的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李尔的影子。”在荒原里,李尔迎着风迎着雨,终于醒悟过来,“我是一个所受惩罚超过所犯过失的人。”但是疯狂没有停止,他最后听到的依然是科迪利娅最为悲剧的答案:“啊,我亲爱的父亲!但愿我的嘴唇上有康复的灵药,让这一吻修复我那两个姐姐加在你身上的暴烈的伤害吧!”悔恨无用,绝望无果,在被面具蒙蔽的世界里,被疯狂主宰的命运中,镜子也早已不在,“借一面镜子给我,要是她的气息还能够在镜面上呵起一层薄雾,那么她还没有死。”
《麦克白》里的鬼魂是那些发出预言的女巫,是死后的班柯,砸碎怀中婴儿脑壳的美妇人、悬在半空的匕首、人肉和癞蛤蟆熬成的魔汤、面容惨白狞笑着的小王子们,但是真正的鬼魂还是麦克白自己。成为君王的预言一开始就夹杂着恐怖,“想象中的恐怖远过于实际上的恐怖;我的思想中不过偶然浮起了杀人的妄念,就已经使我全身震撼,心灵在猜测之中丧失了作用,把虚无的幻影认为真实了。”它让麦克白迷失,而他就是沿着这条迷失的路毫不犹豫地走了下去,得到权力是一场梦,失去权力也是一场梦,只是麦克白在这场梦中不愿醒来,他戴着面具而活,也戴着面具死去,“除非勃南森林会向邓西嫩移动,我对死亡和毒害都没有半分惊恐。”就是一个早就被注定、绝非是预言的现实,头颅落地,连同迷失自己的面具也破碎。
“演戏本来是一片假”,但是不管是“舞台论”还是“历史论”,不管是“面具论”还是“鬼魂论”,莎士比亚对于戏剧“假戏真做”的一次次探索,是在展现暴虐、残忍、压迫、不公,是在表达嫉妒、迷失、疯狂,假戏真做实际上每部戏都是真实的,即使在历史中,即使在舞台上,即使戴着面具,即使成为鬼魂,“演戏的都不能保守秘密,他们什么话都会说出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0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