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11《东西》:以拼贴应许着我的沉默

也斯是谁?陌生者如我,没有读过一本也斯所著的图书,也没有看过和他相关的文章,一个处在阅读甚至了解空白处的名字,自然会有“他是谁”的疑问,但显然导演黄劲辉没有想到向陌生者如我去介绍也斯,他拍摄的纪录片是要为那些读过他的书、了解他的人的观众去展示也斯,甚至是为了让那些听说过也斯对也斯文学和人生怀着某种渴望的人介绍也斯——这便有了一个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无形的沟壑:为什么一部纪录片要框定观众的范围?
其实对于“也斯是谁”的疑问,完全可以从相关的介绍中获得。来自“百度百科”的介绍是关于也斯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关于他简略的人生:“1949年,到香港。四岁,丧父。20岁,开始专栏写作。70年代,参与编辑《中国学生周报》。在香港浸会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任职报社和当中学教师。1978年,赴美攻读研究生。1984年,获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担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任教文学与电影、比较文学、香港文学、现代文学批评、中文文学创作等科目。2010年,向媒体证实患上肺癌。2012年,香港书展特邀也斯先生为年度作家,表彰他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文坛的卓越成就和贡献。2013年1月6日,在香港去世,享年65岁。”以也斯来到香港为起点,以患病去世为终点;另一个则是关于他笔名的来由:“‘也斯’为两个无意义字的组合。据他表示,过往人们使用的笔名本身,常带有一定意思,令人未看作品时就已对作者有一种感觉。于是也斯希望能突破这一点,使用本身没有什么意思的字作笔名。于是选了文言句中常见的两个虚词作笔名。”
网络上的百科,相关的页面,都能呈现一个标签化的也斯,但是正如他的笔名一样,“也斯”完全是一种扁平化的存在,完全是没有实体的结合,那么黄劲辉通过纪录片是不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也斯,一个具体的创作者?实际上纪录片之拍摄计划和最后成品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反差,2009年启动纪录片拍摄时,黄劲辉用镜头记录也斯,尤其是那次苏黎世之行:在雪山之下,也斯有着登攀的渴望,来回六个小时他不顾自己身体原因和天气突变的可能,执意坐车登上山,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漫步在街头,他回忆1988年第一次来苏黎世的情景,那篇《苏黎世的栗子》是他写下的关于“中立的美学”;在友人家里聚会、饮酒、高谈阔论,去苏黎世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头衔……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也斯最后一次旅行,“2013年也斯已经离世……”黄劲辉用旁白说出了最大的遗憾。
| 导演: 黄劲辉 |
本来用镜头记录也斯,那里的也斯是鲜活的,是具体的,甚至就是一个充分有着主体性的“我”,他的快乐,他的多面,展现的是拥有丰富多彩生活的一面。但是当2013年也斯逝世,这部纪录片没有真正完成,所以黄劲辉为了让纪录片被完整记录,于是他选择了另一种角度,“究竟有多少块拼图,才可以接近意味作家的内心?”从这个问题入手,黄劲辉开始转变视角,把对也斯的纯粹记录转变为友人对他的回忆,而这个视角也似乎符合也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若你想认识我,就去认识我的朋友,在我朋友身上都可以看到我的影子。”朋友的影子投射在也斯身上,也斯的生命体现在朋友的回忆里,这似乎是一种对于逝去的弥补,但是,朋友只是影子,朋友只是拼图,于是当黄劲辉将朋友变成也斯的另一面,他始终无法真正还原也斯,他只能在朋友的回忆和点评中制造关于也斯的影子,拼贴关于也斯残缺的故事。
这或者是致命的,因为黄劲辉在某种意义上抽掉了作为主体之“我”的存在,借用也斯的一句话就是:“我敬佩你的沉默,把苦味留给自己……”那是在岭南大学的也斯纪念会上的一句话,当众友人向他的遗相鞠躬,已逝的生命便成为沉默的一部分,即使友人还在,影子还在,拼图还在,也斯依然也是沉默的。从回忆性结构出发,黄劲辉似乎动了一番脑子,以《东西》为片名,他至少从三个层面构筑了也斯:《东西》是也斯的一本诗集,出版时署名为“梁秉钧”——黄劲辉就是以这本书推出纪录片的片名;“东西”当然也是一种物的呈现,黄劲辉就是通过也斯的“东西”来构筑起他的人生和性格,采用章回体,黄劲辉选择也斯的东西包括也斯的鞋,这是一种“游”的写照,也斯喜欢旅游,他的足迹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他的寻访就是在发现诗意,苏黎世无疑是他游走的最后一站,黄劲辉说他“游于游戏,游于生活”;也斯的大衣,关键词则是“食事”,其中包括《苏黎世的栗子》《马赛的鱼汤》《试酒》,对食物之关心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将“食事”变成了一种本土的记忆,并将本土记忆与文化相结合;也斯的眼镜,关键词则是“越界”,也斯不仅爱好文学,也在厨艺、美术、舞蹈等方面展示了也斯的多元性,越界其实是融合;也斯的手表,关键词是“人间滋味”,用手表连接起时间,用时间感悟人间滋味,黄劲辉将其解读为人生的迁徙:从1984年-2013年居住的加宁大厦,逆向时间回溯,则是1974年半-1984的金马大厦、1972-1974的永德大厦,以及童年居住的天后琉璃街向南楼,通过儿子梁以文对旧居的走访以及朋友黄淑娴的回忆,串联起也斯人生中不同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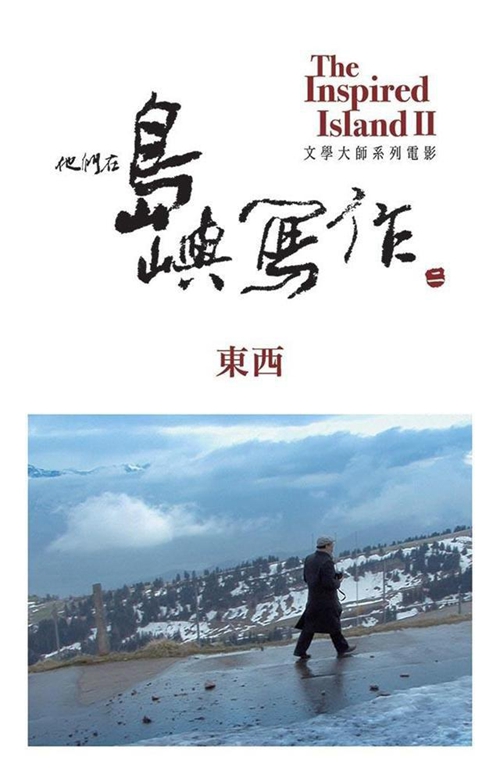
《也斯》电影海报
也斯的鞋,也斯的大衣,也斯的眼镜,也斯的手表,这些也斯的“东西”背后是关于游走、食事、越界和人间滋味的故事,他们构筑了也斯的人生故事。这是关于“东西”的第二层含义,而从这个第二层含义出发,又构建了“东西”更多的隐喻:东西是东方和西方,也斯就是将东西方文化交融在一起、从事跨文化写作和研究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斯的“东西”正体现了他的国家化视野,这是一种多元的呈现,或者和他遍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一样,他的散文、诗歌、小说和评论,他的美食、服装、摄影、舞蹈,他身上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性,都成为解读也斯的一块拼图、一道影子。但是无论是成为作品的《东西》,还是鞋、大衣、眼镜和大衣组成的“东西”,或者他写作上跨越式的“东西”方写作,“东西”所呈现的应该是以也斯为主体的那个我,即使沉默,也是纯粹的我,独立的我,苦味留给自己的我。
但是,在黄劲辉的镜头下,也斯的我终于成为了众人眼中的“他”,从梁文道开始,也斯似乎就活在不同朋友的评价里:他们是翁文娴,“也斯是香港战后第一代本土作家……”是鸿鸿,“他背向了台湾作家……”是苏黎世大学教授洪安瑞,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沈双,是时装设计师黄惠露,是美食家萧欣诺,是刘以鬯,是痖弦,是妻子吴煦斌,是儿子梁以文……每每谈及也斯的文章和图书,说到也斯的创作和生活,几乎每个人都沉浸在回忆中,都在评说。在140分钟的纪录片里,他们的言说占据了三分之二,而正是他们言说着一个不同的也斯,多元的也斯,片面的也斯,局部的也斯。这当然是一种喧宾夺主,他人的回忆和评说应该是一种点缀,一种补充,作为主体的存在,也斯之我是镜头下的也斯,是说话中的也斯,是行文中的也斯,是创作中的也斯,从文和人最本质的东西入手,也许才可能还原也斯。但是,当也斯变成影子,变成拼图,也斯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一种存在,甚至关于也斯的“东西”都被他们拼贴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斯也变成了被言说的“东西”,再无完整的也斯,再无具体的也斯,再无鲜活的也斯,于是,也斯真的变成了沉默的人。
“也斯是谁?”终究成了一个被肢解而没有答案的问题。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