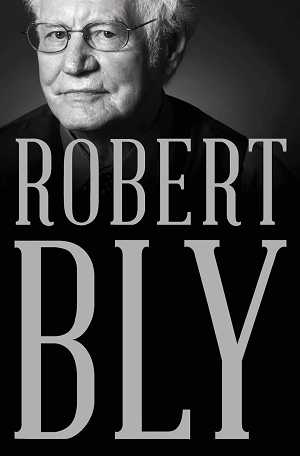2023-03-19《对驴耳诉说》:带我进入我不在之处

罗伯特,这首诗里的一些意象正贴切。
也许就同任何那些人所能做的一样好
他们依然住在欲望的老客栈里。
——《柏拉图有许多》
罗伯特正在写诗,罗伯特正在谱曲,罗伯特变成了一条湿润的舌头,让“精妙的思想”从此滑入世界——滑入的世界里有什么?有坚称只有一个早晨的哀鸽,有向第一块木板尽忠的钉子,有对着一千颗行星啼鸣的乌鸦……哀鸽之早晨,钉子之木板,乌鸦之啼鸣,都是一种单一的存在,但是这个世界需要呈现的是一种多,就像太阳“只有一种燃烧的智慧而柏拉图有许多”,一和多构成的世界也是由舌头和思想构成,舌头如何说话?又如何变成思想而滑入?
《柏拉图有许多》,罗伯特就是写下了这首诗,他让“启明星凌越于一级翅膀的鼓动”而展现多彩的世界,他让精妙的思想从一条湿润的舌头滑入,但是一和多,也体现着某种隔阂:它是舌头的言说和思想的沉默,它是舌头的欲望和思想的理性,隔阂而矛盾,写诗和谱曲就是为了化解矛盾,就是消除隔阂,但是,那个叫“罗伯特”的诗人和罗伯特·勃莱是不是也构成了一种对立?在《漆黑的秋夜》中,“我”听到了一千个圣洁的女人和一千个圣洁的男人在午夜辩解,胜利和喜悦是恋人应有的态度,但是圣洁的男人和女人在辩解,于是有人对着罗伯特说:“你很清楚有多少实质会被/恋人浪费,但我说,赐福那些/穿越漆黑的秋夜回家的人吧。”谁在对罗伯特说话?罗伯特听见了什么?是不是那一条湿润的舌头滑入了世界?是不是对秋夜回家的人赐福是一种摆脱欲望的思想?《献给安德鲁·马维尔的诗》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对罗伯特的言说在继续,“罗伯特,你对秋天的看法是对的。那些研究/卡巴拉的人从路得黄昏拾大麦秆的/故事里收获了那么多。”秋天的故事里有舌尖优美的特里斯坦,有我的诗歌,有千年之前许下的诺言,但是身为12世纪骑士传奇中的人物,当他误用爱药而与伊索尔德相恋,这是真正的爱情?“哀泣越多所见就越少”,安德鲁·马维尔在诗中这样说,罗伯特所写的爱恋是欲望的爱恋,“每一滴水里都含有奇异、疯狂的/渴望,想成为海洋。我不必/说为何每一片草叶都如此纤细。”所以当那个声音说罗伯特对秋天的看法是对的,卡巴拉的人从故事里得到的收获就是关于欲望呈现的合理性问题。
罗伯特在写诗,罗伯特看见了欲望,罗伯特叙说着秋天,另一个声音在对罗伯特说,他们组成了一首诗,就像舌头滑入思想,就像思想进入世界,一和多、欲望和理性在两个声音里响起,它们被阐述,它们也可能被隔阂:《黎明前听西塔琴》所听到的是音乐,但也是一个和另一个的对话,一个在说:“一年在天堂。”另一个在说:“两年于地下。”一年和两年,天堂和地下,构成了两种状态,西塔琴手已经将天堂推倒,已经在爱恋中犯下了错误,所以在两种声音里,最后是缄口无言的结局;《当我与你在一起》中传出的也是音乐,但是沙乐琴有两个音,一个属于你,一个属于我,“当我与你在一起,沙乐琴的两个音/带我进入我不在之处。/所有农场都已凭空消失。”在一起意味着不在一起,因为你是你,而我是我,却在你的世界里成为不在之我,我最后需要抵达的是那个“我不在之处”——因为在而不在,因为不在而在,两个音在变成一个音的路上,需要经历怎样的波折?
这首诗可以说是勃莱对这种隔阂状态最富哲理的阐述,所有农场凭空消失,是一种“不在”,我们会死去,也是“不在”,我和自己的友谊无法长存也是“不在”,当我们不在,当我自己不在,不在之在如何抵达?是谁“带我进入我不在之处”?是我之外的“你”,“现在我明白为何我一直暗示“你”这个字——/“你”的声音带我跨越边界。/我们用婴儿出生一般的方式消失。”从第一人称的“我”到第二人称的“你”,从“不在”到“在一起”,勃莱在这里时分化出一种叙述主体,而这个主体既是对我“不在”的代替,也是“在一起”的合一,而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我”对自己向内的态度变成了对“你”以及“我们”向外的对话,仿佛是一种重要时刻的到来,勃莱完成一个“我们”最具意义的书写,“某个和我同名的傻小子已费力/从篱笆厚木棚司的缝隙里看了/一整个下午。告诉那男孩时辰还未到。”
但是人称的转化只是勃莱努力“在一起”的第一步,我和你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不在之处寻找在的意义,勃莱重新回到《柏拉图有许多》中的那个一和多的世界,欲望的舌头如何说话?如何变成理性的思想?诗集《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快乐》本身就指明了一种方法论,那就是“一千年的快乐”,快乐和欲望紧密结合,但是在“一千年的快乐”之上是判决,判决来自于法官,来自于审判,“‘你是一个小偷!’法官说。‘让我们看看/你的手!‘我在法庭上展出我结着老茧的双手。”在法庭的威严之下,我又是反抗者,因为我给自己了判决,而这个判决就是允许自己拥有一千年的快乐,“一千年的快乐”是什么?就是那个被重新书写的“你”,“我听见/一个‘你’字,‘你’起头的每个句子都有关快乐。”你是快乐的代表,你是快乐的符号,你将我从落后者、懒汉、傻瓜蛋那里带到快乐的境地,于是我变成了你,于是我判决了自己的快乐——法官在哪里?他却真正变成了“不在”者。
| 编号:S55·2230221·1918 |
判决的法官,勃莱在这里其实暗指审判者上帝,《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快乐》中到处是对宗教故事的解读,而宗教里的上帝在判决着每一个“我”,这种判决带来的是“我”的不在,而我找到了那个“你”,在“你”允许的快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起初是对上帝的祈求,“这还不够吗,昏星每晚沉落/性爱在黎明结束?求您了,上帝,帮帮/人类吧,因为有人要来弄瞎参孙了。(《弄瞎参孙》)”被弄瞎的参孙向耶和华讨回神力,然后在非利士人的神庙中推倒柱子,与他们同归于尽,但是上帝真的在帮人类吗?“埃及导师不停追问,为何死者/去拿错误的《圣经》,为何鹈鹕/在复活节的早上弄错了她的巢。”错误的《圣经》是关于上帝言说的一次错误,雅各为娶拉结,服事她的父亲拉班7年,期满后拉班却将姐姐利亚送人洞房,7日后才让雅各与托结成婚,为此,雅各需再服事拉班7年,在《雅各与拉结》中勃莱重新书写这段圣经故事,他指出创世纪中的错误就是指出上帝的错误,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作为父母,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像/该做的那样对孩子们说出真正的祝福。”
上帝是审判者,上帝在言说,上帝制造了错误,但是在上帝之外是“我”的存在,一个人类的世界杯打开,我是自我的审判者,我自己寻找快乐——快乐是什么?勃莱在这里揭示的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那里有渴望的一双翅膀,“如果我们已如此接近死亡,为何我们要抱怨?/罗伯特,你为够到鸟巢已爬了那么多树。/没关系,如果你在坠落中长出你的翅膀。(《长翅膀》)”那里有呼喊:“一些大师说我们的生命只持续七天。/一周之后我们会在哪里?今天已经周四了吗?/快,喊吧现在!周日的夜晚马上就要来临。(《呼喊与回应》)”那里有音乐,“每一个用自己的手指按下琴弦的人/都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指尖的疼痛/有助疗愈双手已犯下的罪恶。(《开心果》)”那里有狂喜,“没关系,在杆子顶上保持平衡!人们/说如果你想对所有人藏起这神奇之物,/你将不得不拥有一段充满狂喜的人生!(《拉莫的音乐》)”当然也有哀悼,“一些坟墓伫立于林中。我们依然不明白/为何松木棺材如此精美。我们不知道。/我们依然忧思着为何太阳会升起。(《哀悼史》)”
上帝制造错误,上帝不在,而我在,我和你在,我们在,在呼喊中,在音乐里,在哀悼中,在爱恋里,甚至在走进死亡的路上——或者人类的全部情感都指向快乐本身,因为“他们依然住在欲望的老客栈里”。“在”构成了“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在场性,这种在场性指向的永远是一种存在的欲望:“有人说每一滴堪萨斯的地下水/都了解海洋。怎么有这事呢?/一滴水都像我们一样渴望存在。(《新郎》)”即使那男女女不停地飞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也是为了证明燃烧的存在,所以勃莱说:“我们每一个都是新郎,渴望着存在。”住在欲望客栈里的我们,像新郎一样渴望存在的我们,构成了勃莱“带我进入我不在之处”的主体,而不在之处也变成了在,我也成了另一个我。如果说2006年的诗集《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快乐》是寻找那个“你”,寻找真正的“快乐”,这种寻找戴着勃莱对宗教的质疑,带着对生命的激情,更多的是找到了那条湿润的舌头,但是要滑入世界,需要的是思想——2012年的诗集《对驴耳诉说》开始了真正对于世界的探求。
|
| 罗伯特·勃莱: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快乐 |
“每一次我们说‘我信奉上帝’,意思却是/上帝已拋弃了我们一千次。”诗集中的第一首《藏在鞋中的渡鸦》依然指向了“上帝”的错误,千次是老炼金术士暗示的千次,是我们已将自己的死亡活过的千次,是母亲保佑儿子的祈求被拒绝的千次,是小潜鸟将脑袋扎进雷尼湖中千次,当然更是上帝抛弃我们的千次,但是千次的错误只属于上帝,属于人类的是千次的信心,“罗伯特,你已浪费了那么多人生/坐在屋里写诗。你还会/再那样做吗?我会的,千次。”千次而不停止,千次而不放弃,千次而不改变,就在于发现属于自我的那些东西,存在着,快乐着,欲望着。在“第一部分”里,勃莱将这种存在看做是对遗忘的遗忘,“尼尔玛拉今日弹奏的音乐有/两个名目:寻回失物者,/和万物自其丢失者。(《尼尔玛拉的音乐》)”尼尔玛拉的音乐有两部分的主题,一部分是万物丢失,“女人对此了然,/因为这是一个万物失落其中的世界。”老虎在林中吃人,诸神对此应允,圣徒仰慕沾血的须髭,但是这也是一个“寻回失落者”的世界,女人新洗了头发,“灵魂/一次次出生于光滑、活泼的肉身”,男人深爱着女人,他们说:“让羔羊过来被宰杀”,而小孩在出生之间,“那么多小地毯被编织又拆散。一百碗/水被倒在地上。”
万物失落,是因为上帝的错误,是因为上帝的不在,但是寻回失落,则是每个人的存在,是每个人的在场,如何寻回失落?第二部分提供了一种言说的方式,“就抓住我的鬃毛,让你的/嘴唇更贴近我毛茸茸的耳朵。(《对驴耳诉说》)”我和驴子在说话,我有很多话要讲,驴子也急不可耐,我问它:“春天怎么了?”“我们的腿怎么了,在四月的跃动中如此欢乐?”驴子却说:“别管这些。”别管这些就是将那些烦恼抛却,是要回到对话的状态中,一个我和一只驴子,我有我的呼吸,驴子有双耳的“矩形燕麦”,贴近再贴近,说出来和听得见,构成了对话最完美的状态——《对驴耳诉说》在解构了上帝之言的同时构建了只属于口和耳的对话世界,它们平等,它们和谐,它们就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在第三部分里变成了欲望本身,“当你已在温暖的被窝里睡了整夜,有时/你会发觉睡衣上有股朽木的香味。/它有点儿下流,但让人满足。/它是某种契合亲密的温暖/由你的蛋蛋在夜间创造。”这是哺乳动物的快乐,这种快乐混合着欲望,而这便是知识的源头,“知识竟来自/如此深邃的源头。(《早晨的睡衣》)”而在第四部分里,勃莱更是发现了自然中的种种存在,它们是在风暴中保住了自己的蛋的“隐士鹪鹩”,是“慢慢地、倔强地,我们找回那些乐趣”的驼鹿,是美味、丰沛、有着古老乐趣的土耳其梨,是“越/过梦者昨晚留下的足迹”的八哥,而这一切都是站在“老诺斯替教徒”的对面——他们无论是禁欲主义者还是纵欲主义者,都不是对自然的生动阐释,都是被肉身的缺少知识的命名,而勃莱把自然看成是乐趣的存在,他和欲望共同构成了“知识的源头”。
和《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快乐》相比,诗集《对驴耳诉说》里更多了一份平静、宽容,也更具有了孤独之存在的诗意。“静默于月光中,无始无终。/孤身,却不孤独。(《静默于月光中》)”一男一女在露天野地里,在羚羊皮的长袍下,在明月和平原之中静默,“无始无终”是一种永恒状态;更孤独的是《致高山的鸣啭》里的那个他,“他行走,他坐下来,他找到一块石头;/还没有人见过它,他坐下来,孤身一人。”一片平原允许生命展开最自然的形态,一块石头托起最孤独的灵魂,仿佛世界只属于他们,“或是在忧伤的峡谷里伸展你的翅膀”,再无干扰,再无不在。而对于诗人自己来说,也在接近这种纯真、纯美的诗意世界,或者拥有动中之静,“现在是周日下午。我读着/朗吉驽斯,超级碗比赛正在进行。/大雪飘飞,而世界宁静。(《周日下午》)”或者找到了细微之美,“那日早晨.我听见水被倒入茶壶中。/那声音只是一种普通、日常、嗑啦啦的声音。/但忽然之间,我却明白你爱我。/一件前所未闻之事,爱在倾倒的水中能被听见。(《茶壶》)”或者在父亲和母亲的世界感受那份爱,父亲的诗是“走进一片田地的样子”,母亲在养老院里“几乎不说一句话”,还有女儿,还有女儿的宝宝,“我女儿已发觉她姑娘时的玩意儿/皆为水中月。如今她有了个宝宝。/她是太阳而宝宝正安眠。”
在生活的细节中发现美发现诗意发现存在,这也许就是勃莱寻找到的“不在之在”,就是存在的真正渴望,就是不确定性的确定。我们一直都让奴隶在夜晚忙活,我们不断将自己送上歧路,每天起誓不会离你而去的妻子每晚她都不在,警察带走了从监狱逃出来的受害者……这是生活本身的错误,这是生活的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却是在“这儿的每一节诗都说了某件事,但究竟是什么?/每一行都说了我们不愿听的某件事。/但每一行都是一块石头带我们过河。(《不确定性》)”石头带着我们过河就是确定性的表现,这种确定性也就是一种存在,由此勃莱在诗意的世界里完成了关于存在的命名:存在就是“打谷者总是在夜幕降临时回家”,就是“我爱着那即将被割去的小麦”,就是“每天我都如此快乐地写下这些诗”,包括苦难、包括愁苦,包括战争,即使它们没有被旧诗人说出,对驴耳诉说的新诗人,也是在“我”成为“我们”中抵达了生存之境:
没关系,如果我们继续遗忘回家的路。
没关系,如果我们不记得我们何时出生。
没关系,如果我们写同一首诗一遍又一遍。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