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29《元诗别裁集》:气格声调进乎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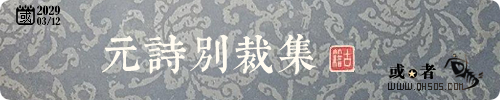
循元诗盛轨,弗坠唐音,而溯源于《风》、《骚》、汉、魏,则是钞岂惟足以供咏吟、资挦扯而已。
——《序》
诗歌不只是吟咏之作,不是挦扯之物,而是让学者从诗歌中感受“金盘餐沆瀣,花界食醍醐”的风格,并“由是而之焉”:循着诗歌发展的脉络,寻找诗源,是风,是雅,是汉魏诗风,那么,《元诗别裁集》真的能担当此种责任?所选录的诗歌真的远超“供咏吟、资挦扯”的功用?
《元诗别裁集》原名《元诗百一钞》,是清人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合编的元诗选集,他们还合编了《宋诗百一钞》,这两本诗选和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合刻,被称为《五朝诗别裁集》。那么,沈德潜为什么独独不编选宋、元两代的别裁集?或者在其他别裁集里找到一些线索,在《唐诗别裁集》的“原序”中,沈德潜说自己“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而和自己的这种爱好不同,“时竞尚宋、元”,于是“适相笑也”,沈德潜似乎故意和被人形成了一个错位,是他们笑自己也是自己笑他们;在《明诗别裁集》的“序”中,沈德潜则提出了宋元明不同朝代诗歌的特点,“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不编宋元诗别裁集,就在于不喜欢近腐的宋诗,近纤的元诗,而独爱复古的明诗,之所以喜欢复古,是因为明朝诗歌处处显示唐音,“而二百七十余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别。”
因为近腐近纤,所以沈德潜绕开了宋元诗歌,而这种绕开本身也是对唐音情结的一种实践,但是宋元诗歌真的百无一处?清人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合编的《元诗别裁集》并没有说明编选的理由,但是沈钧德所作的《序》中却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谓元诗纤弱逊宋,此未究元人大全,遽为一方之论也。”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元诗并非全是纤弱之音,举例来说,“未尝仕元”的元好问“巨手开先,冠绝于时”,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卓然成家为正宗”,而黄溍、柳贯“代兴无愧”,除此之外,“其余骋奇斗丽,不一而足。”所以沈钧德认为元诗的风貌犹在,“掇锦囊之逸藻,嗣玉溪之芳韵,又非独雁门、铁崖已也。”
沈钧德在序中提出了和沈德潜等人不同的观点,给予了元诗特殊的地位,而且他还认为元诗具有自己的使命,“盖宋诗末流之弊也,为粗率,为生硬;元诗则反是。欲救宋诗流弊,舍元曷以哉?”他承认宋诗已经呈现出“末流之弊”,但是元诗一扫宋诗粗率、生硬的特点,反而成为“救宋诗流弊”的存在。看起来沈钧德和沈德潜的观点对立,但其实他对《元诗别裁集》的评价以及张景星、姚培谦、王永祺选诗的标准,却处处是沈德潜的影子。一方面,元诗之所以能救宋诗流弊,就在于他的风格近古,“读《百一钞》,沨沨乎,洋洋乎,气格声调,进乎古矣。”气格声调具在,“正变以揽诸公之长,故不隘;出入略以三唐为准,故不滥。”之所以不滥,就在于“以三唐为准”,而且这些别裁的元诗“循元诗盛轨,弗坠唐音,而溯源于《风》、《骚》、汉、魏”,也就是说,元诗依然保留了唐音,这和沈德潜编诗的标准一致;另外,《元诗别裁集》有别于苏天爵的《文类》,“不及数家,或传或微”,也不同于顾嗣立《元百家诗》,“广搜博采,秀野草堂所刻,号为极富”,《元诗别裁集》则是存其精华,是为了“备一代之文献”,在汰繁芜中“存雅正”,这种“存雅正”的别裁去取的要求也和沈德潜的诗教相符;甚至于《元诗别裁集》的体例,也完全沿用了《唐诗别裁集》以体裁分卷的方式,按照古诗、律诗、绝句分类。
| 编号:S26·1950303·0100 |
“沨沨乎”的元诗,“洋洋乎”的元诗,如何救宋诗流弊?如何“弗坠唐音”?如何“存雅正”?沈钧德在序中所提及的几位诗人可以代表元代诗歌特色,“巨手开先,冠绝于时”的元好问是《元诗别裁集》中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五言古诗中选录了10首,七言古诗收录9首,另外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均有收录。五言古中的《箕山》(“幽林转阴崖,鸟道人迹绝”)、《缑山置酒》(“灵宫肃清晓,细柏含古春”)、《光武台》(“东南地上游,荆楚兵四冲”)等都有古韵;七言古的《游黄华山》最后四句是:“手中仙人九节杖,每恨胜景不得穷。携壶重来岩下宿,道人已约山樱红。”元好问以他那似海豪情和如椽彩笔集中而生动地描绘了黄华瀑布的壮丽景象,抒发了对自然盛景的由衷赞叹,《王右丞雪霁捕鱼图》(“渔浦移家愧未能,扁舟萧散亦何曾?”)、《泛舟大明湖》(“我时骖鸾追散仙,但见金支翠蕤相后先”)、《涌金亭示同游诸君》(“举杯为问谢安石,苍生今亦如卿何?元子乐矣君其歌”)也写尽风流;而在七言律诗中,元好问的诗歌则更多悲戚感,如《横波亭为青口帅赋》:“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疏星淡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颍亭》更是寄托了哀思:“颍上风烟天地回,颍亭孤赏亦悠哉。春风碧水双鸥静,落日青山万马来。胜概销沉几今昔,中年登览足悲哀。远游拟续骚人赋,所惜匆匆无酒杯。”《被檄夜赴邓州幕府》一诗中流露的是躲避尘世的心愿:“幕府文书鸟羽轻,敝裘羸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岂不怀归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鸭闹,一川桑柘晚烟平。此生只合田间老,谁遣春官识姓名?”
除了元好问一家当大之外,《元诗别裁集》收录赵孟頫的诗作也较多,五言古收录了25首,但似乎这些诗作都是反映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张詹事遂初亭》的前两句就是一种赞颂:“青山缭神京,佳气溢芳甸。”《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描写了耕织图上的劳动生活场景,从“新岁不敢闲,农事自兹始”的正月写到“所冀岁有成,殷勤在今朝”的二月,从“乘兹各播种,庶望西成功”的三月写到“旦随鸟雀起,归与牛羊晚”的四月,十二个月不同的劳动场景都被生动地描写出来,在十二个月的“右耕”之后是十二个月的“右织”,从“女工并时兴,蚕室临期治”的正月一直写到“斫桑埋其中,明年芽早抽”的十二月,如此富有画面感、如此贴近劳动生活的诗作,竟然是“奉懿旨撰”。但是在七言古中,选录的诗作风格有了重大转变,《和姚子敬秋怀》:“搔首风尘双短鬓,侧身天地一儒冠。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苜蓿秋高戎马健,江湖日短白鸥寒。金尊绿酒无钱共,安得愁中却暂欢。”传递出的是一个“愁”;《闻捣衣》:“露下碧梧秋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苜蓿总肥宛騕袅,琵琶曾泣汉婵娟。人间俯仰成今古,何待他时始惘然。”更是寄托着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岳鄂王墓》:“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睹物思情“不胜悲”;《钱唐怀古》:“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莺花非旧游。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更是感慨了“千古兴亡”……
元好问、赵孟頫的诗歌呈现出多元的特色,《元诗别裁集》在“弗坠唐音”中“存雅正”,一百五十二个作者、诗作六百十九首也在这种标准下呈现出多元性,尤其是七言古诗,实践着“气格声调,进乎古矣”的风格。郝经的《贤台行》旁注:“古黄金台也,土人称为贤台。”“台上黄金少颜色,惠王空读乐毅书。古来燕赵多奇士,用舍中间定兴废。还闻赵括代廉颇,败国亡家等儿戏。燕子城南知几年?台平树老漫荒烟。莫言骐骥能千里,只重黄金不重贤。”最后一句“只重黄金不重贤”是一种质问;揭傒斯的《高邮城》:“高邮城,城何长?城上种麦,城下种桑。昔日铁不如,今为耕种场。但愿千万年,尽四海外为封疆。桑阴阴,麦茫茫,终古不用城与隍。”诗人通过高邮城的今昔变迁,以极明白的语言,表达了希望和平,永不要战争的美好愿望,诗歌纯用口语,去尽雕饰,音节自由,韵脚细密,反复咏叹,颇似民间歌谣;而宋无的《战城南》:“汉兵鏖战城南窟,雪深马僵汉城没。冻指控弦指断折,寒肤著铁肤皲裂。军中七日不火食,手杀降人吞热血。汉悬千金购首级,将士衔枚夜深入。天愁地黑声啾啾,鞍下髑髅相对泣。偏裨背负八十创,破旗裹尸横道旁。残卒忍死哭空城,露布独有都护名。”更是在哀悼阵亡士卒中诅咒战争;还有杨维桢的《鸿门会》:“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貐。(暗言范增、项庄。)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余。(此言沛公当独王天下,羽不得分也。)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军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拔山,气卷黄河酒中泻。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一首咏史诗,写刘邦、项羽鸿门之会,全诗结构紧凑,用词精炼,事至繁而笔极简,造语奇崛,意境幽诡。
《元诗别裁集》选录的作品也比较广泛,尤其是收录少数民族诗人的一些作品,如耶律楚材、揭奚斯、萨都刺、迺贤、丁鹤年、余阙等,在艺术上颇具特色。或者沨沨乎,或者洋洋乎,或者骋奇斗丽,或者“掇锦囊之逸藻,嗣玉溪之芳韵”,但是要让元诗救宋诗流弊,也许言过其实。而这本别裁集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只选录诗歌,编者的观点全无,没有关于诗人的简介,没有对于诗作的评点,也没有编者的序言,如此“三无”,最后“惟足以供咏吟、资挦扯而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