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1-07《资治通鉴(一)》: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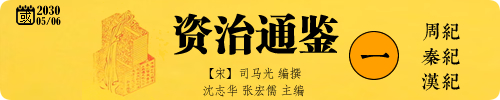
【册牍渊林】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赐名《资治通鉴》。
编撰《资治通鉴》的来由,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土,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一部编年通史;其二则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于是,司马光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成一部政治通史,《通鉴》历时十九载,“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尽于此书。
收录在册的是御制《资治通鉴序》,“治平四年十月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其中谈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规模和成书特色,“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下终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即959年,录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再加上《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余万字,的确是“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序》还说到了得名之缘由:《诗》曰:“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赐书名《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三分晋国】
《资治通鉴》的开篇记述的是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晋一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短短十四字作为《资治通鉴》的开场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三家分晋,春秋走向了终点,战国时代开篇,将这一历史分水岭作为《资治通鉴》开篇,正符合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目的。正文十四字之后便是“臣光曰”为标记的点评,点评为千字长文,这也是整部《资治通鉴》里最长的一段“臣光曰”。司马光从一开始就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礼教、地位和名分是“天子之职”,那么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礼、分和名是道统,是秩序,维护礼教就是维护秩序:“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三分晋国的危害在于完全改变了礼教和秩序:“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这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的标志,也正是由这样的危害性而改变了历史进程,所以成为《资治通鉴》的开篇,而这个观点在《序》中就已经有了交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不管是“先王之礼于斯尽矣”还是“王制尽矣”,都表达了司马光的一种哀伤,但是真正的哀伤在于,这一破坏责任并不在于诸侯而在于天子自身,“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天子自坏就像是自掘坟墓的秩序悲剧,由此进入到了诸侯相争的战国时代,“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从卷二的显王十年,即公元前359年开始讲起,当时的公孙鞅从卫国到秦国,还是卫鞅,甘龙对卫鞅的变法主张提出了疑问,“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但是卫鞅却指出,“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卫鞅的观点很明确,制定法规政策的人是聪明人,而受制于人的人是愚笨的人,因时而变的人是贤德的人,死守成法的人是无能的人,所以卫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开始颁布变法之令。变法的主要条文有以下内容: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从这些条文来看,卫鞅的变化的确是对观念的突破,的确是对束缚的解放,的确是因时而变,但是,变法遇到了阻碍:在刚颁布变法之令的时候,卫鞅担心大家不相信,推出了“徙木之赏”,如果有人将三丈之木从南门徙置北门,就给那人十金,但是这一悬赏还是没人敢试,于是卫鞅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果然有一人站出来徙木,金钱的诱惑,卫鞅变法才走出了第一步;变法一年后,“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面对这一问题,卫鞅说出了变法推广之难的关键所在:“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新法不能顺利施行,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违规,虽然太子犯法,最后“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但是卫鞅的变革还是有其彻底性,于是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司马光在评价变法的时候,谈到了“信”的重要性,“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他举例说:“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否则的话,“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司马光所说的“信”是信誉,是信任,是建立良好关系的保证,当然也是维护秩序的关键,公孙鞅从卫鞅到商鞅,变法之本就是让国君建立信誉,“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称不上完美,而商鞅甚至可以说有些刻薄了,但是处在战攻之世,天下尔虞我诈,他们尚且不忘树立信誉以收服人心,何况今天治理的统治者呢?
到目前为止,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卫鞅都采取了正面的评价,但是二十九年发生的一件事,卫鞅的刻薄甚至变成了欺骗,当时他在秦孝公面前评判了秦魏的关系,““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所以秦孝公同意卫鞅举兵伐魏,而魏国派公子卬出战。在两军对阵时,商卫鞅写给公子卬一封信,“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于是和他相会,正当双方盟誓已毕,卫鞅让事先埋伏好的甲士冲了进来,俘虏了公子卬,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而卫鞅因为这次取胜获得了商於十五邑的封地,从此便称为商鞅。
当秦孝公去世之后,秦惠文王继位,有人搞商鞅有谋反之心,于是前去拘捕,商鞅逃到了魏国,魏国没有接纳他,他又返回到了秦国,带着他的手下发兵攻打郑国,最后,“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商鞅车裂而死,似乎也成为自己变法的牺牲品。对于商鞅的悲剧,司马光记载了曾经商鞅和赵良之间的对话,商鞅问赵良自己治理秦国和五羖大夫相比,谁更具有贤德?赵良认为,五羖大夫“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当他去世时,秦国的百姓流泪悲伤,所以,他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在他看来,商鞅完全不顾这些,“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阂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所以他对商鞅提出了忠告,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但是自恃其高的商鞅没有听进心里,最终五个月不到就大难临头。
【仁义为利】
显王三十三年,司马光记述了邹人孟轲见魏惠王,谈到仁义和利的问题。仁义,一直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传达的治国之道,而在孟子这里,仁义和利的关系被辩证地建立起来,魏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远道而来,是什么利益驱使?孟子在回答中首先否定了利益:“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不是因为利益而是完全为了仁义,但是孟子进一步阐述中把仁义也看成是一种“利”,“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这时的“利”只是有利于的说法。而在孟子和子思的讨论中,子思认为,对于牧民来说,第一位的就是利益,孟子对此的说法是:“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而子思则阐述说:“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仁义本身就是利益,如果上不仁,那么下就无法安分,如果上不义,那么下就会尔虞我诈,子思引用《易》中的话说:“利者,义之和也。”仁义就是利益的最大化。
对此,司马光抛出了自己的观点,孟子和魏惠王,孟子和子思的对话,对于利有不同的说法,甚至在魏惠王面前孟子闭口不谈利,而直接宣扬仁义,但是和子思一样,认为最大的仁义就是一种利,如此,根据不同的对象谈论内容,这也是仁义的表现,“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
【天下之将】
司马光关于仁义的思想也体现在用兵之道上,他记述了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况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论兵的经过。荀况先是论述了“仁人之兵”,“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仁人之兵所体现的就是王者的仁政,“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仁人之兵,可以使上下一心,可以使三军同力,“仁人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必将聪明警戒,和傅而一。”相反,如果上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代翕代张,代存代亡,相为雌雄耳。”那么,这些也都成了“盗兵”。
从仁义之兵,荀况又论述了“为将”的看法,“知莫大于弃疑,行莫大于无过,事莫大于无悔;事至无悔而止矣,不可必也。”如何达到无悔,荀况提出了“六术”,“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行吾所明,无行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提出了“五权”,“无欲将而恶废,无怠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提出了“三至”,“将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提出了“至臣”,“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小能怒,夫是之谓至臣。”提出了“大吉”,“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提出了恭敬,“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提出了“五无旷”,“敬谋无旷,敬事无旷,敬吏无旷,敬众无旷,敬敌无旷,夫是之谓五无旷。”由此,荀况认为,做到这些便是“天下之将”,“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旷,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荀况长篇大论了仁义之兵、天下之将和王者军制,那么,这些思想的背后是不是一种权术?是不是只为争夺?当陈嚣问荀卿:“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况对此的解释是:“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战争的本质是除害,是禁暴,而不是争夺。
【自屈者负】
项羽最后战死垓下,对于项羽这一生,司马光借用司马迁的评价:“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项羽在最后时刻所说“天亡我”,被司马迁认为是一种荒谬的说法,司马光还引用了杨雄《法言》中的评价,杨雄也质疑了项羽之败的“天也”,他通过项羽和刘邦不同的态度对比来说明项羽“自屈者负”,“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一个是群策群力调动众人的力量,一个只是凭借一己之力想要征服天下,所以结果是一种必然。
司马光引用了司马迁和杨雄的观点,阐述了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和“自屈者负”的悲剧命运,从而否定了所谓的“天命”。而在广武涧对阵中,司马光通过刘邦细述了项羽的十大罪状:“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矫杀卿子冠军,罪二;救赵不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罪六;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王,罪七;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与,罪八;使人阴杀义帝江南,罪九;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
【人物评价】
孟尝君:“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
韩非:“臣闻君子亲其亲以及人之亲,爱其国以及人之国,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燕太子丹:“燕丹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挑怨速祸,使召公之庙不祀忽诸,罪孰大焉!而论者或谓之贤,岂不过哉!”
韩信:“世矢乘时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报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难哉!”
张良:“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7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