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1-07《铜钟案》:皆由正义统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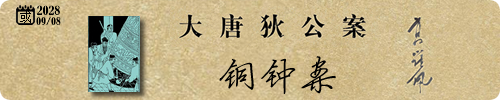
正如前文所述,如今我已全然放弃了研究古代刑名罪案,对于这些暴戾不祥的话题,不再发生任何兴趣,转而乐此不疲地沉湎于收集宋代青瓷了。
——《第一回 赏古物行家逢奇遇 受任命狄公赴蒲阳》
又是大明盛世,又是第一人称之“敝人”,又是将前朝之事投射在后世之人中,高罗佩在《铜钟案》中延续了《湖滨案》的开篇模式,只是当“我”放弃了对古代刑名罪案的研究,拒绝关注暴戾不祥的话题,甚或对狄公判案之拒绝,隐含着怎样的心理转变?
第一人称“我”自述是一个茶商,但是在退职后不问店务,迁到乡间之后过起了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其中之一种兴趣便是研究古代刑侦断案的文献,收集前朝留下来的判案工具,收藏品包括罪案记录,坏人所用的凶器,盗贼使用的工具,以及其他作案的器物。这无疑是一种器物崇拜,而当我在刘掌柜的古董店发现“蒲阳狄府之物”时,这种器物崇拜甚至变成了疯狂:一个是狄公曾经用过的惊堂木,上面还刻有提醒自己为国尽忠、为民效力的诗句;在刘掌柜的古董店里发现了狄公曾经戴过的乌纱帽,除了被蠹虫蛀出的几个小洞外,官帽完好无损。于是,我戴上了乌纱帽,然后面向那面年代久远的镜子对照,“原本锃亮的镜面已变得晦暗无光,仅仅映出一团灰黑的暗影。”这种镜像般的存在终于演变为一场梦魇,“不料突然之间,从黑影中显出清晰的轮廓,我分明看见一张完全陌生的人脸出现在镜中,面色憔悴,神情惨苦,喷火似的两眼正直盯着我。”
镜面中的暗影,镜子中的人脸,就在那一刻让我中邪,我仿佛坠入了无底深渊,当醒来时发现自己还在刘掌柜的店里,而那顶古旧的乌纱帽已经滑落,掉在了破镜的碎片之中。梦魇并未结束,回家之后大病一场,卧床一月之后才慢慢恢复。对断案文献和器物的迷恋,终于在戴上狄公的官帽时变成了一种在场,但是这种在场的感觉是被谵妄所支配的:我便是当年断案如神的狄仁杰,由此的疯狂制造了邪念,黑影和人面终于将我推向了深渊。在这里高罗佩设置了这样的场景,一方面是在当下和前朝之间建立联系,以乌纱帽和镜子作为器物的代表,让我穿越到了古代,自己当然也变成了狄公,所以之后试图连缀成篇的三桩奇案便有了被叙述的可能。而另一方面来说,我的内心具有某种猎奇心理,在大明盛世的当下,作奸犯科之事几近绝迹,天下太平,海内清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对于奇案的渴望也只能让狄仁杰复活,而复活只是一个镜像,当现实再也无法回到狄公生活的时代,我演绎的故事其实变成了一场梦魇,而最后的幡然醒悟便是再次回到现实,对宋代青瓷的研究取代了对古代断案的兴趣,我当然只生活在盛世之中。
一种想象的完成,是一个梦魇的开始,而以此为引子,当狄仁杰登场,这个故事似乎也只是属于文本,属于传说,属于那些不可近身的器物,属于猎奇本身——高罗佩的狄公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更多人的猎奇心理,“至于我讲述这三桩前朝奇案时,到底有几分是在这离奇遭遇中真正经验过的,又有几分是高烧发作、神志昏迷时臆想出的,如此疑问将统统留给有心的看官去自行裁断,至于是否真有其事,我也无意再去故纸堆里费神查考。”而回到高罗佩所书写的狄公案故事里,所谓的惊悚,所谓的恐惧,所谓的神奇,也都带着那些想象,也都变得有些疯狂,也都是一些虚构的传说。
作为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狄公案系列小说,《铜钟案》里依旧是三奇案,只不过和《黄金案》和《湖滨案》相比,这里的三桩案件彼此之间的联系相对松散,甚至可以说它们缺少环环相扣的结构特点,尤其是萧屠夫女儿被奸杀一案完全脱离其他两桩案件而独立存在。狄公到蒲阳任县令,甫一到任便着手处理这一案件,因为这个案件是前任冯县令没有结案的案子:萧屠夫的女儿淑玉被发现奸杀在闺房之中,经调查她有一个情人名叫王献忠,半年前王献忠遇见淑玉心生爱慕,之后二人幽期密约,王献忠总是在半夜时从窗口爬进去天亮之前溜回住处,这一偷情故事只有半月街的龙裁缝知道。而这一次淑玉被杀害于闺房里,头上的金钗不见了,王献忠成为最大的嫌犯,冯县令查验过证据,也听取了证词,断定王献忠就是真凶,但王献忠拒不承认罪状,冯县令用刑时王献忠没有招供便不省人事,之后冯县令离任,于是这个案子便落在了狄公手上。
| 编号:C38·2221004·1881 |
“本县细思过后,认定秀才王献忠罪行属实,并无疑义。待其招供后,窃以为应典以重刑处死。”这是冯县令给狄公留下的纸条,但是在听取了关于案件的汇报后,狄仁杰认为这里面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再次审问王献忠,他依然只承认引诱少女却拒不承认杀人害命,于是玉淑丢失的那只金钗变成了重要线索。狄公从案件的各种线索出发,认为很可能是当晚有歹人经过发现了这一桩风流情事,于是悄悄潜入玉淑的房间将他杀死然后取走了金钗,所以在这样的怀疑论面前,狄公派出马荣装扮成无赖闲汉的模样,然后去乞丐偷儿们时常出没的地方去,然后暗地打探一个云游僧人或道士,或是假扮成此类人物的恶徒,“他手里定有一对纯金打制的精巧发钗。”狄公对此的判断是:“我从未见过此人,因此尚且不知他姓甚名谁。至于犯下何罪,我敢说他就是奸杀萧屠户之女的歹人!”
马荣依计行事,认识了丐帮军事盛八,又混进了他们的内部,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最近想要卖掉金钗的道士,最后那个名叫黄三的人落网,在衙门里黄三也终于招供:是他潜入了半月街玉淑的房间,然后奸杀谋财。于是黄三被判死刑,而王献忠也获得了清白,鉴于他对玉淑之情,狄公命他“娶淑玉为妻”,灵牌便是新娘,“等你付清了这两笔钱之后,方可另娶妻室,但以后的妻妾均不许侵占淑玉之位,终此一生,她始终是你的元配夫人。”由此萧屠夫之女被奸杀一案水落石出,这一案便以完全独立的方式成为狄公在蒲阳所断完的第一桩案件。
第二桩案件是普慈寺淫僧案,高罗佩在后记中说,此案件取材于《醒世恒言》第三十九回《汪大尹火焚宝莲寺》;而第三桩案件铜钟藏尸一案,其主线来自中国著名小说《九命奇冤》,“原书取材于1725年前后发生在广东的一桩涉及九条人命的案件,结局依例是在公堂上结案,但笔者改写得更为惊心动魄,并借用了在明清断案小说中时常出现的铜钟题材。”实际上这两桩案件之间也并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也基本上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陶干发现蒲阳的普慈寺疑点多多,“那普慈寺格局宏大,刚刚修缮一新,灵德法师乃是一寺之主,手下有六十名僧人,但这群和尚既不吃斋也不念佛,整日里吃肉喝酒,日子过得穷奢极侈。”所以他对狄公说:“老爷明鉴,我尚且不能说有十足把握,但很是怀疑这普慈寺的钱财,乃是由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聚敛而来的。”狄公闻得这些信息后,初步判断这里有可能会如《湖滨案》中白莲教组织一样的秘密机构,“你我要对付的并非一伙平常的罪犯,而是一个势力广大、遍布朝野的组织,他们定会立即为那灵德撑腰壮胆,予以全力支持,不但在朝廷四处奔走,还会上下打点那些身居要职者,一层一层地逐级影响至此地。”
狄公将普慈寺和和秘密组织相联系,这一判断最后终于得到证实,他邀请当地四位社会名流,一起前往普慈寺揭开了其中隐藏的秘密,除了从住持灵德法师那里知道勾结官府从事秘密计划之外,普慈寺还成为淫僧强暴良家妇女之所,阿杏和青玉假扮良家女子利用手中的胭脂膏给淫僧头上留下鲜红的掌印,才让这一切大白于天下。当普慈寺一案水落石出,狄仁杰将其命名为“正义”的结果,“我并非疑神疑鬼之人,也从未断言过魑魅魍魉一定不会在人间现形。不过,我亦确信清白正直之人无须惧怕鬼怪,因为无论阴间还是阳界,皆由正义统摄一切。”
半月街奸杀案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普慈寺淫僧案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叛乱计划,狄公揪出这两桩那间的凶手就是为了还一个公平,就是为了达到正义的目的。而小说着笔最多、案情最复杂的则是和“铜钟”有关的林帆一案。当时狄公正查看公文,有老妪梁夫人报案,“此案乃是世居广州的梁林两家富商之间的血海深仇,起因是林家公子诱奸了梁家女眷,之后又狠心无情地百般迫害梁氏一门,并掠去了梁家的全部财产。”狄公翻至诉状的最末一页,才发现这一纸状写于二十年前。二十年前发生在广州的案子,二十年后出现在蒲阳,无论如何,梁家和林家的仇恨并不能轻易化解。经过调查,狄公发现案件的来龙去脉:林帆娶了梁夫人的女儿,即梁鸿之妹为妻,梁鸿之妻被梁家生了孩子,但是林帆夫妇没有生育,于是林帆由妒生恨,认为梁家是他失意与不幸的根源,后来林帆竟然对梁鸿之妻心生邪念,于是生出歹计,预备要将梁鸿的家产与妻室一并据为已有。后来林帆之妻失踪,人们猜测是他杀妻还藏匿了尸身,于是更加痛恨其梁家,残忍杀死梁家九口人便是他犯下的罪状——梁夫人和孙子梁科发在那场灭门的火灾中逃生,之后辗转来到了蒲阳,梁科发暗中调查林帆贩运私盐,不像后来也莫名失踪 ,所以梁夫人找到了狄公,引出了两家长达二十余年的恩怨。
狄公在调查普慈寺一案之后来到寺内发现了其中的铜钟,出于职业敏感命人查看铜钟下面有无可疑之物,当打开铜钟才发现里面躺着一具人骨,人骨的圆形锁片里发现了一个“林”字,狄公判断此人可能就是失踪的梁科发。当众人研究铜钟下面的尸身时,对于狄公甚至整个断案团队最大的考验出现了:垫在铜钟下的石头鼓凳突然滑脱出去,在场的五个人被齐齐罩在铜钟下面。如果不设法从铜钟中出来,那么这五个人无疑也会最后变成尸骨,而这个铜钟巨重无比,里面的呼救声外面根本听不到,而凭借里面五个人的力气也没有办法逃出来。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考验,在这紧要关头,狄公利用大家的力气移动铜钟,然后寻找地下的空隙,最后终于找到了透气的地方并最终通过众人努力从铜钟里出来。这时他们才发现,是有人用长枪将鼓凳撬开,故意将他们置于死地,而这个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林帆。
“我并非睚眦必报之人,但是不想林帆竟使出这等卑鄙的手段,企图一举害了我们五人性命。若不是侥幸将大钟推出平台一侧,蒲阳城内又会传出一桩离奇的失踪案了。我定要亲手捉住林帆这厮,以解心头之恨,最好他不肯乖乖束手就擒,动一场拳脚方才痛快!”这是狄公感性一面的流露,在铜钟历险之后,狄公也发现了林帆在林宅和圣明观之间建立的密道,用以走私,“对于林帆的走私生意来说,这片房产真是再合适不过,难怪他肯花费大笔银子统统买下!”最后提审林帆,“人犯林帆,犯下谋反大罪,依律将被处以车裂。”在林帆被宣判之时,却传来梁夫人服毒自尽的消息,狄公认为二十年前的恩怨自此了结,“梁林两家一案,今日总算彻底了结。林家最后一人死于法场,梁家最后一人也已服毒自尽。这一场冤冤相报的世仇,延续了将近三十年从未稍歇,经过一连串的杀人放火、奸淫欺诈后,人人皆死于非命,如今终于一了百了。”
但是这并非是最后的结论,梁林两家的恩怨还存在一个最大的疑点:为什么在广州期间林帆想方设法要斩草除根,而到了蒲阳之后,林帆却并未对梁夫人痛下杀手,所以这里隐藏着惊天秘密:梁夫人并非是梁夫人,而是林帆之妻,而那个铜钟下面的尸骨也并非是梁科发,而是林帆的儿子——比起林帆当初犯下的罪恶,林帆之妻以这样的手段惩罚罪人,更是一种残酷,“我之所以说她泯灭人性,是因为她为了报复丈夫,竟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儿子,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亲口对林帆说出,其实他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从而给予他最致命的一击。”案件有悖伦理,甚至是泯灭人性,而这正是铜钟案之暴戾、之残酷、之难以置信的一面,而那间落幕时闪闪发光的“义重于生”四个大字,或许是对人性之正义再一次的强调。
从狄公戴上乌纱帽的那一刻起,“皆由正义统摄一切”便成为了断案的信条,而历经百年,当官帽成为了藏品,当断案成了文献,正义是不是也变成了前朝的某种记忆?所以当“大明盛世”的我头戴官帽在镜子中照见暗黑的人脸,器物崇拜的背后或许是正义的埋没,而天下太平、海内清晏的“大明盛世”也许也是一个镜像般的幻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