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20《摄影机舞蹈习作》:“自然”的完成

一部“习作”,是试验性的影像,是片段的实验,但是却完全呈现为一种“完成”的状态,2分14秒的短片,“完成”似乎对于“未完成”献祭的《女巫的翻绳游戏》而言的——同一天观影,12分钟和2分钟的时长区别,所谓完成和未完成其实都是对于影像本身呈现的叙事而言的,并非是两部影片被置于同一评价体系的人为标准所左右。
梅雅·黛伦完成这部习作,其“完成”的叙事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依然是关于舞蹈的影像,舞蹈激活了身体,舞蹈引出了动作,舞蹈发生了运动,梅雅·黛伦热衷于在舞蹈世界里阐述影像的运动叙事,就在于舞蹈和电影的亲缘性存在,舞蹈是具体的,更是抽象的,舞蹈在时间之内,更在时间之外,舞蹈就是一种“超然于时间之外的整体”,而电影也是如此。在这部短片中,舞者的运动是在摄像机的主动参与中被记录的,这种记录便成为了影像,但是摄影机在这里并非是纯粹作为机器的物的存在,而是以另一种运动的方式和舞者的舞蹈形成了同时的构建体系,也就是说,摄影机在进行着舞蹈的编码,它并不出现在镜头里,但是在跟随舞者的运动中,也以超然的方式形成影像本质的运动,它形成的空间叙事将舞蹈成为一种运动中行进的艺术。
但是在这部短片中,梅雅·黛伦的“完成”还是在叙事意义上的,“一首诗,在我的心中,为一些看不见的东西,例如感觉、情感及形而上的内容,制造可看见或听见的形式。”梅雅·黛伦曾经这样表述诗意的存在,一首诗让看不见变成看见,让听不见变成听见,并非是一种从隐蔽到显明物理状态的变化,而是赋予感觉、情感和形而上内容的表达,而这些内容完全超越了介质本身,“我在试图将图像转译成文字的失败中获得解脱,不像是发觉了另一种介质,而是终于回归到一个词汇、句式、语法都是我母语的世界,我理解且认定它,而我曾像一个哑巴从未说出话。”不说话是默然的状态,但是默然是重新发现语言,重新创造语言,诗歌如此,影像也是如此,它超越了物理状态,也超越了形态本身。
| 导演: 梅雅·黛伦 |
摄影机成为舞蹈的编者,成为舞蹈的一部分,就是这种从看不见到看见的“言说”,而在这部短片中,没有对话,没有背景音,没有旁白,无声的状态就是“哑巴”式的沉默,但是梅雅·黛伦却在叙事中引入了感觉、情感和形而上的内容。电影是在三个场景中完成的,首先是在树林里,男舞者在林中翩翩起舞,他们站立的姿态就像树木一般,而当舞者开始起舞,肢体的弯曲、下蹲、站立,也像树木的摇摆,由此构成了第一重的自然;在摄影机的编码中,舞者的脚步从树林进入到室内空间中,这空间是一出博物馆,这是从自然到人文世界的转变,镜头巧妙地完成了过渡,在自然的过渡中,可以将博物馆纯粹人文的场所看成是第二重的自然,但是这里的自然就实现了梅雅·黛伦所说的转变,它让感觉、情感和形而上的东西变得可见,甚至开始说话——看起来舞者的身体坐着几乎和第一个场景中一样的动作,但是在伸展、转动中,他已经完成了语言的转换:是富含感觉的语言,是具有情感的语言,是触及形而上内容的语言——尤其那个佛像的存在,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信仰的物化?
但是这并不是舞蹈的最后完成,舞者在佛像前不断加快旋转的速度,摄影机又将其带回到自然之中,这是第三重自然,但是这并非是对最先自然的复制,它以嬗变的方式为自然命名:舞者在树林里舞蹈,但已经超越了舞蹈,当最后对着山顶呼吸,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由此构建:从自然出发,经历文化的转变,在被触及了感觉、情感和形而上等的超越中又返归自然,自然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而这也是对于艺术的阐释,它是新的词汇,新的句式,新的语法,由此组成了艺术的母体,并最终在完成的状态中开始言说,而“习作”也终于变成了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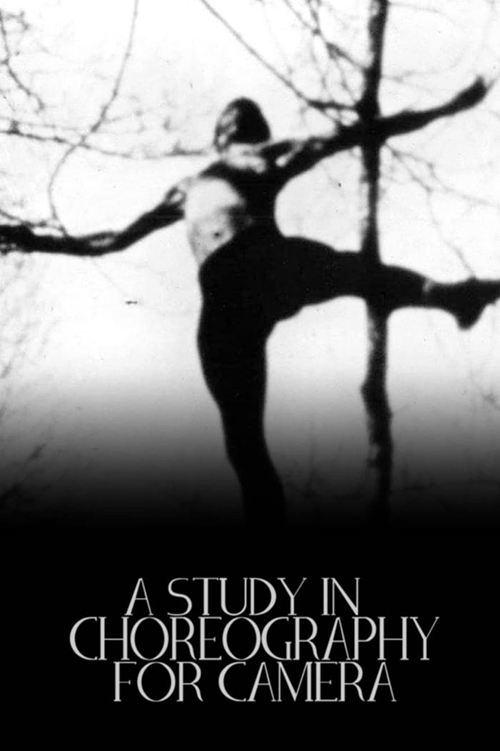
《摄影机舞蹈习作》电影海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