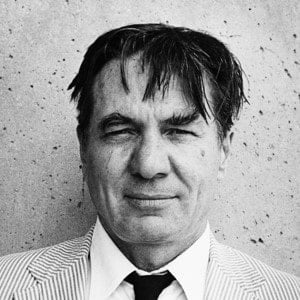2022-09-20《梦魇之书》:死的报酬是爱

这是第十首诗,
最后一首。它在
最后,一
与零
一起走掉,
一起从这些书页的末尾走掉,
一个活物
与虚无相伴离开。
——《十 最后》
最后的诗章,10,由1和0组成,翻过去,便是合上。一本诗集走到了最后,翻过了最后一页,是封底,“啪”的一声并不清脆地盖上,这是一种结束的标志,这是一种关闭的死?“停下。/就此停下。/生带你至死,别无他路。”高威·金奈尔的声音很坚定地响起,却像是很微弱地说着,因为河上漂浮着一具尸体,所以停下来,所以别无他路,所以“一/与零/一起走掉”,一个活物最后从书页的末尾走掉,与虚无相伴而离开。
这是怎样一种“最后”?这是关于一首诗的最后,“这首诗,/如果我们这样称呼它,/或者这场自我/分裂者的音乐会”,背上的虫子在啃噬着“爱人的丝绸”,手臂进入到飞行状态的自由,身为漂浮着,“在遵守必然规律时坠落”——最后是分裂的最后,是漂浮的最后,是坠落的最后,当然,也是死亡的最后。但是诗歌所有的序列都只为另一种出发做准备,合上,关闭,是为了返身,是为了打开,轻而易举的一个动作,它就回到了封面,回到了第一页,回到了第一首:垂死的世界被点燃;一棵树、一只迷失的动物,一块石头进入到光芒之中;或者关于死亡,是生命的重新开始,“第一声渴望/再次从他们嘴里发出。”甚至是死亡成就了这第一声渴望,因为死者已死,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留下,“死者躺着,/至虚,满盈”,就是死亡本身,只有让死亡在至需和满盈中最后离开,第一声渴望才会从嘴巴里发出,一首诗才会从起点开始被重新阅读,而生命,也从第一诗章的《莫德月下》开始。
莫德,高威·金奈尔的幼女,当他以孩子的名字命名这一诗章,对于生命的注解是不是必须从出生开始?刚出生的孩子,又唱又哭,头发在发芽,牙床在开花,“她/把手伸进/父亲的嘴,去抓/他的歌。”这是多么美好而又温馨的画面,但是这首歌注定是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必定和经历过一切的我联系在一起,而生命之降生也成为我所经历的另一个事件:她被脐血环绕,她的身体被门槛夹紧,“那缓慢/而痛苦的挤压,最后一次/塑造她在黑暗中的生命。”最初的生命之歌就奏出了黑暗的音符;之后剪下了黑暗的纽带,倒提起她,拍打她,让她开始哭泣,吸进空气,喊出第一首歌,却是用无羽的胳膊伸向虚无,“她死了”;从生到死,是从死到生的逆转,她死了是因为我们或者,我们死了是因为她活着:“我驻足,/采拾湿木,/折断干燥的幼枝,为她”,点燃小火,在雨中,水又熄灭了火——水和火的誓言被打破,又被宣告,就像灵与肉的誓言,在被打破和被宣告中开启了生命之歌;像是一切被注定了,“我在火边/坐下,在雨中,对着它的温暖/说了几个字”,而石头在雨中唱歌,“我曾用这首歌遮盖/噩梦中的女儿。”
生命之歌是黑暗之歌,是伸进父亲嘴里的歌,是雨中的温暖之歌,是灵与肉的誓言之歌,但更是“磨砺之歌”:“不是穿梭于/天使明亮发丝间的/光之歌,/而是在舌上开花的/磨砺之歌。”磨砺之歌里有光滑的石头,有爱的音符,当然有死亡的奏鸣,“而在未来的日子里/当你失去父母,/失去/任何风的歌唱,任何光,/你舌上只有几片被诅咒的面包”,就会听到“姐妹”的呼喊——它来自死去的万物,而只有等到这一切发生,生命才真正被开启,于是一本书便成为了“梦魇之书”:“那时/你将打开/这本书,尽管它是一本梦魇之书。”
| 编号:S55·2220820·1863 |
第一诗章的《莫德月下》就是高威·金奈尔关于“梦魇之书”的序曲,当融合了灵与肉,当编织了水与火,当注解了生与死,开启的“梦魇之书”就是关于生命的磨砺:从生开始的磨砺,其实死亡也是生,生也是死亡。题辞所引用的里尔克诗句就说明了高威·金奈尔的这种生死构想:“尽管如此,但是:死亡,/死亡的全部——即便在生命开始之前,/如此温柔地捧着它,好好地:/这无法描述!”生命开始前的死亡,死亡之后的生命,无法描述,高威·金奈尔却要在最先和最后的十个诗章中描述,是要将死亡的全部都书写出来?是要将生命的温柔都捧出来?从死到生从生到死,磨砺之歌又如何被唱响?《母鸡花》渗透着高威·金奈尔自我关于生与死的记忆,“记得很久以前,我把/第一颗乳牙/播在母鸡羽毛下,把叉骨之钩/种在母鸡羽毛下,/那块叉骨曾动人地向我分裂开来。”这些动作都是“为了未来”,而其实“母鸡花”这一意向所承载的也是死亡和黑暗:“将头/甩向身后/的剁板,只渴望/死。”而死亡的同时呢,一颗蛋,一颗金黄的地球所产下,是她的“来生”——在母鸡花身上,感受着死亡的“第一缕阴风”,像那个零,冻僵了手指;但也是那枚蛋变成了一,为了未来,走向未来。
“听着,金奈尔/你被抛在/这古老的摇床上,活着/又在死去”,这是高威·金奈尔在“母鸡花”中听到了磨砺之歌,关于生命的生与死、零与一、飞翔与坠落。而在《流浪的鞋》中,那种记忆已经从观察变成了行走,谁穿着流浪的鞋?鞋子为什么会流浪?“现在我穿着死人的鞋/走出去,在新的光线里,/在别人流浪的/踏脚石上”,转弯或者停下,迈步或向后,别人的鞋,死去的鞋,行走便成为一种死亡的延续,就像巫婆所说:“第一步/即为迷途”。迷途或者正是为了开启磨砺之歌,只是这一种磨砺是从别人世界里获得的认识,“我会呻吟//或喘息,而那将是/另一个人的呻吟或喘息”:另一个可能是屋子里死去的酒鬼,可能是从亚洲火堆里运回来烧伤的兄弟,或者袒露过自己过失的男人,他们遭遇了人生的变故,一双鞋是一个人故事的记载,它当然经历了磨砺,“整天摩擦着鹅卵石/和菊石,/这最卑微的/舌,用舔痕/把我们错误的历史告诉后面的尘土”,这是可能展开的之翅膀,也可能如母鸡一样的噩梦。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另一双鞋提供了人生的文本,“我渴望获得伟大流浪者的/斗篷,他们/用纯粹的饥渴之灯/点亮自己的步伐,//且无论踉跄到哪里哪里就是路。”
《母鸡花》和《流浪的鞋》几乎构筑了同一种磨砺的文本:死就是生,这一个就是另一个,磨砺的介体就是母鸡的命运和一双鞋的流浪,但是从《蓝色朱尼亚塔边亲爱的陌生人在记忆中尚存》的诗章开始,高威·金奈尔开始寻找属于人类普遍的记忆。这种记忆是迷失,以“你的,对此生不忠的,/弗吉尼亚”为名写给高威·金奈尔的信里提到了上帝,提到了自己,“上帝,我想,我的呼吸急促,心开裂,噢,上帝,我想现在我有了个魔鬼情人。”后来的第二封信写信人变成了“你的,身陷黑暗的,/弗吉尼亚”,而上帝变成了自己的敌人,“他给我欲望和喜悦,他砍掉我的双手。我的大脑被他的血液窒息。我问为何我需要爱这个令我害怕的身体。”上帝要杀死的是人的盲目,而陷入盲目的弗吉尼亚走进了迷失。这种记忆也是背叛的记忆,曾经,“我们对永恒之爱的渴望/散落下来,一粒接/一粒,落入最后/最冷的房间,也就是记忆”,相爱的朋友在哪里?爱过的人又在哪里?他们,“三圣颂钟声/每小时在这座钢筋玻璃之城死一遍”。在迷失和背叛的记忆中,在爱的异化和对上帝的敌视中,磨砺已经变成了对人类的普遍拷问,“这难道是真的——/所有身体,是一个身体,一个光/由所有人的黑暗组成?”也许,对于这一份普编之记忆的保存,就是:“让我们的伤疤相爱吧。”
一个人的身体是所有人的身体,一个人的黑暗是所有人的黑暗,弗吉尼亚的迷失是所有人的迷失,高威·金奈尔的记忆是所有人的记忆,个体的经历和遭遇变成了人类的生和死,所以向前,“母鸡花”也是所有人的母鸡花,另一个人的鞋子也是带着所有人去流浪——或者在这个时候,普遍性构筑的才是人类的梦魇之书。《在失去光的旅店里》诗章里是苍蝇,是小蜘蛛,是虱子,是蛔虫,它们成为人类的一个隐喻:
我依偎着在鸡腿的浓油中四溅的细火,
我昏厥于路旁勿忘我开放的裂缝边,
我看见游乐场的转轮用霓虹在夜空书写巨大孤寂的零,
我把脚心涂紫为了在某一天展现这美丽的颜色,
我摇晃着死亡判决书走过空荡街道,鹅卵石向我保证:“你在劫难逃”,
我听见自己的叫喊已在冲上岸的瓶里哭嚎,
我把祈祷鬼书于噩梦的肢体语言中。
这个关于噩梦的笔记抄录于“七零年三月”,这是“我的第一万六千个战争和疯狂的夜晚”,生命被拉长到一万六千天,却被注解于战争和疯狂的夜晚中,人生便在“失去光的旅店里”,滑向最后的噩梦。这是高威·金奈尔个体的生命序列,但是一个人是另一个,一个人是所有人,一万六千个战争和疯狂的夜晚也是所有人的战争和疯狂的夜晚。《死者将被唤起永不堕落》是高威·金奈尔对黑暗的噩梦揭露最深的一篇诗章,对于经历过战争又加入反战组织的高威·金奈尔来说,这是他对于战争之恶的无情批判。“中尉!/这具尸体仍在燃烧!”从一句话开始,从一个悲剧和一场灾难开始,死亡成为人类的噩梦——而在高威·金奈尔的笔下,这种死亡的噩梦从杀人者的口中被讲出更体现了它的悲剧性:“记得北边/那个伞兵吗?/我把他射到只剩肠线挂在降落伞上,/每晚我一吃下安眠药,/他的一只细眼,一片/笑,就会从我面前浮过……”一发发的子弹,一只只的眼睛,一片片的笑,以及一次次的死亡,都是战争带来的复数灾难,甚至不仅仅是战争:
在我擅自闯入地球的第二十个世纪,
已处决了十亿个异教徒、
异端分子、犹太人、穆斯林、巫婆、术士、
黑人、亚洲人、基督兄弟,
他们都咎由自取,
处决了整个大陆的红种人,因为他们不但生活方式不自然
还与这片土地依依相连,
处决了十亿种动物因为他们比人类低贱,
并已准备好了对付嗜血的外星生物,
我,一个基督徒,在呻吟中宣布最后的遗嘱。
|
| 高威·金奈尔:梦魇之书也是磨砺之歌 |
十亿个异教徒,十亿种动物,在“一个”基督徒面前,呈现出何种增殖式的悲剧?而单数的“一个”又如何在最后的遗嘱中救赎?血液留给天空中最后的轰炸机飞行员,舌留给死亡的迷树,胃留给印第安人,灵魂留给蛰完就死的蜜蜂,大脑留给吸食疯癫黏土的苍蝇,肉留给广告商,弯曲的脊柱留给骰子投资者,“在这地球第二十个世纪的/噩梦里,我以我闪亮的睾丸的名义/宣告这份遗嘱/和我最后的/铁的意志,我的爱之惧,钱之痒,我的疯狂。”这一个的遗嘱是人类善的最后微光,是基督徒的最后救赎,但是在数以亿计的死亡面前,“那只苍蝇,/那最后的噩梦,孵化着自己。”最后喊出“中尉!/这具尸体仍在燃烧!”的又是谁?是不是另一个制造和见证了死亡的基督徒?是不是另一场制造了灾难的战争?无休无止,复数增殖为更大的复数,“一个”早已在“第一万六千个战争和疯狂的夜晚”成为可怜的符号。
高威·金奈尔揭露战争等人类之恶的书写是振聋发聩的,它以复数的死亡、复数的噩梦将一切变成人类所有人的“噩梦之书”,但是这也是人类必须经历的磨砺之歌,而磨砺的意义是在死中看见生,是让变成生的一部分——再次回到《沉睡的小脑袋在月下发芽》的“莫德月下”,再次从死亡的生开始思考生命和爱,再次唱起磨砺之歌:“沉睡的小脑袋在月下发芽,/等我回来时,/我们将一起出去,/一起走在/万事万物里,/并总将过迟地明白这个道理:‘死的报酬/是爱。’”死的报酬是爱,是高威·金奈尔这本《梦魇之书》最后的主题,生从死中而来,爱在生中产生,所以死亡所对应的是生命之爱,它是莫德在月下唱起的歌,它也是“穿越莫知山谷的呼唤”:“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分裂的一半,/去寻找失去的另一半,/直到死,或放弃,/或真的找到她”。有过伤害,有过离别,但是最后,“两个陌生人/紧紧拥成一个,在地球上的一瞬间。”
生命和爱,在死亡之后磨砺而形成,就像石头,“巨大的黏土星座伴着满月/为沙粒裹上又一层/无形之衣”,它们是牧场的石头,是田野间的石头,是破碎的石头,但也是坚毅的石头,留下花纹的石头,“将自己给予生者/破碎的心,/而生者,把破碎的自己,还给石头。”是凝结,是煅烧,是成型,石头的叙事中有生与死,有破碎和完结,有沉默和永恒,它最后区分的是上面和下面:
上面:最后几颗散布的星
以宝瓶座的形状跪下:
将几滴水
泼在头顶,
在这连星星都热爱的地球的草场上,泼洒神圣的水……
下面:坟地里灯开始点亮,每一盏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石头的
每一扇窗里。
最后是回归,回到幼子弗格斯身边,回到生命的诞生上,回到最后离开的到来,“他用痛苦的/几乎黏合的眼睛斜视/溅落地板的九月之血。而我/几乎笑了,几乎预先原谅了一切。”这便是“第一声渴望”,生命的渴望,爱的渴望,在死的报酬中完成关于梦魇之书的最后命名,“在这具尸首上,/在这摊泛蓝的肉上,/看你能否找到/一只发笑的跳蚤。”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