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0《梼杌萃编》:惟有使人各适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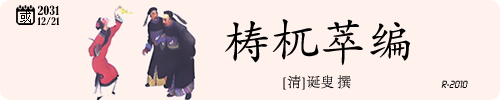
看他到著末一回,结句还是“且听下回分解”,心里想道:“这部书到底完了没有呢?”
——《结束》
以“缘起”为始,以“结束”为末,构成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封闭结构,这封闭结构共有十二编,十二编分别以禹、铸、鼎、温、燃、犀、抉、隐、伏、警、贪、痴命名,每编分上下两回,十二编共计二十四回,组成了《梼杌萃编》的完整性,但是完整性又通过最后一回“且听下回分解”这种中国章回小说的特有表达所打破,也就是说,小说还有未完的故事,还有后续的情节,对完整性的解构,似乎都像抱真子一样发出疑问:“这部书到底完了没有呢?”
署名“诞叟”所作的《梼杌萃编》其实有着同时代小说没有的“先锋结构”,缘起和结束独立于故事之外,它构成了一种“别册”,而这一“别册”又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诞叟在这里创造性地使用了嵌套结构:十二编二十四回构成了最内部的部分,它是小说的主体,而缘起和结束两回又内在地解释了这部小说,它既独立又融入其中:诞叟和抱真子是莫逆之交,抱真子去上海游玩了几天后回来和诞叟在汉口话别,在讨论了酒色财气的生活害人与否的讨论之后,诞叟就提到了朋友写的一部小说,“我初次看了一遍,见他既没有朝代年月,又没有关涉治乱兴衰的事业,也没有格致算化的学问,并没有甚么诗词歌赋、酒令灯谜;而且写到男女闺房之事,虽不致蹈那些淫书的恶习,也有些觉得形容太过的地方,那笔墨似乎还不及《品花宝鉴》、《花月痕》呢,也就把他放开了。”但是因为正契合两个人讨论的话题,于是诞叟就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抱真子,让他消遣消遣,当抱真子拿过书十二本白纸毛边的抄本,发现就是十二编的这部小说。抱真子看完书之后,也推荐给茶馆的主人,主人看了书之后,问他要不要排印出来,抱真子同意排印,但是书没有名字,于是馆主人给书取了名字,“既然你说这书上没有一个好人,就叫他做《梼杌萃编》罢!”
在缘起是提到了这本书,在结束中最终给书命名最终排印,也就是说,《梼杌萃编》是在故事讲述中成书的,而故事本身就是《梼杌萃编》,所以,在结构上,《梼杌萃编》既是包含十二编二十四回的故事,又是更多包括了缘起和结束的小说,这就是嵌套。而且这种嵌套并不只是在文本意义上,比如书中写到的诞叟就是这本书署名的作者,故事中的贾端甫是抱真子认识的贾端甫,任天然则是抱真子在船上认识,抱真子甚至还拿着写着任天然故事的小说给任天然看,“前回在上海,有个朋友拿了一部书与在下看,内中有一位的姓名与天翁相同,就连如夫人的芳名亦复一字不差,此次去游嵩岳,这书上也叙及的。这是甚么缘故呢?”任天然觉得诧异,也拿起了小说翻阅,的确看到了同样名字而且就是自己的任天然,“这书上所说的任天然自然是我了,叙我的生平事迹虽然不能十分详细,大致也还不差”,也正是这样,任天然解释了书已完结却未完结的奇特之处,但是这书上的人,就我所晓得的,还有一大半在世上,以后的穷通正未可知,你教他做书的怎样替他归结?自然只好‘且听下回分解’了。”不仅如此,抱真子除了在缘起和结束之中成为主角,在故事部分的二十四回中也有他的身影,第一回就讲到抱真子打开那本书,发现里面的贾端甫就是自己所认识的甘肃臬台,“他是个有名的暮夜却金、坐怀不乱的君子,怎么也被这人编入小说里头?”同样在故事中的诞叟就告诉他:“你到船上慢慢的看梼,这书也并未埋没了他的好处。”正是这种过渡,从缘起进入到故事中;在第五回的时候,插入了抱真子阅读之后的一番感悟,“这部书上做官的法子最多,稍为学点,宦途总可得意的。但不知这做书的他到底做过官没有?他做官又是用的甚么法子?”抱真子带着阅读中的疑点,“几时见着诞叟,倒要问问看呢。”
故事中的人物又在故事之外,故事之外的人物又被编排在故事之中,由此构成了小说的嵌套结构,这的确是小说形式上带来的革新,甚至是一种惊艳。而回到抱真子关于这本书既完结又没有完结的疑问,嵌套结构又具有了结局的更多可能性,任天然看了书之后,认为自己就在书中,很多人也都在书中,而且他们的故事并没有归结,也就是说,人物和故事都在一种发展过程中,这种正在发展的过程其实表达了诞叟对“梼杌”进行时的态度,“就是这书里叙的几件新奇怪诞的事体,虽为理之所无,却为世之所有,并非全由捏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故事所反映的主题适合现世,那么站在当代性的意义上来说,诞叟要作这一本小说就是为中国的现状寻找一条可能的出路,正如他在缘起中交于抱真子所说,小说“没有朝代岁月”,正是预示着正在发生的故事,而故事围绕着酒色财气四个字,也成为诞叟对中国如何更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一种态度。
在缘起时,诞叟和抱真子讨论了这四个字的生活,抱真子因为在上海游玩时花天酒地,起初感觉快心,但是后来渐生厌倦,所以他认为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是一种害人的生活。但是诞叟予以了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酒为用有限为害当然也不多,气是因为财和色不平而起,也不是害人之因,所以四个字关键就在财和色上面,他认为看起来它们害人,但是如果没有更害人,引用古籍中的说法,“有财此有用”、“无财不可以为悦”“食、色,人之性也”“未见好德如好色也”,这些说法并不是说财色害人,反而是必不可少的,“那除非叫这五大洲的人皆人了佛家寂灭之教才可,那还成个甚么世界呢?”诞叟甚至就拿眼前两个人对坐饮茶来举例,如果没有财,“并此几间破屋、两盏清茶都不能办,岂不成了两个乞儿荒郊对语,试问有何趣味?”同样,如果没有色,人种不是就灭绝了,诞叟还认为,既是所谓的淫也有其作用,“不淫无以申其情,无情不能动其好。”淫中也含有情,而情更是男女相悦,“不但风流才子、慧业佳人往往由他作合,就是那些蠢女痴男野田草露,也未尝没有这‘情’字行乎其间,情愈深则好愈笃。”
| 编号:C25·2240826·2169 |
从反向来论证,诞叟认为,如果在财和色上面不能如愿,就会生出很多是非,“或则忧伤憔悴,夭折其生;或则背礼败常,自罹于法;甚而至于愍不畏死,酿成犯上作乱之事。”还有人受了折磨耐了凄凉,最后甚至造成了矫揉造作的戾气,“小则殃及身家,大则为害邦国。实按起来,比那愍不畏死的为祸还要烈呢。”诞叟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阐释,然后又找出了财色问题的根源,“推原其本,君相亦不得辞其责。”对于这个说法,抱真子颇为不解,个人的财色问题难道还和君相相关,难不成要国家按人头“分给家资,选择配偶”?诞叟解释说,君相之责就在于君相要使举国的人各有专业生计,“足以自生其财,自得其色,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实际上,缘起中诞叟所说财色是一种必需,是基于缺乏而言的,因为缺乏所以为害,而不是有了而为害,但是无论是抱真子所说,还是小说中所述,真正的问题是过多的问题,积财过多是一种害,因色而淫而放纵也是过多的表现,当然是一种害。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变成了财和色到底多少才是适宜的?这个适宜问题,诞叟就从个人事务相关问题变成了国家礼仪的诟病,“中国婚姻多由父母作主,男女一面未识,试问从何生情?到了合卺的时候,以为理所当然,兀足为喜,那情自然薄了。”在诞叟看来,中国古来婚姻理想的状态是由男女自主,“寤寐求之”、“求我庶士”就是这种理想化的表达,如果这样,彼此无情何必去求?但是中国社会却慢慢走向了因情制礼、以礼废情的现实,如此便出现了现在的流弊。无疑,这里诞叟的观点也是对于“君相之责”的一种补充。
小说展开之后,以贾端甫为主人公的故事就在这多和少、有和无、求之和拒之之间摇摆。贾端甫死了父母之后托亲友找了个馆地,为师爷的孩子破蒙,后来去了酒馆,就看到了色的一幕,增二少爷堂而皇之去摸丫鬟小银珠的双乳,桂云在炕上替周师爷大烟,文卿则趁人不见拉着龙少爷到自己房里去了,只有贾端甫一个人坐着,颇感凄凉,回到住处贾端甫就心里不平衡了,“同是一样的人,他们有钱有势,就如此快乐,如此光辉。我一介寒儒,不但没人理睬,还要被这些浪子淫娼奚落嘲笑,怎能有一日让我吐一吐胸中的这口恶气呢!”但也只能自己生闷气,但是后来出恭的时候捡到了杨姨妈的茉莉针,杨姨妈正是背着丈夫和毛升鬼混,不小心丢了茉莉针。当她发现贾端甫手中的茉莉针,才知道自己的事被他知道了,于是杨姨娘开始勾引贾端甫,而贾端甫正苦闷中,所以一个是浑身欲火发动,一个则是放出胯下英雄——但是,“这书再照这样作下去,那就成了《金瓶梅》、《肉蒲团》了。”诞叟果断叫停,他通过贾端甫的自省而终结。
一方面贾端甫认为杨姨娘勾引自己只是因为自己撞见了他们的私情,所以用来塞自己的嘴,另一方面,贾端甫认为自己是个秀才又是处馆的,如果做了就会败了名声,“不如现在忍一忍欲念,将来被人家晓得,我还可以落一个夜拒奔女的美名,何苦贪恋这一息息的欢娱呢!”不仅自己忍住了欲念,而且还斥责杨姨娘,“我一个圣贤子弟,几乎被你这浪货所误!我同你家老爷是多年宾主,你的儿子、女儿都是我的学生,你怎好这么无耻呢?我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不比那些奴颜婢膝的家人,你拿我当作甚么样的人看待?还不快替我滚出去!”这是贾端甫维护自己名声守住节操的证明。后来贾端甫科考,居然考了个一号第二,有人变来说媒,女人是周姑娘,这周姑娘禁不住浴火和白小官勾搭,白小官又离她而去,伤心之时正好说媒的将她说给了贾端甫,而贾端甫并不知道周姑娘的风流韵事,认为自己是一一介寒儒,有人嫁给自己也是福分,于是也就答应了,“难得这么一位富翁丈人可以招赘上门,不但自己目前免了孤单,日后也还有个依靠;而且那个小官听说已不知流落何地,这事有无也还没有甚么实在的凭据,怎好因旁人蜚语,误了这美满良缘?”于是结婚,后来还生下了女儿静如,可以说,在这里贾端甫又表现出一种“善举”,而且他从此深恶烟花,绝迹不入青楼,“有人同他谈到风月闲情,他不是正言弹驳,便是掩耳不闻。”
中了进士之后,贾端甫又在贺宴上对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将来我放了外官,我那衙门里可一个官亲也不用。倘各位高亲以俗情相待,到那时远道见访,不要怪我贾崇方无情。不但衙门里不能破例位置,就是盘川也分文不能送的。宁可将来回家多多尽情负荆请罪,在官的时候可不能不恪守官箴的呢。”贾端甫将官亲看做是衙门最坏的事,所以他采取了全然拒绝的态度,让乡亲断了念想,这也是贾端甫不失操守的表现。后来增朗之为了从贾端甫那里得到好处,要用金钱贿赂贾端甫,贾端甫拒绝了,并且对增朗之说:““我们读书做官的人,这操守二字是最要紧的,就同女人家名节一般。我虽是个寒士,却向来于这些上头最有把握,通籍两三年来,从未受人家丝毫非分之财。岂不知道这部曹是个穷京官?”贾端甫暮夜却金更是传为美谈。可以说,贾端甫的种种行为都可以说是道德典范,甚至成为了小说中的“好人”。
但是在宦海之中,贾端甫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好人,诞叟再现了官场的腐朽淫靡、放荡庸俗的生活,上至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总督、巡抚,下到藩台、(臬司)、知府、县令以至管家、奴仆,对金钱、权势、女色无止境的占有欲望,写尽了财色为害的故事,其中第十回就写到了骇人听闻的一起案件。范星圃成为臬台之后,从孝廉那里搜出了重要的册子,孝廉夫人知道丈夫保不住命了,自己又在公堂上被人乱摸,于是一头撞向了阶前石上,血液横流,脑浆进裂。孝廉被带上堂之后就咒骂范臬台,“你做臬司,执法是你的义务,那也不能来怪你,你却不应该设这些阴谋诡计,锻炼周纳的害这许多善类。”孝廉一针见血指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贪图升官发财,以博取闺中妻妾的欢欣,无疑就是被财色蒙住了双眼。范臬台搜查到了这本册子,就可以知道谁是保皇党谁是革命党,长沙府保善从范臬台那里骗取了册子,发现里面一半人是学堂里的学生,“这本册子留着,照着这册子一个一个的拿起来,不知要连累多少人!不如我拼着一官,救了这些人的急难罢!”就把这册子烧了。他的这一行动就是保命,连抚台也出来为他解释,“这种会匪的事体重在歼厥渠魁,若要把那些胁从、附和的人一一追究起来,必致弄到人人自危,万一激出点变故,岂不好,不如记他两过,使大众知道这本册子已经被他烧去,那些被人哄骗的也可以安心悔过。”于是范星圃随风就转也不再追求,所谓四境平安也就是这种非法勾当的结果。
不管是贾端甫的道德操守,还是范星圃的见风使舵,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就是官场的自保术,而诞叟之所以讲述财色的故事,其实是在表达维新和守旧的问题,厉尚书曾对贾端甫说起百日维新的事,他认为这是要废祖宗成法,“我们是老旧无能的人了,且看他们这一班维新经济的好手怎样支撑这个时局罢!”贾端甫当然也是维护这样的利益,“朝廷虽一时求治,太急用了他们这些新进喜事的人,久后必定还要念及‘人维求旧’的这句古训,倚重老成典型的,藉此暂时怡养怡养也好。”而通过魏太史的话,道出了政治上的专制之必要,““他们讲新学的总说不可用专制手段,其实天下事非专制不行。就是他们外国,说起来呢有甚么君主、民主、立宪、共和的分别,替他按实了考较起来,也还不是这专制的主义!”所以和守旧一样,专制才能维持秩序,“若讲到治家,更非专制不可,若不专制,儿子不服老子的管教,妻子不受丈夫的约束,那还成个甚么人家呢?”
诞叟无疑是对守旧和专制持批评态度,所以财和色的必要性其实也是追求革新甚至是自由的意愿,回到贾端甫最后的命运,妻子和女儿的淫荡最后都付出了代价,所以诞叟提出了这个问题,“贾端甫如此一位道学先生,家政又如此严肃,怎么他的妻子儿女会得如此淫荡呢?”在他看来,这就是专制的悲剧,不是贾端甫治家不严而是太过专制,“不知道天下的事体无一样可以强制的,只有顺性而导,使他涵濡于不觉,自能就我范围;若去逆而制之,就如抟沙遏水,必致溃败决裂。”专制带来的就是缺少,一旦被打开就会造成决裂,“男女身备淫具,他不动欲念则已,动了欲念,铜墙铁壁不能限他,刀锯斧钺不能禁他,只有愈遏愈炽的。”因为专制而抑制欲望,因为抑制了欲望所以会爆发,这是从极少到极多的双重问题,所以在引入外国观念提出维新思想的时候,诞叟又将其变成了中庸,那就是适宜,“有鉴于中外家国历来变乱,无不由于防制太严,惟有使人各适其性,方能消患未萌。而且人生处世,无论何人,总宜待之以诚。”如果能各适其性,那么妻妾子女就各循其分,国家秩序也会在礼法中得到维护。
所以诞叟故意以未完结的方式完结,就是让这条“各适其性”的金科玉律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取名为《梼杌萃编》就是让故事里的人物都成为坏人,以坏人的故事反坏人,正如结束中任天然最后的解读:“不过细看他这部书里的皮里阳秋,大旨是宽于真小人而严于伪君子,这还不失天地公理。倘然传到世上,是书中的人,看了固应汗颜;自返不是书中的人,看了也可触目惊心,于世道人心也还不无小补。”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