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1《金陵旧事·凤凰台记事》:今古帝王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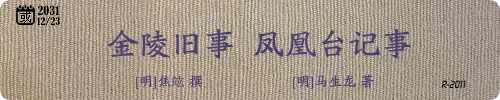
胡综博物。孙权时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义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莫能识其由。使人问综 综曰:“昔秦皇以金防天子气,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气。此盖是乎?”
胡综为三国时东吴官员,少年时避难江东,十四岁时在孙策属下做门下循行,在吴郡与孙权一起读书。东吴将领晋宗判吴降魏,胡综与贺齐生擒晋宗,后来孙权进封吴王后,封胡综为亭侯,孙权称帝后,胡综成为侍中,进封都乡侯,与徐详兼左右领军,后拜偏将军,兼左执法,领辞讼。孙权接手江东后,很多诰文、策封任命文书和致邻国的书函都是出自胡综之手,而当筒匣被发现之后,博物的胡综便识得此物非同一般,他认为这是秦始皇时留下的宝物,一句“以当王气”不仅指出了这一铜匣的宝贵之处,更是间接指出了当时作为东吴都城的健康的王者之气。
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而东吴建都的建康正是六朝古都的起点,所以从这个起点发现玻璃为盖的白玉如意,就是暗示着王气的回归,这也是对南京最好的定位。和秦始皇有关的这个说法,也恰好是“金陵”的由来,《元和郡县图志》载:“本金陵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都邑之气。故秦始皇东游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金陵之“金”,史书载:“楚子熊商败越,尽取故吴地。以此地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号曰金陵。”两种说法都指出了“金陵”之金是一种埋没,但是在几百年之后,孙权掘得了铜匣,使得王气,由此开始了“六朝古都”一段辉煌且遗恨的历史。
焦竑在本书的首条就记录了晋元帝时的天象,“金陵为斗分。晋永嘉中,岁星、荧惑、太白聚牛女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间当兴王者。”晋元帝在此定都,“星斗呈祥,金陵表庆。”这一天象也预示着王者之兴,“星斗呈祥”似乎和孙权发现铜匣恰好形成了呼应,地下之物和星斗之象都指向了“王气”。焦竑之后引用了宋代王野所写的《六州歌颂》两阙,更是在“咏金陵”中对“金陵旧事”进行了抒怀:
龙蟠虎踞,今古帝王州。水如淮,山似洛,凤来游。五云浮。宇宙无终极,千载恨,六朝事,同一梦休。更莫问间愁。风景悠悠。得似青溪曲,著我扁舟。对残烟衰草,满目是清秋。白鹭汀洲。夕阳收。
黄旗紫盖,中兴运,钟王气,护金瓯。驻游跸,开行殿,夹朱楼。送华辀。万里长江险,集鸿雁,列貔貅。扫关河,清海岱,志应酬。机会何常,鹤唳风声处,天意人谋。臣今虽老,未遣壮心休。击楫中流。
“龙蟠虎踞,今古帝王州”这句可以看做是对金陵作为王者之城的表达,但是王野在时过境迁中也充满了“对残烟衰草,满目是清秋”的哀伤,焦竑引用这首体现金陵的过去和现在的诗词,他用了“读之亦自爽然”的感受,这“爽然”也是焦竑作为明代士大夫“臣今虽老,未遣壮心休”的心怀,而实际上,在“星斗呈现”开创的六朝古都时代,金陵也处在南北分裂之时,政权变更频繁,金陵也被渲染为残烟衰草、千古遗恨的六朝意象,但是在焦竑看来,即使在鹤唳风声处,也依然是“龙盘虎踞”之地,所以一本《金陵旧事》更多是焦竑在辑录南京的“旧事”中寻找“今古帝王州”的依存的王者之气。
| 编号:Z67·2240826·2168 |
这里有齐永明九年种在秣陵安明寺的古树,“伐以为薪木,目然有‘法大德’三字;晋时徐景在宣扬门外得到一锦麝橙,“有虫如蝉,五色,后两足各缀一五铢钱”;愍帝建兴四年,有白玉麒麟神玺出于江宁,其文曰“长寿万年”,这是江宁县名字出现的年份;江宁县寺有晋朝的长明灯,“岁久火色变青而不热。隋文帝平际,已讶其古,至今犹存。”茅君种在句曲山的灵芝“实坠地如七寸镜,夜视如牛目”,而且句曲山有五芝,“第一芝名龙仙,食之为太极仙;第二芝名参成,食之为太极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科玉,食之为三官真御史。”汤山西边的云穴山,“汤泉出其下,大小六处,四时常热。”这里的温泉有奇特之处,“禽鱼之类,人者辄烂。以煮豆谷,终日不熟。草木濯之,愈鲜茂。”茅山玉晨观的许长史旧宅有一口井,“色白而甘”,徐鼎臣曾经作铭:“—长史含道,栖神九天。人非邑改,丹井存焉。射兹谷鲋,冽彼寒泉。分甘玉液,流润芝田。我来自西,寻真紫阳。若爱召树,如升鲁堂。敬刊翠琰,永识银床。噫嗟后学,挹此余光。”
印有“法大德”的古树,缀有五铢钱的五色虫,岁久不热的长明灯,夜视如牛目的灵芝,四时常热的温泉,色白而甘的古井……这些都构成了金陵独特且奇特的“旧物”,它们像是金陵有关的传奇,却在焦竑的笔下成为城市的某种隐喻,而《金陵旧事》就是讲这些“旧物”重新发掘出来的,在这本书中,很多旧物的确被掩埋了多年,却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御史刘焘曾经说金陵有高正臣书,埋没与园圃之中,回来他的父亲果然发现了它,“其字画殊有虞、褚法也。”茅山华阳宫有一口陶隐居井,岁久湮没,后来道土庄慎修索得之,“去三尺许得瓦井栏,虽破,合之尚全。”这里曾是吴国之地越,当时的吴国“将图楚,称霸江淮”,于是“筑城于长干里”,而现在这一段废城就在秦淮南一里半的地方……它们有的已经淹没,有的已经消失,但是总会被人发现,而这或许就是金陵之城的特殊性所在,就像《图经》所说:“金陵者,洞墟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其土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则浮,故曰地肺。”
焦竑辑录《金陵旧事》,也是发现和发掘,所谓“旧事”,就是将“旧物”和建立关系。《金陵旧事》摘录的六朝人物史事最多:葛洪曾结庐方山,山上有洗药池,葛洪有诗云:“洞阴泠泠,风珮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长荣。”南朝齐梁时期的阮孝绪,母亲生病须要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只有在钟山能找到,阮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获,忽然有一天看到了白鹿导之前行,“至一所,不见。就求之,果得。”米芾有洁洁癖,择婿的时候闻建康段拂字去尘,米芾感叹说:“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最后把女儿嫁给了他;吴人陈焦死去之后埋了六个月,不想,“更生,穿土而出。”在《金陵旧事》中,焦竑两次提到了“谢公墩”,一次是论证谢安登临处在冶城之北,“谢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吴王夫差冶铸处,宋为天庆观。今朝天宫、铁塔寺、谢公墩一脉绵亘,皆其地也。”《世说》和谢灵运《撰征赋》也都有记载,另一次则是考证王安石“我屋公墩”句乃其自城西北铁塔寺箨龙轩望谢安墩所作,王安石于半山寺营居时,以其地为谢公墩,故诗中有“我屋公墩”之句,引发后人争议,焦竑好友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也考证过谢公墩的具体位置,顾氏认为王安石“我屋公墩”句乃指城东半山寺之地,因其误将谢玄居处当作谢安登临处,焦竑由此发出疑问,他用李白《登冶城西北谢公墩诗序》云:“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義之同登处,予将营园其上,故作是诗,云:‘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公墩。凭览周地险,高标谢人喧。想象东山姿,缅怀右军言。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焦竑认为,李白的观点已经很清楚了,他又在介甫之前,“《世说》与太白诗证之,纷纷之疑尽破,亦何必凿空指谢公他子孙为说耶?”
除了这些名人轶事之外,作为藏书家,焦竑特别关注六朝时期江南藏书、刻书情况,并记录重要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乃至手工匠人。朱遵度好藏书,隐居不仕,卜筑金陵,著有《鸿渐学记》《群书丽藻》《漆经》,皆行于世;齐时立儒馆于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开馆于鸡笼山,高帝曾经受《礼》及《左氏春秋》;竟陵王子良移居鸡笼山下后集四学士,抄五经百家为《四部要略》千卷;当然焦竑对王谢世家“衣冠之盛,为江左第一”的文化遗产也深感自豪,“谢以文学世其家,有集,安石而下,历宋、齐、梁、陈,凡十有六人,诗三百四十余篇,为《谢氏兰玉集》十卷,吴兴汪闻为序。”江南府库之中,还有“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集贤殿书院印”印记的书画,“以墨印之,谓之金图书,言惟此印以黄金为之。”在《金陵旧物》的最后,焦竑辑录了和金陵有关的人物表,按照生于此、居于此、职于此、墓于此、祠于此和封于此分类,比如周朝“职于此”的历史人物有范蠡,“越上将军,筑越缄。”“墓于此”的则有左伯桃,“祠于此”的又羊左庙;晋朝“生于此”的人物包括纪瞻、薛兼、张闽、许迈、葛洪,“居于此”的则有王导、谢安、纪瞻、谢玄、卫玠等,“职于此”的有陶潜等,“墓于此”的有王导、温峤、谢安、纪瞻、卫玠等,“祠于此”的包括王导、谢安、刘琨、祖逖、纪瞻、司马承、卞壶、王羲之、王述、谢石、谢玄、陶潜等等。这些人物构成了金陵的系谱学。
无论是山川形胜、释道仙人、异闻奇谈,还是人物事迹、典章名物、文史经籍,焦竑在《金陵旧事》中摘录的六朝、南唐、南宋时期与金陵相关的各类知识,展现的是他对金陵历史、地理及人文传统的深切关怀,一方面和自己的旨趣有关,另一方面则折射出明中后期南京士大夫的集体心态。《金陵旧事》中焦竑摘录的山川盛景除了核心的青溪、秦淮、钟山、茅山外,还包括鸡鸣山、清凉山、覆舟山、三山、摄山、汤山、东山、莫愁湖、新林浦、潮沟、新亭、赏心亭、龙洞、越王台、谢公墩及寺刹道观等,这不就是和当时盛行的雅游、选胜之风深为契合?明代万历时期,南都士大夫与僧人交往频繁,甚至有“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为雅”的看法,而焦竑雅游之趣也受到了家庭的影响,焦竑曾言,其母“善病,厌药饵,喜祷祀,岁则四五举”,其父晚年亦“弃人间事,味方外言,延诸比丘,向往西极”,所以焦竑也喜欢避世,而在摘录的笔记中,很多还是一些怪力乱神的事,这其中就有两则和金陵有关的成语典故,一是江郎才尽,江淹梦见自称郭璞的人,他对江淹说:“吾有笔在公处多年,可见还。”江淹在怀中得五色笔,郭璞授之于他,“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谓之才尽。”另一个则是画龙点睛,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画四龙,画完后不点睛,有人让他点上眼睛,“顷刻雷电作,二龙乘云腾上。”正是对金陵的特殊感情,《金陵旧事》中摘录了两则金陵不被破坏的典故:《后山谈丛》中记载:“黄巢为乱,将攻金陵。人解之,曰:‘王毋以攻也,王名巢,入金则剿矣。’巢因自引去。”还有就是石勒,他率军来攻建邺的时候,扬威将军纪瞻督诸军讨之,石勒退河北,“帝铸一鼎,沉瓜步江中。其鼎无文字,乃龟形。”
焦竑辑录《金陵旧事》,反映的是明代士大夫对金陵的态度,他们着眼于对“旧事”的回忆,缅怀“王者之气”的那段历史,而同为明代的马生龙在《凤凰台记事》中重点则放在明代开国如何建设南京,书注解为“俱洪武中事”,全书搜集洪武年间逸闻野史二十五条,涉及南京城池修建、山川地理、制度沿革,及太祖、高皇后轶事。马生龙的史料来源有二,一为摘录前人野史笔记,另外则是来自地方传说掌故。在关于明代定都南京之后的城市建设,马生龙首先回顾了自六朝以来的城市规模:
六朝旧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至杨吴时改筑,跨秦淮南北,周回二十五里。本朝益拓而东,尽钟山之麓,周回九十六里,立门十三:南曰正阳,南之西曰通济,又西曰聚宝,西南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钟阜,东曰朝阳,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曰仪凤,后塞钟阜、仪凤二门。其外城则因山控江,周回一百八十里,别为十六门,曰麒麟、仙鹤、姚坊、高桥、沧波、双桥、夹冈、上方、凤台、大驯象、大安德、小安德、江东、佛宁、上元、观音。
然后写到了如今的皇城,“皇城在京城内之东,当钟山之阳,以乘王气。又旧内城在京城中,元为南台地。本朝既取建康,首宫于此。”洪武时期,在江东门外稍南五里开河通大江,“江中舟船尽泊此以避风雨,名上新河。又开下新河,官司马快船所泊处。”又造海运及防倭战船,“所用油漆棕缆悉出于民,为费甚重,乃营三园于钟山之阳,植棕漆桐树各千万株,以备用而省民供焉。”还在玄武湖筑堤,又建开稳船湖,以通江水,为泊舟避风之所;还建造了来宾、重译二楼,“待四夷朝贡者。”还有清江楼、石城楼、集贤楼,“三山门外有集贤楼,皆洪武间建,以聚四方宾客。”这里还提到了阅江楼,宋濂奉敕撰记中有云:“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实蟠绕其下。因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名为阅江。一览之楼,万象森列,岂非天下之伟观与?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不油然而兴耶?”楼大约是造了,但是后来被毁了,现在的阅江楼是后人所建。
在筑京城的记载中,有一句“用石灰秫粥锢其外”,“秫粥”指的就是高粱粥或糯米粥,修筑南京城墙使用糯米汁的说法,在这本书中有迹可循,“即筑筑者于垣中,斯金汤之固也。”还记载了宫中阴沟直通土城之外,“高丈二,阔八尺,足行一人一马,以备临祸潜出,可谓深思远虑矣。”这对于理解建文帝出逃也有重要得文献价值。但《凤凰台记事》中更多记载了明太祖的逸闻,比如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于一媪门前木榻歇息,知老媪为苏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收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太祖遂感叹苏民忠厚,恐京师百姓千万无此一妇。“迨洪武二十四年取富户实京师,多用苏人,盖亦始此。”苏州太仓陆容《菽园杂记》、福建李默《孤树裒谈》中均有此记载,语言表述亦十分相似。还有两则记载的是高皇后的大足,一则说“上尝戏之曰:‘焉有妇人足大如此,而贵为皇后乎?’皇后的会答是:“若无此足,安能镇定得天下?”但是另外一则讲的是在元宵时张灯结彩,太祖微服私访看见有一盏灯上绘有大足夫人怀抱一个西瓜,“上意其有淮西妇人大足之讪,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口,邻里俱发充军。”可见对大足十分敏感,而且为了大足灭了九族,是在残忍;还有一则是太祖的趣事:太祖进膳有发,召问光禄官,对曰:“非发也,龙须耳。”因即埒须,得一二茎,遂叱去不复问。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