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2-21《素书》: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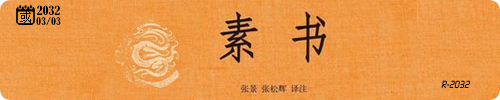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
——《史记·留侯世家》
陈涉起兵之后,张良也开始聚义,但是他所面对的是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是选择已经自立为楚假王的景驹,还是“略地下邳西”的沛公?尽管沛公那时已经拜张良为厩将,但是张良似乎还在犹豫,只有当张良拿出那本《太公兵法》,只有当沛公用书中之策,张良才作出了最终的选择,一句“沛公殆天授”让张良认清了形式完成了取舍,“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而跟随了沛公的张良并不曾独立带兵作战,但是以“画策臣”的身份为沛公出谋划策,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这是《史记》中的记载,张良从犹豫到坚定,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那本《太公兵法》,虽然司马迁说到的是《太公兵法》,但是史学界也一致认为《太公兵法》就是《素书》,《素书》让沛公“常用其策”,《素书》让张良“为画策臣”,关键就是《素书》之策将张良和汉王连接在一起,也是《素书》之策让张良感觉沛公就是天选之人,而张良不正是黄石公《素书》的“天授之人”?正是在圯上的时候,张良遇到了衣褐的老人,掉下鞋子让张良忍辱捡起,几次相约又责怪张良迟到,最后终于通过考验将书给了张良,黄石老人留下的那句话是:“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张良成为了《素书》的最佳人选,“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十三年后,老人的另一句话得到应验,张良在穀城山下看到了黄石,这就是老人的化身,即“黄石公”,由此司马迁在记述完这段“史实”之后发出了感慨:“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
在这里太史公虽然认为这一传说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言有物”,这“物”大约就是指《素书》对于张良一生所起的作用。《素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简单朴实,它的阐述如何言之有物?《素书》之“素”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是指白色丝绢,故此书称为“素书”,另一种认为“素”就是指基本原则和道理,入《黄帝四经》所言:“能至素至精,悎弥无刑,然后可以为天下正。”《素书》分为六章,文字大都由格言组成,但是蕴含着一些深刻的含义。《原始章》“言道不可以无始”,可以视作全书的总纲,“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它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的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道和德似乎更像道家的说法,仁义礼则更具儒家思想,但是《素书》将其合成一体,具体而言,“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什么是道?它是必须遵循的规律,但是“万物不知其所由”,这些规律并不能轻易掌握,但是德作为“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一个是“不知其所由”,一个则是“各得其所欲”,“不知”和“各得”构成了否定和肯定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仁义礼中得到了更具体的论述,“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道和蹈,德和得,仁和人,义和宜,礼和履,似乎以一种谐音的方式得到了阐述,而仁义礼更指向人的层面,人之所亲、人之所宜、人之所履,共同构成了道和德更外化、更具体的落脚点,所以这一思想更倾向于儒家:道、德、仁、义、礼形成五位一体的原则,“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这个“一”就是《素书》的“原始”,“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而要达到这一“原始章”,需要的就是抓住时机,“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对时机的阐述分成了几个层次: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和怀才不遇,所谓的时机一方面是如黄石公对张良、张良对沛公的人授和天授,另一方面则是对客观环境的顺应和把握,“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而这就是真正的贤人君子。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的思想传达出的规律意识所体现的就是哲学思想、治国原则和个人修为,而从《原始章》之后,《素书》通过格言更具体阐述了这几个方面的思想。
| 编号:B22·2241021·2191 |
《正道章》所提出的“正道”就是指正确的原则,它尤其提到了君主所应有的素质,“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这是“人之俊”;“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这是“人之豪”;“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这是“此人之”——只有品德高尚、真诚无欺、坚持原则、鉴古知今、体察下情、足智多谋、廉洁奉公的君主,才是人中俊才、世间豪杰。《求人之志章》讨论的是人如何选择自己的意愿和志向,重点则是“志不可以妄求”,“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禳过。贬酒阙色,所以无污……”如此等等,才会无咎、立功、保终,才能顺应客观局势,永保美好言行。《本德宗道章》似乎又回到了道和德的具体阐述,在这里所提出的就是博谋、忍辱、修德、好善、至诚、体物、知足等等的做人原则,同时指出了欲望过多、神不守舍、反复无常、非法获利、贪婪卑鄙、孤傲自负、任人而疑、极端自私等不良行为,“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乐莫乐于好善,神莫神于至诚,明莫明于体物,吉莫吉于知足,苦莫苦于多愿,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短莫短于苟得,幽莫幽于贪鄙,孤莫孤于自恃,危莫危于任疑,败莫败于多私。”《遵义章》更侧重于对“义”的解读,“言遵而行之者义也。”这其中就包括对不要以明示下、有过不知、迷而不返、以言取怨、好直辱人、略己责人、自厚薄人的防范,特别提醒领导者“决策于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安礼章》则从礼的本质和形式上做出要求,这里有一个以“同”和“相”列出的原则,形成了一系列的要求,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人与人交往寻找同道的具体表现:“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
由《原始章》作为总纲对五位一体进行阐述,然后通过《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等各章具体阐述,形成了总分的结构体系。这是《素书》文本内部的一种解读,但是《素书》却并不只是一本书,它向外扩展就构成了另一种解读的文本,这个文本就和张良的传说和传奇联系在了一起。《史记》中记载了张良此书“人授”之人的经过,也记载了张良最后和黄石合葬的故事,“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从起始到结束,可以说《素书》和张良的一生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本记载张良故事的书则是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全书记载了数十位隐士的生平事迹,关于《素书》和张良的故事见于《黄石公》,也就是皇甫谧是将神秘的黄石公作为记载的主角,但是内容则将《史记》相关内容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些细节和《史记》有所不同,比如说到黄石公,“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乱,自隐姓名,时人莫能知者。”《史记》记载的是张良在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而此书直接认定黄石公就是下邳人;“初,张良易姓为张,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与黄石公相遇。”《史记》说张良为了逃亡而改名换姓,但并无明确张良原来姓张还是改姓后姓张,而此书则明确张良改为张姓……
两本书的说法有出入,但是关于《素书》和张良的故事,更多在《史记》的记载中,而这或者也是解读司马迁所说“言有物”的关键,北宋宰相张商英在《素书序》中就根据《史记》中记载的张良生平事迹,和《素书》中的思想进行了结合:张良暗中劝告汉高祖封韩信为齐王,张商英认为这就是张良使用了《素书》中“阴计外泄者败”这条原则;张良劝告刘邦早点封和自己曾结怨的雍齿,“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高祖听从张良的计策,“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张商英认为这就是《素书》上所说:“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张良还劝告刘邦不要分封战国时期六国的后代,他列举了八条理由以此说明时代之变,这就是因为张良熟读《素书》,吸取了其中所说:“决策于不仁者险。”《素书》所说“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张良用这一策略,设计请来商山四皓以稳固刘盈的太子之位;汉六年正月封功臣,但是张良并没有立下什么赫赫战功,高帝对他的评价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但是张良婉言:“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这就是张良将《素书》“吉莫吉于知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张良最后选择抛弃人间事务,“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这无疑就体现了张良对《素书》“绝嗜禁欲,所以除累”的贯彻;而最初张良之所以得到黄石公的肯定而授予《素书》,更在于他面对老人的刁难、傲慢等考验选择了忍,“为其老,强忍,下取履。”这就体现了《素书》中所说“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的原则,从而造就了张良此后的辉煌。
《素书》的神秘性和张良的传奇有关,所以《素书》的基本原则和观点构成了第一个文本,那么张良的故事则构成了第二个文本。“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素书》定乾坤。”《素书》之所以被拔高到如此地位,更与张商英有关,由此构成了第三个文本。张商英认为古今圣贤思想没有谁能超越《素书》,它在《素书序》中说:“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等人被称为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于他们知天人之道,“天人之道,未尝不相为用,古之圣贤皆尽心焉。”但是黄石公留下了《素书》,完全超越了这些圣贤的思想。在他看来,张良之所以能成为张良,就在于使用了《素书》中的策略,但是张良之所以成为了这样的张良,更在于他“仅能用其一二耳”,也就是说,张良之使用了书中的皮毛,《素书》中还有着更多深奥的道理,“嗟乎!遗粕弃滓,犹足以亡秦、项而帝沛公,况纯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张商英的遗憾,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蕴含着对时机的阐述?或者在他看来,能真正得起根本的人还在寻觅之中?——或者是不是给《素书》以至上评价的张商英就是那个“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的人?他在《素书序》中记载了在晋朝战乱年代发现张良墓,那本《素书》就在张良玉枕中,而书上写着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这一段“秘戒”并未见于其他典籍,张商英却明确做了记载,他认为这是一种“慎重”的做法,因为这本书所需要的是真正的“人选”,如果传给了不合适的人必然会遇到灾祸,如果遇到合适的人而不传授此书也必受其殃——当张良死后五百年被盗贼得到,盗贼当然不是真正的人选,《素书》重见天日就需要真正的传者,而作序、注解、称之为圣贤之书的张商英是不是就是那个道、神、圣、贤之人?的确如此,在《素书序》的最后,张商英具体阐述了何谓真正的道、神、圣、贤:“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
“非此四者,虽口诵此书,亦不能身行之矣。”要成为道、神、圣、贤之人,不只是口诵而是要身体力行,而是要超越智慧,张商英如此阐述,的确更在于一种当下的意义,或者作为北宋宰相的张商英,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素书》的贯彻者和实践者,更是有着道、神、圣、贤品德的人,或者张商英期望更多的人能从《素书》中领略治国、修身之智慧,代代相传而始终维护道、神、圣、贤,就如《素书》所言:“如此理身、理家、理国,可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