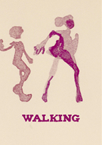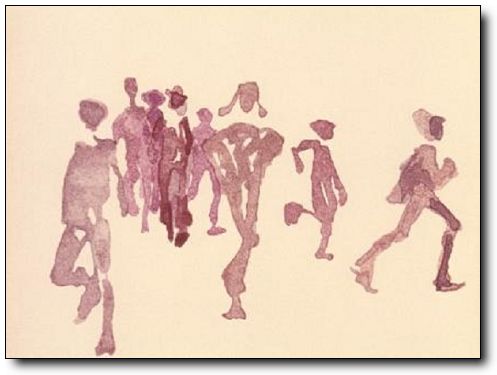2017-12-21 《行走》: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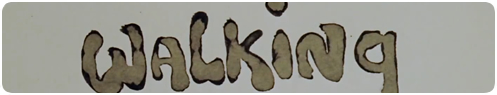
行走,最简单的运动类型,或者也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当人迈出那一步行走,就是要走出房间,走向更广阔的地方:那里有不一样的风景,有不一样的人群,有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是用脚步来引导眼睛,是用脚步丈量世界。
当瑞恩·拉金用《行走》来表现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阐述这样的主题?1968年的行走和以往的行走、未来的行走有什么不一样?人是不是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行走,是此时此刻的动作,但是却是一个过程,左脚迈出,右脚跟进,左脚再迈出,右脚再跟进,如此左右左或者右左右,就组成了一种过程的节律,就绘制了一段行走的轨迹,它从起点到终点,从此时到彼时,或者有停顿,甚至有后退,但是行走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人生。
可是,瑞恩·拉金,似乎要把行走变成一种可观的场景。一个男人如此步履坚定,如此步幅均匀,大约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步又一步,双手插在衣服口袋里,也不侧目,也不斜视,也不驻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自我的行走,自我的生活,是遗世独立的。一个人的行走,却也不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的周围是他们,他们是小孩,是女人,是老人——当他在他们世界里行走的时候,就仿佛隔开了两个世界,他的色彩是灰色的,他们的色彩是彩色的;他的行走是动态的,他们的生活是静态的:他们坐在长凳上,他们喝着咖啡,他们等着公交车。
|
| 导演: 雷恩·拉金 |
 |
所以在俯视的行走之后,则是仰视的行走,也是步履坚定,也是步幅均匀,也是自顾自,可是那一个微胖的男人是另一个男人,当他呈现出被仰视的视角的时候,一定还有另外的旁观者——当每个人开始行走的时候,他们都在别人的看见中完成对生活的定义。于是,行走的路上,有了健壮的人,有了瘦弱的人,有了小孩,有了女人,他们从静态变成动态,是被行走带入到一种公众生活里,而在这个场景里,那些人的行走是无遮的,肌肉在变化,身体在变化,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就是在行走中接近最原始的状态。
|
|
| 《行走》剧照 |
但是这种纯粹的行走并不是他们世界的唯一,男人继续行走,而场景开始变化,时髦的女人在行走,时尚的青年在行走,穆斯林妇女在行走,情侣在行走,各式各样的人,不管是什么宗教,不管是什么文化,不管是什么年龄,他们都在行走,而行走的方式也开始出现变化,有人在行走中和别人相遇,有人独自一人行走,有人跑步代替行走,有人翻滚着跟头,有人跳着舞步,有人和别人交叉跑动,不同的人,不同的姿势,也是对于多变的行走、多元的生活的一种呈现。
从一个人动态地行走,到一群人集体行走,行走的意义在最后又发生了变化,还是那个男人,还是不停的行走,却向着旁观者的位置走来,而且越走越近,人越变越大,甚至本来被隐去了表情的面部也渐渐放大,五官逐渐清晰,或者像一个你熟悉的人正向你走来。这是一种从模糊的个体走向清晰自我的隐喻,行走从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有着目的的行为,走向你,是为了凸显自己,凸显自己,是为了不淹没在行走的人群中。但是这种一步一步向你走来的方式,会不会反而消解“就这么一直走下去”的意义?走向你,最终一定是碰到你,碰到你,和你打招呼,或者被你阻挡,那么这行走就已经被中断了,甚至就结束了。
而这个越走近你就越失去我的最后场景是不是就是瑞恩·拉金1968年设置的隐喻?用有线稿素描和水彩,描绘的那些行走的人,是流动的,是迷幻的,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不固定的,当然,更不是直线型地走向终点,人群的加入,自我的放大,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行走本身也就有了不确定性——当一种常态的生活变得不确定,是不是让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变数?1968年后的瑞恩,是不是也以这样的方式走近了你,却慢慢失去了自我?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对于瑞恩来说,是一种打击,也是他在动画片创作这条道路上迷失的开始,当灵感慢慢枯竭,他在行走的路上开始依靠可卡因,可卡因慢慢摧毁了他的身体,当他他痛苦地戒除之后却又开始了酗酒,酒精麻醉了他的神经,当他终于从酒精的折磨中挣脱出来,却又陷入了困顿,最后只好在街上乞讨。
可卡因、酒精,以及乞讨的生活,都是瑞恩行走的方式,只是那条路已经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崎岖,越来越没有路可走,而这没有路的行走,就像那个在动画片的男人一样,是因为想要走近那些观众,走近就意味着走出了镜头,走向了障碍,脸越来越清晰,而最后是消失——从行走的路上消失,从旁观者的视野里消失,从自我的世界里消失。
“我真正想做的影片就是行走的人。”瑞恩曾经这么说,在行走的故事里,他制造了梦幻般的动画效果,那年他25岁,就像那个男人一样,遗世独立。但是最后就如宿命般注解了自己的行走,一直向前,可能就是自己行走的终点,当无法返回,无法转身,“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就变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来一杯冰啤酒是最让我享受的东西,我会放弃它,改喝茶之类的吗?不行,我做不到。”最终在可卡因、酒精和颓靡的世界里彻底走失。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785]
顾后: 《章鱼的爱情》:这世界已足够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