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1-05《法哲学导论》:人类需求整体之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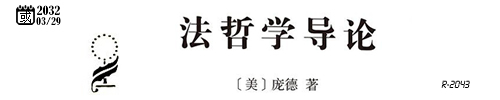
我们必须去建构法律,而非仅仅改进法律;我们必须去创造法律,而非仅仅将法律的内容有序化、体系化,协调其内容细节的逻辑关系。
——《法哲学的功能》
我承认,从购买到阅读都是从对作者的“错认”开始的:庞德,不是文学家埃兹拉·庞德,是罗斯科·庞德,虽然两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一开始瞥见作者时以为是康德,但康德没有写过关于法哲学的著作,到时黑格尔在1821年出版了《法哲学原理》,作为19世纪的产物,黑格尔在当时科学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力图通过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法哲学无疑是他庞大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从哲学的角度解析法,用辩证的思维探悉法、道德与伦理之间的奥秘,从而迈向自由的意志。不是埃兹拉·庞德的书,不是康德的哲学体系,也不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这本《法哲学导论》无意中成为了个人阅读史上歪打正着地通向法哲学的入门书。
入门就是从未知出发,就是填补空白,这倒是和庞德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理念相一致,在他看来,法律不是用来改进的,而是需要建构的,不是为了有序化、体系化一种学说,而是用来创造的——建构和创造成为人们对待法律的态度,这也是法哲学在法律科学中具有的意义所在。这是一百零三年前庞德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斯托讲座”上演讲的内容,他在前言中就指出了哲学引入到普通法的必要性:它可以回答哲学能够为法律科学帮助什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如何以哲学的方式处理问题?他之所以提出这种必要性,就在于认为哲学一直是法律装备库中的“重器”,而现在,“恢复其应有地位的时机”已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哲学在法律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就扮演过重要角色,也是法律日渐成熟和日臻完善的理论工具,当它需要“重启”,意味着中间也有一段曲折经历,所以庞德就指出法哲学的中心引入就必须避免两种理论倾向,一种是18世纪的自然法学,另一种则是19世纪的形而上学法学。
什么是法哲学?法哲学无疑就是法的最高形式的理论思维,它既指一种应用哲学,也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支,法哲学当然不是法律和哲学的简单相加,通过哲学理论思维的运用和建构,就是为了在法律理性中达到普遍安全的目标,或者说,通过理性的中介,将自在的法变成自为的法,由感性形式达到理性的普遍形式。从自在到自为,从感性到理性,法哲学的理念就是一种建构和创造,这也是法哲学本身具有的内在功能。建构和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庞德认为,就是保障一种秩序,法律的由来首先是满足人们寻求某种可靠基础的实现,这就是普遍安全,它是一种表现为和平与秩序的社会至高利益,体现的是稳定牢固的社会关系;而当在社会利益的压力并不紧迫的情况下,法哲学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不断变化中利益与普遍安全之间的适应问题,它通过对细节的不断调整来完成。无论是稳定牢固的社会秩序之维持,还是社会利益和普遍安全之调整,总之,哲学家建构法律,其目的就只有一个:构想一种完美的、永恒不变的法律,所以法哲学的构建目的,或者试图为法律提供理性说明,或者是为了构想一般性的法律秩序理论,或者将两者结合予以更普遍性地阐发,“使其足以应对所有时代与地域的法律。”
法哲学所指向的一般性、普遍性就是从自在到自为,从感性到理性的路径需求,就是为了形成一种完美、永恒不变的秩序。庞德通过对法律发展的历时性考察,更细致而具体地阐述了法哲学的内在需求。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家所思索的就是,社会的正当是基于自然而正当,还是因制定或惯习而正当,“正当”的需求在公元前5世纪就被提出,这就是意味着法哲学从一开始就在人类制度方面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在古希腊时代,法律规则是以个案衡平的方式被应用,法律获得的基础则是比人的意志以及意志执行者的权力更为稳固,但是它的目的就是维护普遍安全,确保制度安全——防范个人权力的恣意,并说服和强迫贵族维持社会有序状态。但是在庞德看来,古希腊在法哲学发展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区分了法和法律,法律是和习俗联系在一起,达到的正是法具有的权威性,或者说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正”,所以法与法律的区分成为希腊法哲学“永恒贡献”,“该区分是自然公正与制定公正之分的基础,对法律发展的所有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
| 编号:B42·2241119·2209 |
古希腊的法律还处在原始法阶段,法律和道德没有被分开,它们还具有同一性,到了罗马时代,出现了罗马法,罗马的严格法和道德就被区分了,在共和国和帝国之交时期,罗马的法律就要求一种适应综合性法律的理论,西塞罗提出了七种法律形式,其中四个被保留下来,即制定法、元老会决议、行政长官法令,以及法律学者的权威理论,后来又演变为三个:立法、行政法令,基于法律传统的法学理论,它们对应着法律的三个构成要素:市民法、程序性故意则和法学家著作。随着职业法律人的出现,城邦法开始转向万民法,法律科学的需求更加迫切。庞德提到了“自然法”,在当时来说,“自然”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神,也就是说,“自然”的物体是“最为彻底体现了该物之理念”的物体,是完美之物,所以自然法就是“完美体现了法之理念的法律”,它既需要一种完美适用问题的法律理念,又必须让规则对问题的解决是完美的,而建立这种理念和规则的机制就是法律理性,但是当时法学家所提出的是“法理”,指向的是规则背后的自然法原则,它既带来了实践上的好处,也导致了解释上的认知混淆。
庞德认为,自然法是法哲学的重要理论,“它的出现,是用来满足衡平与自然法阶段的社会需求,这是法律史上一个重要的创新期。”实在法都是对自然法的宣示。之后从市民法转向万民法,则意味着法律内容向一般化过渡,更在适用性原则下北一般化,这就是法哲学不断探索的见证。到了中世纪,法律开始了科学化的建设,受到哲学的影响更多,进入严格法阶段之后,经院哲学通过对权威给定的前提进行辩证论述,这就是为权威提供了理性基础,在庞德看来,这是对法律科学永恒性的贡献,“此方法将权威观念之内容予以逻辑展开,确保了法律的确定性。”到了16世纪,自然法逐渐摆脱了神学更依凭理性,无论是新教神学法家还是天主教神学法学家,都为了时代之需找到了哲学基础。之后提出的自然权利,代表着内在于人的、被理性所揭示的特定品性,它是自然法的保障对象,同样,实在法对其必须予以肯认。
所以庞德认为这就标志着法律已经开始步入了成熟期,因为所有时代立下法律章程,都试图确定法律不变的内容。到了19世纪,法哲学出现了四种类型,但是不管怎样的类型,它们都导向同样的结果,都有同样的精神内涵,都是法学需求的理性化模式。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推演自美国政治制度的自然法让位于“形而上学-历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自然权利推演自个体自由意志,它从形而上学上确定了推证的论据;之后出现了“功效-分析”理论,立法者的原则就是功效,即“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总量构成了立法的标准”;19世纪末,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想代替了“形而上学-历史”和“功效-分析”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所有现象都是被无情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道德、社会及法律现象被规则支配,超出了人类控制的能力范围。
梳理法哲学的历史发展,哲学思想对法律的影响当然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庞德面对法哲学的现状,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即法律及其应用问题需置于当下社会理想之下,对法律目的以及基于社会功效的法律规则、原理和制度的评判,必须在法哲学的理性认识中,“我们有责任去构架此时此地社会文明的法律原理,依此评判法律及其应用,以便于通过法律促进社会文明发展,并使得过去时代传递下来的法律素材成为维持和促进今日之社会文明的手段。”当社会向前发展,法律就必须成为一种构建之物,一种创造的规则——这就涉及到法律的目的这一问题。法律的目的,就是阐述制定法律所预设的图景,在这里庞德把制定法律看作是“发现法律”,发现比制定更体现了对预设目的的回应,也更符合目的论的构建和创造。
无论是发现法律还是构建法律,法律的目的问题就涉及法律的本体,庞德首先列举了关于什么是法律的十二种说法:法律被认为是神定的人类行动规则,法律是为人指明安全行动路径的古老传统习俗,法律是一套在哲学层面发现的原则体系……如此等等,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十二种解释,庞德找出了共同要素,它们都超出了个体人类意志的范围,展示了某种终极根基的图景,也就是说,人类生活会有诸多变化,但是根基不受影响,它是稳定的,牢固的,这也是法律理论中首先要强调的特征;同时它的运用是按照决定论、机械绝对性模式进行推演的,最终目的则是满足普遍安全的社会需求。考察法律的概念,庞德无疑总结出了法律背后的理性,那就是稳定性、绝对性、普遍性,而这就是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律目的,不管在历史上呈现出怎样的法律目的的运用,庞德认为,今日法律的目的就是实践这样的理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可能的人类需求整体之满足。”通过社会控制,人类的需求、主张和欲望不断被承认和满足,同时社会利益被一种更包容和更有效的方式被保障,社会内耗的消除、社会冲突的化解,也变得越来越有效,总之,这样的法律目的就需要将法律变成一种社会制度。
法律成为社会制度,它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类需求之整体,这就是法哲学所体现的理性意义下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而在具体的应用层面,庞德认为法学的所有问题都涉及规则和裁量的关系,它表现为一些基本问题的争议:法律的本质是法律体系中的传统要素还是命令要素?立法的性质是通过司法经验而发现还是通过要求而创造?法律权威是基于理性与科学还是基于命令与主权意志?这些争议它所表现的问题就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和衡平的区分,法庭和陪审团的智能划分,程序运行依赖固定规则还是宽泛的司法权力,实现正义通过司法判决还是行政个别化实施?
通过对责任、财产和契约这些法律最基本层面的历时性考察和本质阐述,庞德从历史演变过程总结提炼了法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他的制度化构建,法哲学其实也变成了法学社会学:责任的终极要素不是自由意志,而是“文明社会条件下可证立的依赖”,因为法律保障的是源于行动、关系和情境的合理期待;私有财产不是永恒的、绝对必然的,财产法的目的就是满足更多人类需求,保障更多利益,而且,“付出的代价却比任何我们可能设计的制度更小。”而对于契约,庞德提出了将诚信和允诺的推论植入法律生活中,“为法学家、法官和立法者提供一套逻辑评判标准,一种可行的决策尺度,以及一个法律该追求什么的理想,让他们用这些东西继续拓宽法律上可执行的允诺的领域,并由此同时扩张法律满足人类主张的领域。”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