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4-04《雅斯贝尔斯与生存哲学》:将目光投向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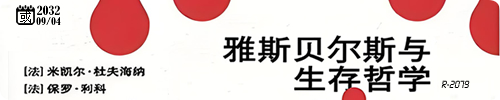
在这个必然性下,人毫无疑问地承载着其人类境况、限度、历史性以及因处在世界中且生活在国家中而形成的客体性,从而让生存在其身上重拾其源头以及超验的真正意义。
——《附录》
“必然性”就是对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批判反思中提出的可能性的回应:当雅斯贝尔斯在《哲学入门》中构建了从生存到超验的“生存哲学”,它就是一个“对真实性充满激情的追寻”,在其中有座位生存之人的使命,有自由及其世界中之机会的代价,有交流及其界限,有超验不可言说的在场,以及这样的“必然性”——当个体的人以超验的方式抵达了生存哲学的终点,这也是他对人类生存的一次启明,从个体之人到人类之人,境况、限度、历史性以及由此形成的世界客体性,都在生存和超验意义上成为了对真实性的追寻。或者这种必然性就是形成了“向一个思想以及一个命运的连续性致敬”。
从个体之人到人类,必然性成为对生存哲学的回应,其实也是雅斯贝尔斯战后思想对战前的一种回应:在这篇“附录”里,保罗·利科和米凯尔·杜夫海纳提到了他们最近读到的一本书,这是雅斯贝尔斯关于德国“有罪”问题的新作,在这本书中,雅斯贝尔斯就从自我的生存哲学超越成为人类的生存哲学,他提出的“有罪”就是基于境况、限度、历史性以及世界和国家的客体性提出的,“坚持不懈地对德国人的过错进行忠诚的沉思,从每个德国人身上实现对人的净化问题”——利科和杜夫海纳借用斯宾诺莎的说法是一个人的“再生”问题,而“再生”就是对必然性的回应,就是回到了雅斯贝尔斯在《哲学入门》中提出的批判反思。而在这里,利科和杜夫海纳之所以特别提到雅斯贝尔斯战后的“有罪”问题,更是与自身有关:就是在二战的战俘营,他们共同研读了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入门》等著作,合写的读书笔记就成为了《雅斯贝尔斯与生存哲学》的初稿,他们为什么要研读这本著作?他们为什么要关注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是不是身为战俘的他们深刻地理解了失去自由的痛苦?是不是面对着最本质的生存问题?
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就是他们生存最现实的写照,也是他们最现实的生存哲学,而在阅读、笔记和写作中,这种反思和批判就构成了一种“同感”:如何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不同的个体意识中寻找共同点?如何在思想与思想之间寻找关联?如何在生存与生存之间寻找共同的境况?寻找就是对“同感”的寻找,“唯有字词、概念装置以及论据恇架位于意识与意识之间,绝对匿名地平躺在一本又一本书中,等待着被某个类似于作者经验的独一无二的经验所验证,并在与作者经验的关联中诞生。”而实际上,这种“同感”正是雅斯贝尔斯的作品希望读者建立的,也是利科和杜夫海纳在阅读和写作中所发现的,“同感不仅意味着一种冒险,而且也意味着一种跳跃;突然间,人们进入他人的思想中,并跟随其前行。”
雅斯贝尔斯让读者进入,利科和杜夫海纳作为读者进入,这就是同感所具有的契合,它跨越了不同语言、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更是在战争这个特殊时期跨越了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对立世界:消除差异寻找生存的“同感”,就是生存哲学真正的开端。当然从哲学思想出发,利科和杜夫海纳看到的则是雅斯贝尔斯承担着的哲学的任务:面对古典形而上学的危机,面对时代前行的方向,生存哲学如何在西方哲学不可避免走向衰落中重建真理?利科和杜夫海纳把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的出发点理解为:“黑格尔之后,体系的不可能性。”黑格尔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一次终结,该哲学被构思为普遍、总体和系统的知识,于是它在理性的世界里演变为科学本身的危机,而在非理性的吹捧下变成了情感的宣泄,危机本身就是在召唤“大哲学的回归”,这个大哲学就是雅斯贝尔斯提出的生存哲学:生存与超验一起,指向了最高意义的个体,这个个体不是生物学意义上存活的个体,不是被精神的、不朽的、永恒的规则所定义的普遍的个体,而是对存在的忧虑所定义的自由的个体,是在死亡面前“在国家里以及在朋友之间用命运下注的人”,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是可能“回归自我”也可能“遗失自我”的个体。
将生存从生物意义、普遍意义变成一种个体的存在,雅斯贝尔斯面对危机和哲学的衰落提出的生存,其思想源头可以看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影子,而雅斯贝尔斯将个体的生存哲学定义在三个主题里:出于知识界限处的生存、作为自由之内在行动的生存和与超验展开斗争的生存,这三重的生存任务在雅斯贝尔斯那里则表述为哲学的真正源头:“我们不是例外,但将目光投向例外,以进行哲学思考。”为什么要将目光投向例外?为什么在例外中进行哲学思考?按照利科和杜夫海纳的理解,对“例外”的忠诚才能给予哲学原初的动力,才能让生存哲学获得“生存”,才真正配得上“哲学”这一称谓,因为“例外”意味着一种“永恒哲学”得以完成自身的任务:以思想为方式,以存在为终点。在这里,“例外”就构成了“永恒哲学”的一种更新力量,因为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当不可分的存在系统崩塌之后,另一个被撕裂的存在系统将应运而生,这一种生成是以思想的方式表达着生存的显现,雅斯贝尔斯将其称作“超越”——超越是对旧有体系的一跃,这一越何尝不是“例外”,而更深刻且具体的表达,“例外”也正是个体将目光投向他者并在和他者的交流中实现向人类生存进发的动力,而投向例外的目光也将实现“向一个思想以及一个命运的连续性致敬”。
| 编号:B83·2250113·2225 |
所以,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的基本操作就是“超越”,超越是对障碍的超越,那么障碍是什么?那就是客体性,“这个客体性由那些对存在的最初决定构成,目的是让存在始终首先作为客观物呈现。”客体性在德语里又两个词,一个是“Gegenstand”,雅斯贝尔斯将其看作是与“我思”之主体相关的“我思”客体,这就是表征客体,另一个则是“Objekt”,它所指的是相对某个客观知识而言的客体,具有精确性和普遍性。表征客体涉及意识和存在的关系,涉及思想和客体的关系,普遍的客体则和科学知识的有效性问题有关。为什么客体性是一种障碍?表征客体关涉的是意识,它和意识拥有相同的广度,对某个表征的意识也总是对自我的意识,于是,“任何未在意识中呈现之物都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是存在的限度;逃离意识的存在对我们而言就像不存在一样。”所以雅斯贝尔斯认为只有一超越的方式,意识才能超越所有表征,从而抵达不再能表征之物;但是,在超越的开启中,某个知识决定的客体的客观特征也将成为障碍,而客体性就成为由理念所表达的总体性:这里的理念就是精神的范畴,它是国家、宗教与文化,更是知识、艺术、精神,它呈现出客体性帝国“宽广的疆域”,主体在这样的客体性面前体验到无与伦比的满足,也因此“我”的主体形式将合法地消失,“主体性只是客体性的一个条件”。
所以生存需要一种超越,超越知识的客体性,超越任何的表征,超越就构成了生存哲学的任务:抵达生存、直面超验,“超越就是思考不再能被思考之物,就是邀请思想在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去宣称自身的虚无。”但是实际上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客体性根本就是无法被克服的,而且具有必要性:表征具有必要性,“生存和超验同样只有被归入某个表征时,才可能服从于哲学的反思。”也就是说,生存的存在只能以意识为支撑点,超验也是表征的客体;明晰性具有必要性,至于这样,思想才能被表达,否则就会陷入无形和任意之中;客观世界具有必要性,生存和超越只有相对世界而言才有意义。所以,被超越的客体性也是哲学用以照亮生存的方式,“超越并不是永久地抛弃客体性,而是在超越客体性的同时,总是不断地回归客体性。”没有世界的客体性就没有知识的普遍性,没有表征的明晰性,就不会有思想,超越行为永远在无法完成的进行中,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一个行动,“而且是所有行动中最高的一个”。
哲学是一个超越的行动,这个超越就是对生存世界的探索,但是科学也是超越,也是对生存世界的探索,哲学的探索如何又是对科学的超越?这里就涉及到“世界”的概念,“世界”在康德的世界总体中就是一个经验存在,如果世界是一个总体,那么它就将存在的所有可能占为己有,对世界的认识将被等同于对存在的认识,甚至这将是一个“我的”世界,而世界之经验是与我相对的“非我”,这样世界就变成了一个模糊概念。所以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世界无法作为一个总体被思考,它的意义也总是局部的,而对世界进行探索形成的知识,也只是成为科学的目标,“一切科学都渴望获得某个客观、普遍、永恒的知识。”但是这样的科学理念只是某种对世界探索的乌托邦,科学始终无法确定自身的边界与地位,世界不再具有统一性,同样知识的统一性也将不再存在。但是按照利科和杜夫海纳的理解,科学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实现对自身的显现,按照这一理解来说,哲学当然应该和科学相分离,但是正是在科学无力的时候哲学出场,也就是说,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的序幕,甚至科学和哲学所揭示的世界还是同一个世界,“无论是通过科学还是通过哲学,人都只有一个憧憬,亦即对存在的憧憬。”
当然,哲学并不同于科学对世界的探索方式,哲学是知识,但是是一种扎根于生命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雅斯贝尔斯用“介入”让哲学承担起了生存的使命,“让一个人的具体行动像火焰般喷涌而出的‘火炉’”,被点燃的火炉是哲学的自我反思,也是哲学的行动。这就进入到了雅斯贝尔斯生存哲学中最关键的一步:对生存的启明,“生存不是哲学思考这一行动的目的而是该行动的源头,生存在自己身上捕获自身”,这种捕获就是让生存显现为一个通过有关自身的决定而“成为”这个存在,从一个不“在”的存在生成为“在”的存在,“我将自我超越”。在这个捕获自身的行动中,雅斯贝尔斯揭示了生存的三大领域:当生存自我生成时,就是自由,当生存与其他生存共在,就是交流,当生存处在世界之中,就是历史性。对自由、交流和历史性的考察,利科和杜夫海纳也进入到生存哲学关于自我生存最现实性意义的考察上。
被关押在战俘营,当然最需要一种自由,但是生存哲学中的自由是一种超越的意识,是一种跳跃的显现,“只有自由才能针对自由进行提问,正是在这一提问中,我们得以与自由不期而遇:充满激情地探寻着自由的人已经自由。”自由在我的存在受到质疑的焦虑中被提出,但是自由不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只有在发现可能不自由且会自我遗失的时候,我才是自由的。在这里,利科和杜夫海纳提炼出了雅斯贝尔斯作为存在主义者对于选择的思考,自由的选择不是我采取的立场,而是采取立场的事实本身;自由的选择是我走向我自己的行动,是通过自身选择决定自我存在;选择意味着偏见、风险和勇敢以及自我忠诚,“每个决定都是我所冒的风险。”所以自由作为灵魂,选择意味着我给予我自己,“我选择我所是之人”,选择的自由所抵达的就是必然性,“这是一个真实的自由,因为它以某个必然性为基础,这也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自由,因为该必然性永远不相对自由透明。”
当我给予我自己作出的选择,当我成为我所是之人的自由,这里就有了他者的存在,我“通过一个他者”而在,他者是我的超验,也是进入“交流”的保证,“我只有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成为我自己:这便是交流的悖论及其独特的神圣性。”利科的“他者”理论也正是从这里获得了灵感来源,而在雅斯贝尔斯并不对纯形而上学问题感兴趣,而是在描绘生存中进入到了伦理学领域:我通过他者变成我自己,但我之所以变成我自己,那只是因为我曾是我自己,这是交流的一个出发点;我需要他者来真正意义上地成为我自己,这就从形而上学过渡到了伦理学,它所启明的就是交流,“交流只有通过不断超越每次的具体实现才能完成对自我的表达”。如果说生存与自由的关系是“在……里面”,生存与他者是同在的关系,那么生存和世界则是“处在……之中”,由此构成了生存的存在坐标,而对生存和世界的关系,利科和杜夫海纳认为这体现了生存的历史性,体现了生存境况,在死亡、受苦、斗争及过错中,境况赋予了生存“历史的深度”,也标志这生存哲学从个体的境况扩展到了整个经验现实性,它所讨论的就是“普遍现实性的历史性”以及“一切经验存在的普遍界限境况”。
自由、交流和历史性将生存哲学赋予了伦理意义,“确切、固定的道德准则与无条件行动之间的冲突属于自由的循环,客观社会形式与个体之间的张力属于交流的循环,而世界本身与可能生存之间的张力则属于历史性的循环”,这种伦理学意义超越了个体的生存,它在不可克服的客体性中就表现为义务、社会和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生存的启明开始将目光投向例外,生存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其实就变成了现实性问题,个体生存就变成了普遍生存——当个体的目光投向了例外,就是构建了一种类的相似性,“只有当主体真实性与无条件性定义为人的相似性时,这个哲学才可能。”从个体和个体的例外到普遍的相似,这里产生的张力就具有一种时代性,“或许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不仅应该被发现,而且应该被重新发现。”而普遍性和时代性让生存哲学不再是一种知识,一种伦理,而是一种信仰,“生存哲学排斥将生存视作一个可完全客体化且可让任何约束性知识进入的某个本质;它只是指出,生存就像一个本质,可能被启明并允许某个理性的信仰进入。”
当战争结束自由成为可能,当战后重建需要交流,当境况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雅斯贝尔斯“坚持不懈地对德国人的过错进行忠诚的沉思,从每个德国人身上实现对人的净化问题”时,生存哲学是不是超越个体,超越客体化世界,而构成了“同感”中的对话和反思?在他者中完成选择和重构?“生存找到了它的箴言:经历失败,并在失败中体验存在。”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