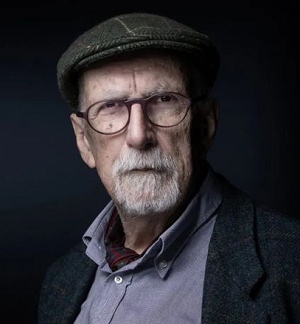2025-05-02《我们从未现代过》:中间王国展现在面前

只要将这两种维度同时展现出来,我就可以将杂合体吸纳进来,给予它们一个位置、一个名称、一处容纳之所、一种哲学、一种本体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给它们一种新的制度。
——《制度》
“制度”便是现代制度,它体现的是现代性,它阐述的是现代论,它要解决的是科学的实践运用,但是当从17世纪中叶逐渐形成这一制度开始,它却走向了完全被割裂的两个维度里:一边是非生命体的行动者,一边是道德、信仰的行动者,一边是通过实验室对物进行的表征,一边是则是以社会契约为媒介对公民进行的代表,一边是实验、事实等有关自然的主要资源,另一边则是七月、君主为代表的权力资源,当割裂的两个维度被同时展现出来,它不是趋向于构建一种现代制度,反而变成了人为建构的“二象之间”,从而走向了“我们从未现代过”的尴尬。
布鲁诺·拉图尔为什么声称我们从未现代过?在他看来,现代制度凸显的现代性是以人类主义为基础进行界定的,但是在17世纪中叶形成这一制度的时候,它完全朝着两个维度各自发展的方向被建构起来。这两个维度的代表一个是自然哲学家罗伯特·波义尔,另一个则是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他们在对科学力量好政治力量的分配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目的论来看,他们都渴望有一位国王能够建立起议会和听话的教会,他们都在彻底的理性主义中构建一种机械论的哲学,但是分歧产生了:波义尔及其门徒利用的事有关自然的主要资源,他们把没有个体意志的非生命体看成是这一制度的行动者,在毫无偏见中在实验室的仪器中进行展示、指示和书写;而霍布斯及其追随者则创造了分析权力时所需要的最主要可用资源,他们把专属于上帝、国王、物质、圣迹和德性的观念进行转译,从而进入仪器所能够正常运行的实践之中。
朝着不同的方向,完成统一建构的人物,一方是以实验室为媒进行的表征,一方是以社会契约为媒对公民进行的代表,他们的问题就出在对于新制度的建构完成变成了如巴拉什所说的“事实是被制造出来的”,人类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切,建构了一切,却又割裂了一切,一个制度形成了两个维度,而两个维度又“恰恰是一套”:“这套创造在我们的两个主角之间进行力量分配:将政治学分配给霍布斯,将科学分配给波义耳。”也就是说,这种割裂的“二象之间”没有在对非人类的表征和人类的代表之间、在事实的人造性和国家的人造型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因为和前现代相比,现代性将被忽视的非人类纳入其中,物、客体和兽类这三种实体和现代性一起诞生,也就是说,当现代制度赋予非人类一种新的符号力量,由此促发了新的文本样式,即实验性的科学文献,它构成了介入古老《圣经》诠释学和新仪器之间的杂合体,正是这种杂合体的存在,使得转义工作运转起来,从而使得杂合体的扩展增殖成为可能。
但是现代制度所体现更重要的是一种批判力量,这种批判力量是将两个维度同时展现中构建真正属于人类主义的双重体系中:“当人们使自然无限远离人类时,他们仍然能够将自然动员为社会关系的核心部分;当人们赋予社会定律以必然性、必要性和绝对性时,他们仍然可以自由地制造或者毁灭其社会。”仅仅将非人类纳入其中,仅仅形成科学文献,仅仅让杂合体增殖并不是现代制度的真正要义,科学需要的是在被制造的事实和主体之间构建新的体系,需要在双重语言之中真正起到批判的作用——如果两个维度永远被置于割裂的两边,那么,“我们从未现代过”。拉图尔用“从未”的否定形式阐述17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制度时期,实际上是面对的就是“危机”问题:我们从未现代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如果长此以往,未来也将不会进入现代。
| 编号:B83·2250406·2277 |
他把被割裂的现实形容为斩断戈耳迪之结的利剑,当现代的车轭被斩断,意味着有关事务的知识被搁置在左边,权力和人类政治则被放置在右边,他认为,批评家对世界进行分析往往采用三种进路方式,一种是以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然化进路,当他谈论自然化现象时,社会、主体以及各种形式的话语都消失不见了;第二种则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化进路,当他谈及权力时,科学、社会、技术等内容也都隐蔽不见了;第三种进路是解构主义进路,当德里达讨论真理效应时,也从来不会相信大脑神经元或权力游戏的真实存在。也就是说,每一种社会分析进路,都与其他两种进路不相容,也就导致了社会批判所使用的是三个割裂的范畴:自然、政治和话语。
既然戈耳迪之结可以被利剑斩断,那么是不是在这场危机中还有将其重新构建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拉图尔似乎在阅读现代的报纸时发现了这个逃离困境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报纸上刊登的是不同内容的新闻和信息,它们有关于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绩,也有政治生活中的纷争,而且还有社会事件、娱乐新闻——它们杂糅在一起,“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自然,每天都在不断地重新组合并纠缠在一起。”而且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拉图尔说自己还做着现代人的祈祷方式,这种阅读和祈祷构成了拉图尔对自我身份的绅士:在杂合状态中,自我是不是自由地穿梭?和在科研机构中的职位一样,既是工程师也是哲学家,而这就是米歇尔·塞尔所说的“第三类知识分子”,他既有完备的科学知识,有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报纸呈现的是一个杂糅的世界,阅读者拥有杂合的状态和身份,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是不是被不断转译从而构建了一个网络?网络,比系统更具有韧性,比结构更富历史性,比复杂性更有经验性,当阅读成为网络的一种构建,是不是“第三类知识分子”也可以构建一个现代的制度体系?当拉图尔说“我们没有现代过”,既不是指我们还在前现代,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甚至也不是对现代性完全颠覆的反现代,而是在现代制度中展现一个“非现代世界的领域”,就像报纸信息一样,就像复杂身份一样,就像网络一样,它是一个未开肯的中间地带,“这样一个中间王国,就像是中国一样,幅员辽阔,但我们对它所知甚少。”
回到制度层面,当“我们从未现代过”的现代制度割裂了两种维度,那么重构意味着展开这个幅员辽阔的中间王国,但是这个中间王国到底怎样呈现?为此,拉图尔也提出了疑问:“那么,我们必须要将科学实践不偏不倚地放到联结客体极与主体极之线段的中点吗?这一实践是一个杂合体,抑或是两者的混合之物?部分客体,部分主体?又或者说,既然某种政治语境和某种科学内容同时产生,那么,面对这一离奇境况,我们是否有必要为之创设一个新的位置呢?”拉图尔借用米歇尔·塞尔的概念,引入了“拟客体”:拟客体位于两极之间,二元论和辩证法因此绕过了它而与之不相容;但是与自然的“硬”相比拟客体更具社会性、被构造性和集体性,而与社会部分相比,它又更加实在、更加非人类、更加客观。要将拟客体吸纳进来展现非现代的王国,拉图尔提出了三种策略:首先要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确立期间的距离,然后完成摒弃拼主客体两端的“符号学转向”,第三则是分离出存在的观念,进而整体拒绝杂客体、话语和主体之间的分割。
|
| 拉图尔:我们首先要重新定位人类 |
三种策略实际上应对的是拟客体的增殖,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完成区分,然后实现语言或意义的自治化,最后则实现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自然化、社会学化、话语化,最后是遗忘存在。”拉图尔将其看做是一种革命,而且是一种针对现代化的“反革命”——反哥白尼革命,“使两极向中心和下方移动,这种移动使客体和主体围绕拟客体和转义的实践而旋转”,也就是说,不再需要依附于客体或主体两种纯形式之上,而是形成一个实践的出发点,自然在旋转,社会在旋转,主体在旋转,它们所围绕的是集体,“它围绕集体而转”,自然和社会就构成了这个旋转附属。在这里,“集体”就是拉图尔的一个实践概念,科学所讨论的就是集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联,“集体”描述的也是社会学意义上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只不过是集体的一部分,所以,“集体中充满着我们所展现的事物”,当一切的旋转围绕着集体,当集体给拟客体留出了革命的位置,中间王国便被表示出来了:客体从自在之物中剥离,靠向了拟客体这一共同体一侧,而不至于和主体构成二元;在拟客体的不断增值中,形成了四种资源:自然的外在资源、社会纽带资源、意指和意义以及存在,“如果我们追随拟客体,我们就会发现它时而像是一个物,时而像是一段表述,时而又成为一种社会纽带,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它无法被还原为某个纯粹的存在者。”
一个共同体,四种资源,拟客体的增殖过程就是一种反革命的革命:本质转向事件,纯化转向转义,现代维度转向非现代维度。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是实在的,它们是集体,它们是话语性的,它们具有历史性,由此构成了“网络”,“这种像自然一样实在、像话语一样被叙事、像社会一样具有集体性、像存在一样实存,这就是现代人使之增殖的拟客体。”拟客体这个共同体既有主体的标识,也是主体间性的建构者,是主体实在性的体现,引入这个主体间性的建构者,拉图尔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掀起一场反哥白尼式的革命,而是要让革命变成实践,用于他一直致力的人类学研究,这种人类学研究的模型就是比较人类学,就是对称性人类性,“如果它想获得在现代人与非现代人之间来回穿梭的能力,它就必须具有对称性。”
什么是对称性原则?拉图尔认为传统的人类学是非对称的,在认识论上形成了“被认可的”科学和“过时的”科学这种先验的二分,在身份上形成了以知识、信念系统和科学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之间的分割,而对称的人类学就是将错误与真实放在同样的位置进行考察,确立起连续性、历史性,这样才能建立根本意义上的公正性,“人类学家必须要将自己摆在中点的位置上,从而可以同时追踪非人类和人类属性的归属。”这个中间点的位置不就是拟客体的场所,不正是被呈现的中间地带?只有在对称原则下构建自然和文化的平等,才能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这项工作的全部挑战在于,要用最少的方法产生出最多的差异。”这种对称之下形成的差异,就需要建立关系主义,就需要开展实际的戳伤,而这也正是体现主体间性的拟客体的功能,它是一团阿里阿德涅线团,“帮助我们从地方性逐次走向全球性、从人类渐次走向非人类。这个线团就是实践和仪器的网络,是文件和转译的网络。”
引入拟客体,确立集体之间的对称性,形成阿里阿德涅线团,拉图尔由此开展的实践就是从“我们从未现代过”的现代进入到“非现代世界”:非现代世界不是对现代的完全悖反,而是在割裂的现代制度中重建,“现代人的伟大之处,来自他们对杂合体的增殖、对特定网络的加长、对轨迹的持续生产、对委派的增加、对相对普遍性的不断探索与制造。”对称的人类学所要保留的恰恰是现代性中的勇气、创新意识、自由创造;同时,也吸取了前现代的一元性,从后现代那里保留多重时间、建构主义、反身性和去自然化,可以说,对称性的人类学研究就是构建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拟客体网络,而拟客体的构建就是对人类的重新定位:拟客体不是物,“但是物本身也不是物。”拟客体不是商品,“但是商品本身也不是商品。”它不是一部机器,“任何见过机器之人都不会认为机器就真的是机械性的。”它也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它当然也不存在于上帝之中,“但是天堂之上帝与尘世之上帝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所以拉图尔认为人类主义就意味着像拟客体一样,既分享自身又维持自己的存在,“人类的本性是由其委派员、其代表、具形象、其发信者的组合。”这种人类主义构成了一种对称的共性,在这种共性里,集体的连续性被重新型构,不再有无遮蔽的真理也不再有无遮蔽的公民,转义者占据了所有空间,启蒙运动占据一席之地,自然在场,科学在场,社会在场,与作为基石的客体站到了一起,这就是拉图尔的非现代世界,“自然和他者都不会成为现代的。”在这个非现代世界中,人类“别无选择”的改造就是为了对文化可以继续支配,对环境进行接纳,非现代的自然和他者,现代的人类,就这样在这个共同的栖居之所中形成了对称的结构,“人类处在自己的委派之中、处于流逝之中、处于传播之中、处于一种持续性的形式交换之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