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06《论确定性》:位于语言游戏的本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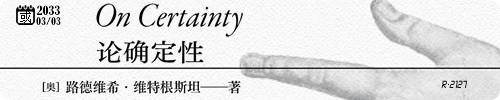
因为“我知道……”似乎描述了一个事实,它保证了所知道的东西是事实。人们总是忘记了“当时我以为我知道它”这个表达式。
打开《论确定性》,合上《论确定性》,一本作者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书是确定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为58元、页码244页也是确定的,当这些图书的信息汇聚为一本《论确定性》的书,一切都是确定而不容怀疑的,但是这种“确定性”可以变成一种“我知道”的句式?:我知道这是维特根斯坦在去世前一年半写下的手稿;或者再扩展,我知道编辑取了《论确定性》作为书名在他去世后出版了;再扩展,我知道维特根斯坦针对摩尔的命题进行了批驳;再扩展,我知道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确定性位于语言游戏的本质之中这个著名的观点……
从手稿写作,到编辑出版,似乎在“我知道”中是一种对客观性的描述,这种客观性并不需要怀疑,因为它就是真的事实,但是维特根斯坦对摩尔观点的批评和自己提出的思想,是不是“我知道”的事实?它显然具有某种可怀疑的成分,或者后两个“我知道”可以被别人轻易就提出疑问:你真的知道了吗?这句话就像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那样,可以变成“我以为我知道它”的表达,那么这个被冠在“我知道”之前的“我以为”是不是取消了和事实相符的部分,取消了为真的判断,甚至只是成为了对人们某种质疑的辩护,而反过来可以扪心自问的是:我真的读懂了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里的观点?它被我自己所怀疑,连同辩护本身都成为了一个理由,于是,真正的事实是:我知道我没有读懂它,这种“知道”直接变成了一种对确定性的表达:我确信我没有读懂它。
那么,“知道”是不是就是一种不容怀疑的确定性?在这里,其实有两种疑问,一种是他人对“我知道”的怀疑,另一种则是转向自我时对“我知道”的自我怀疑,从“我知道这是一本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手稿而出版的一本书”的确定性到“我知道我没有读懂它”的怀疑,确定性是如何从一种事实变成一种面对怀疑的表达?维特根斯坦似乎在这本书里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这是一只手,那么我们就会向你承认其余的一切。”维特根斯坦在第1节中就指出了“知道”指向的对象,那就是“一只手”,一只手在这本书的封面上,还有另一只手,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它们没有合上,它们是一个人的两只手?还是各自属于不同的两个人?和确定性有关的手,也是和“知道”有关的两只手,毫无疑问,不管哪只手,它都和关于确定性讨论的摩尔有关,它是这个论题的起点,当然它也和维特根斯坦有关,它是从这个起点而走向确定性的另一个起点,但是从一一直手到另一只手,真的如维特根斯坦开宗明义所表达的那样,在“知道”的意义上达到“承认其余的一切”?
第1节的表述一半放在后面的括号里,“人们说这样那样的命题不能被证明,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从其他命题中被推导出来,每个命题都可以从其他命题中被推导出来。但它们可能并不比它本身更确定。”从证明到推导,从本身到其他,这是关于命题确定性的一条轨迹,而这句话也很明显是针对摩尔的观点。关于知识,从笛卡尔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任何单独的偶然命题是否可以被确定地知道为真,也就是说“知道”天然地指向了确定性,而确定性则是为真的命题,在摩尔看来,比如这样的命题:他是一个人,他正指着那个对象是他的手,地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这些都是单独的命题,也都被确定地知道为真,“我们都处于这种奇怪的位置上,那就是我们确实知道很多东西,关于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我们一定有过它们的证据,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它们的,换言之就是我们不知道这证据是什么。”之所以被确定地知道为真,就是因为命题所集合的都是偶然真理,因为这些本身就是常识命题,而即使不是常识命题,比如存在着一个外部世界,时间是真实的,自我存在,这些哲学命题也都是偶然真理,在不需要证明的情况下它们就是确定地知道为真。
| 编号:B87·2250503·2300 |
但是,“知道”就真的意味着确定地为真?真的不需要对命题进行判定?偶然真理在摩尔那里其实就是“看来它是这样”,但是能否得出“它就是那样”?从“看来”到“是”,这其中是不是还有更多可以怀疑的不确定性?在这里维特根斯坦直接指出了像摩尔那样做,“我相信是不行的”,因为“知道”在这里被误用了,它可以是“我以为我知道”这样的表述,也可以是“我在生活中表明我知道这是一只手”的赘言,甚至是“我知道这里躺着一个病人”的胡言——在关于确定性中,这些表述是胡言乱语,但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命题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而这种使用很明显是在语言表述的层面,当我说“我知道”的时候,意味着对我的陈述有恰当的理由,而当别人熟悉这种语言游戏的时候,他当然会承认“知道”为真,也就是说,“知道”是在语言游戏中才是合理的,才是理所当然的,才在没有怀疑的地方。
语言游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体现在表达具有的“正常情境”,也使得确定性变成一种断定事实的语调,不管是情境还是语调,都是在语言游戏的层面中展开的,所以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将其视为从哲学语言中踢除出去的确定性,“人们就像被迷住一般一再地回到这些命题,而我想要将它们从哲学语言中剔除出去。”从哲学中剔除是不是意味着回到日常,回到经验,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一种预设,是为了一个实践目的而做出的决定,是语言游戏中的形式,“词语的一种意义就是对其的一种使用。因为这就是当这个词被并入我们的语言中的时候我们学到的东西。”所以语言的意义就是一种职能,“如果语言游戏变了,概念也变了,词语的意义也随之改变了。”维特根斯坦把“知道”的确定性看作是一种语言游戏,是一种表述,一种实践,一种运用,那么,“确定性的程度是如何显示出来的?它有什么结果?”
确定性也可以是记忆的确定性,感知的确定性,当我知道的时候是确定的,但是我也知道“什么检验能证明我错了”,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否设想一个总在我们认为错误不可能,并且也不会遇到错误的地方犯错的人?”他将一种错误看成是某种精神紊乱,而用检验陈述的方式来解释错误,这个错误当然也不会被接受,“被视为对一个陈述的充分检验的东西,是属于逻辑的。它属于对语言游戏的描述。”回到这个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那些经验命题的真“属于我们的参照系统”,对于这个参照系统,“我知道”就是这个系统里表述的一种关系,不是和意义的关系,而是和事实的关系,“于是事实被收入了我的意识。”就像看见一样,知道借助视线感知外部事件,它是一种想象的“知道”,而位于这个想象根基处的东西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图景”,“我之所以有我的世界图景,并不是因为我确信了它是正确的,也不是因为我对其正确性深信不疑。它是那个被继承下来的背景,我借助这个背景来区分真与假。”
这可以视为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另一个层面,世界图景的命题是“神话性”的,“人们也可以纯实践地、无须任何明确规则地,学会这个游戏。”也就是说,世界图景的命题没有真也没有假,不被怀疑也不被证明,它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我们的所有论据的某个多少有些任意和不可靠的起点,相反,它属于被我们称为‘论据’的东西的本质。”这种本质就是论据的生命意识,“让我们信服的是一整个判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中,结果和前提相互支撑,一个人就和整个人类保持一致,所以,我知道自然就变成了我相信,“我知道的东西,我就相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表达了逻辑经验论的主张,“人们必须从解释走向纯粹的描述”。
因为我知道,所以我相信;命题不再是解释,而是纯粹的描述,这些都是语言游戏,但是维特根斯坦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一个命题的真是确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通过“我知道”而确信并试图说服别人,就是把主观的确定性变成客观地确定,那么如何实现?按照传统的哲学命题,为真的客观性就是一种符合论,但是当摩尔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如何能在证明中“符合”事实?维特根斯坦认为,与实在相符这个观念并没有清晰的用法,它也只是世界图景的一部分,语言游戏就是从这个信念出发的,所以,在语言游戏根基处的不是观念论,而是“我们的行动”,我们通过理智行动,理智的行动就是不怀疑事实,这种不怀疑就是“无理由的信念”,也正是在这种蘑菇有充分理由的确定性中,使得确定性成为了客观的东西,“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相信或确定我的朋友的身体或头脑中没有锯屑,虽然对此我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官证据。基于别人告诉我的东西、我读到的东西以及我的经验,我是确定的。”就像松鼠冬天储存食物,不是通过归纳来作出的决定,而是确信,“我坚定地确信其他人相信,相信自己知道一切都是这样的。”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其实区别了命题为真和命题的意义的不同,这无疑是对《逻辑哲学论》中“两极性”的一种补充和深化,在他看来,命题有意义和命题是偶然的联合并非是为真,而是缺乏意义,但并不是无意义,它们是“真理的旁边”的命题,“知道”和相信的命题并不在求真的认知范围里,而是一种偶然的事实,它们不可能被设想为怀疑的东西,也就不可能被知道,不可能被确定,也就是说,在真理的旁边是为真的东西之外的存在,它由一个被接受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为真本身,也不是我们知道的真,而是使真成为真,但基本本身却不能被知道,所以,这个基础的存在就是作为知识被知道的“前知识”,语言游戏就是这个前知识的一个片段,“你必须记住,语言游戏可以说是某种不可预见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它没有理由,也不是合理和不合理的范畴里讨论,毋宁说,“它在这里——就像我们的生活。”
语言游戏之所以存在,从来不指向一种为真的事实,而是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一种保证,“这个保证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即使预言得不对,它也可以被视为是合理的。”于是“我知道”就变成了真理的基础,变成了实践,变成了行动,引用浮士德的话就是:“太初有为。”实践和行动本身构造的就是确定地为真,“是的,确定性就位于语言游戏的本质之中。”于是在打开和合上这本书之后,我可以说:“我知道我阅读了这本书”,当然,我也确信我读完了维特根斯坦的手稿。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