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06《千柱之城》:生来就是混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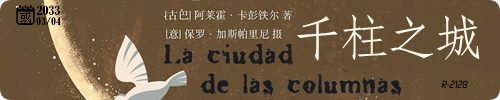
不过,当我们把歌德的朋友的这本书再往后翻上两页,便会在他对商人街的描写中看到这样的文字:“这里跟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一样,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把规划得一塌糊涂的街道改造好。”
——《一》
定价69元,对于页码只有132页的图书来说,还是显得虚高了,而且132页的书包含了介绍“卡彭铁尔作品集”的一篇《大师中的大师》代序,和《蓬勃“粗野”的哈瓦那,巴洛克精神的万花筒》的译后记,去头掐尾的话,真正的内文只有几十页,而这只有四万多字的图书,三分之二的内容则是意大利摄影师保罗·加斯帕里尼的摄影照片,也就是说,这正属于卡彭铁尔文字的只有一本书不到一半的量,本来就是虚高的价格,如此拆解分析,图书就完全是一种圈钱的注水行为——为什么非要把这样一本“哈瓦那指南”的小册子单独出版,构成《卡彭铁尔作品集》中的一本?
当然,这不是卡彭铁尔本身的错。从卡彭铁尔写作的目的来说,也是完全为了配图,一九六三年,旅居古巴的意大利藉摄影师保罗·加斯帕里尼出版了表现哈瓦那街头建筑的摄影集,卡彭铁尔是保罗的好友,于是他专门为这本影集撰写了文案,文章被收录进他的散文集《触碰与差异》之中,后来又以《千柱之城》之名配图独立出版。配图的意义不只是对照片进行解说,实际上卡彭铁尔在介绍哈瓦那这座“千柱之城”的文字,表达着他对这个古老城市的某种情感,在这里就有了某种情结:保罗旅居古巴,用照相机拍摄了哈瓦那城市的建筑细节,可以说,他是用摄影机记录和解读着这座城市,这是西方视野的一次看见,卡彭铁尔之所以为好友的这部摄影集配文,在某种意义上他找到了对城市观察的契合点,而这也是他和西方世界的一次对话。
如果说他和保罗之间文字和图片的对话是一种契合式的对话,那么他在开篇时对德国作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引用却颇有微词。十九世纪初,洪堡来到了哈瓦那,写下了关于这个城市的文字,他乘船一进入哈瓦那港,就被这个赤道以北的热带每周国家的景色所吸引,他形容是“最为赏心悦目、如诗如画的景象”,“陶醉在如此旖旎的风光里,一个生活在安的列斯群岛熙攘城市中心的欧洲人,会忘掉他身边所有的危险,只顾一心去探求这片广袤山川中多姿多彩的元素,去远眺矗立在港口东面岩石上树,以及半掩在桅杆与风帆之林的城市……”这是洪堡的一次看见,完全可以用惊艳来形容这位西方人对哈瓦那的发现,但是正如卡彭铁尔所说,如果再往下翻几页,就会读到他的另一段话:“这里跟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一样,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把规划得一塌糊涂的街道改造好。”在这里洪堡明显将哈瓦那放在和欧洲城市的对比之中,而且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一塌糊涂的街道”,那就是必须经过“规划”,如此才能告别一种古典主义,达到整齐有序的现代水平。
初次看见哈瓦那港,是感受到了赏心悦目的美景,但是在商人街里看到了“一塌糊涂”的街道,这仿佛就是自然和建设上的差距所在,卡彭铁尔曾就读于哈瓦那大学建筑系,虽然被迫退学,但是他对于建筑也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洪堡的抱怨带着西方视角,对于哈瓦那来说,糟糕只是一种表象,它的背后却是“一种伟大的智慧”,因为作为热带地区的城市,哈瓦那满足了生活在这里的人最大的需求,那就是“与烈日捉迷藏”:那些修建起来的“修士街角”,就是从太阳那里抢夺阴影,还有老城的“墙角”,还有五颜六色的“涂鸦彩墙”,都是为了使人们逃离烈日的炙烤,虽然在洪堡的看见中它们一塌糊涂,但是“它带来的安静与清凉的感觉”,在那些被规划得整整齐齐的作品中很难被找到。卡彭铁尔认为,哈瓦那的阴影就是“一切向着西方萌芽和生长的事物的对照面”,西方人追求规划,追求规划中的齐整,追求齐整中的现代性和秩序感,但是哈瓦那并不需要这一西方标准,它“天生就是为了利用阴影而修建的”,哈瓦那不应该是规划之城,而是一座“阴影之城”。
| 编号:E57·2250519·2306 |
“正是在这个现实间的纷繁、交错与嵌套中,一整套常量在这里油然而生,哈瓦那也因此成为了美洲大陆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卡彭铁尔认为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读者认识某些常量”,因为常量赋予了哈瓦那独树一帜的鲜明风格——如果规划造就的是城市的现代风格,那么在卡彭铁尔看来那属于学院派,对于哈瓦那来说,风格就是常量赋予的,“除了哈瓦那大教堂广场、哈瓦那老广场、政府机构所在的市政广场,这座城市的街道全都被故意设计成狭窄逼仄的模样,以求投下更多阴影,使得路上的行人无论日出还是日落,都不会被炽烈的骄阳直射脸庞,炫花眼睛。”可以说常量就是西方视点对照面的“阴影”,但是卡彭铁尔为什么不把这本书称为“阴影之城”而用了“千柱之城”这个名字?阴影制造了安静和清凉,阴影体现了人们的伟大智慧,但是寻找阴影、抢夺阴影更多是从实用主义层面来解读的,但是真正属于哈瓦那独树一帜的风格就体现在柱子所代表的巴洛克精神中。
“从那些宫殿般的古宅中和那些依然保留着旧容颜的豪邸中都可以看出,立柱在十九世纪前一直是内庭里奢华的点缀,直到十九世纪后才走上街头,并在建筑已经明显走下坡路的年代里,创造出了哈瓦那风格中那个最为标新立异的常量:柱子在以柱子闻名的城市里难以置信地蔓延。”柱子是多立安式的柱子,是科林斯式的柱子,是爱奥尼亚柱子,是女神柱,“可以说,哈瓦那城中的柱子之多,是美洲大陆上任何城市都无法匹敌的。”之所以把这些柱子看成是哈瓦那城市的风格体现,就在于它体现了从古至今的“常量”:巴洛克主义。卡彭铁尔对哈瓦那这一常量的介绍是通过内和外不同层次的连接发生的:哈瓦那的街头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市井喜剧、小丑滑稽戏、神话群像剧在这里不断上演,而完全不同的宅院则追求与世隔绝的效果,它守护的是主人的生活隐私;从街上的热闹到宅院的安静,内和外构筑了不同的风格,卡彭铁尔就引领着读者进入到哈瓦那的常量世界。
在宅院里,体现巴洛克风格的就是气象万千的铁栅栏,它们借鉴了格列柯博物馆里的山羊花样或阿兰胡埃斯的宅邸花样,也模仿了古巴卢瓦尔古堡中的样式,无论是豪宅、杂院,还是宿舍、窝棚,铁栅栏构筑了不同阶层建筑的独特风韵,“哪怕是寒酸得连油漆都没涂的门板外的一扇只有单个涡旋的铁栅栏,也出乎意料地惹人注目。”除了铁栅栏,老宅里的另一种风格体现就是阳台,它们在街角蔓延,形成了与铁栅栏密不可分的“阳台隔”,为重重的阁楼划分了疆界;另外还有锈迹斑斑的护墙套,被海盐腐蚀成绿色,但是那些装饰图案还是清晰可见。立柱、铁栅栏、阳台隔和护墙套以及窗边的装饰图样、雕花木的镶嵌、古怪的面饰、檐角的排水兽,共同构成了街头巷尾的古巴风格。这些也还是一种外部的风格展现,而在宅邸的内部,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假门的“幔笆拉”,它们被截短到与人身高齐平,它们通过合页叠加到真门前面,它们以遮挡的方式制造了特殊的群居关系,看起来因此而养成了高声喊话的习惯,但是当喧嚣声透过流光溢彩的贴花玻璃而被传递,它反而更有利于彼此的交流,当然,“幔笆拉”也体现着一种建筑风格,“它们被安放在花木扶疏的院落与五彩斑斓的半圆花窗之间,后者作为阳光与阴影的分界线,构成了古巴巴洛克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元素。”
从热闹的街上到安静的宅邸,从宅邸外观的立柱、铁栅栏、阳台隔和护墙套,到再进入里面的“幔笆拉”,卡彭铁尔构筑了从内到外“进入”的视线,剖析了哈瓦那日常生活的常量。也正是从“阴影之城”的实用到“千柱之城”的风格展现,卡彭铁尔阐述了存在于西方对照面的精神,立柱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调节,这种调节体现的正是美洲巴洛克主义别具一格的表达,一方面它所调节的是太阳和阴影之间的矛盾,避开日光的直射,永葆静谧和安详,而另一方面也是历史和现代的调节,卡彭铁尔认为哈瓦那的巴洛克主义比较接近的是西班牙的塞戈维亚和加迪斯,而在时间的沉淀中,巴洛克风格就成为这种调节的产物,“幸运的是,这个国家就像墨西哥和上秘鲁一样,生来就是混血的。”它是共生,是添加,是交杂,千柱之城的“千柱”,就是多立安式、科林斯式、爱奥尼亚式以及混合风格的立柱和廊柱的积累、汇聚和繁衍。
混血的柱子,混血的风格,混血的城市,哈瓦那就是在共生、添加和交杂中保持着属于这个城市的常量,卡彭铁尔更是将这种可见的常量内化为一种精神,“巴洛克精神天经地义就是安的列斯群岛的精神,是这片‘美洲地中海’中各个岛屿跨越文化的混血精神,它体现在对经典的柱顶范式既无礼貌又无章法的颠覆上。”1519年建城的哈瓦那,从最初的一座广场、一所教堂和几幢楼房开始,五百多年的城市历史就是不断在共生、融合、创造的混血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它是建筑意义的,更是文化意义、信仰意义的,宛如波德莱尔诗句中的神殿,“活灵活现的柱子时常发出含糊不清的絮语。”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