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6《纯粹现象学通论》:反思中将自己领悟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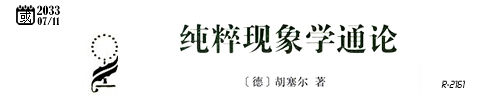
知觉的现在不断变为与刚刚过去者接联的意识,同时一个新的现在闪现出来,如此等等。
——《意识和自然现实》
我的面前是一张桌子,我看着这张桌子,然后绕着它走动,一方面在我走动而改变的位置中,在不同位置而进行的观看中,所构建的知觉也是不断在变化的,甚至当我闭上眼睛不看是,我的感觉和桌子无关,我对它也没有知觉,当我睁开了眼睛,我又有了知觉,不同位置的得到的知觉是不同的,闭上眼睛和睁开眼睛的知觉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毋宁说是对桌子的知觉不同,但是桌子却是同一个,而这个同一个就是将记忆等和知觉合在一起的同一个,它就是被体验为同一个东西的“综合意识”,也就是说,桌子作为实体具有事实存在性的同一性,尽管知觉发生着变化,但是知觉本身作为连续意识流中的东西是一种连续流的存在,连续流将知觉接连为意识,在意识中桌子被体验为同一个东西。
这是胡塞尔在阐述现象学中所举的例子,也是被引用为理解知觉和意识之间关系的经典例子,桌子是一种实体的存在,知觉在某种程度上都只能被知觉到实在的一个部分,颜色、光线、形状这些侧显功能所组成的只是感觉材料,并不是颜色、光线和形状本身,也就是说,侧显只是体验,它并不是作为某种空间物而存立,而作为空间物是超越对物的知觉的,但是,为什么我所意识到的依然是作为桌子这一实体的体现?在这里其实凸显了超越的可能和不可能,一方面,知觉是一种内在体验,物是超越对物的知觉,那么内在体验和超越物之间就存在着一个矛盾:我的内在知觉如何能达到外在的超越物?这种对立其实体现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一种错误看法认为,知觉并未达到物自身,而另一种荒谬的看法则认为在超验物和存在物之间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他在上帝的直观中都属于上帝意识流和体验流的一种体验。
而另一方面,我们看见的空间物,并不需要通过所有知觉的总和才能形成对物的意识,即使它是超然于内在体验而存在,也是某种被知觉的东西,依然是意识所与物,意识根本不是代替空间物的一个“记号”,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又是超越性的。在心物二元论形成的内在体验和超验性的物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成的连续流又将超验性的空间物成为被知觉的对象,知觉如何在内在的不可怀疑和超验的可怀疑性中形成被意识的体验?这就是胡塞尔所说的“我思”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反思中被知觉把握的东西,不只是被基本地刻画为某种存在的和在知觉目光中持存的东西,而且也是某种在这种目光朝向它之前已存在的东西。”当我们说“一切体验都是被意识的”的时候,意味着与意向体验的有关东西,不只是某物的意识,不只是作为它们本身是反思意识的客体时作为呈现者,而是在未被反思地已经作为“背景”而存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不依附于任何条件的“我思”:我存在着,我生存着,而这个反思地主体“我”就是无条件和必然的纯粹自我,它是自我生命的设定,是绝对无疑的存在,就是先验主体。
纯粹自我和自我生命的设定,是必然和绝对无疑的,而世界的设定则是“偶然”的,这个偶然的世界设定和必然的纯粹自我设定是对立的,这种对立其实就体现了事实和本质的区别,而这也是胡塞尔提出纯粹现象学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一般的认识论是以感性经验为开端的,它就是对个别存在的“偶然的”经验,由此形成的经验科学就是关于“事实”的科学,这就是胡塞尔提出的“自然的”理论态度,它用自然的思想方法研究“世界”,“世界是关于可能经验和经验性认识的对象的总和,是关于那些根据实际经验在正确理论思维中可认识的对象的总和。”经验论所使用的认识方法就是这种自然思想方法,但是在胡塞尔看来,经验的科学是关于个别的、偶然的存在的“事实”的科学,它无法建立普遍的规律,当然无法把握纯粹的本质。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呈现其为“什么”的东西,只有纯粹的、严格的、绝对无条件性的一般性才具有本质的特性,它是全称判断,是“一个自身如是的存在物”。
事实和本质就是偶然和普遍性的区别,它体现在认识的直观之上:自然的思想方法依赖经验,经验是一种自然的直观,个别的直观,而要对本质的认识就需要一种“原初给与”的直观,这就是本质直观,“本质直观的所与物是一种纯粹本质。”但是本质直观却寓于个体直观之中,个体的显现、被见都是个体直观的部分,是未被把握的个体,也未被设定具有任何现实性,但是却有一种朝向“相应的”个体的目光,并形成示例示性意识的自由可能性,它使得个体直观成为本质直观,这种朝向个体的目光就是观念化的作用,就是胡塞尔所说的反思,从个体直观到本质直观,从事实走向本质,从自然的思考方式变成纯粹现象学,这就是胡塞尔提出的任务,“产生现象学态度,并通过反思将其特殊性和自然态度的特殊性提升到科学意识层次,这是首要的然而绝非轻而易举的任务。”他提出的纯粹的现象学,即先验的现象学,就是作为本质的科学被确立,“作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将专门确立无关于‘事实’的‘本质知识’。”
| 编号:B82·2250421·2288 |
所以现象学的态度,首先就要厘清基于个别直观、对于事实认识的自然的态度。在自然态度的科学看来,世界就是我和我周围的世界,世界永远是事实存在的世界,全面而可靠的认识世界就是经验的认识,并解决呈现在这个世界里的一切科学认识问题,这当然是一种朴素的经验论,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解决心物二元论问题,无法解决内在体验和超越性的物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一种新的考察办法,这就是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还原就是将属于自然态度的设定“失去”作用,将该设定的一切存在性方面都“置入括号”之中:不仅要排除自然界,即心理的和心理物理的世界及其认识的对象,还要排除超验者的上帝,排除作为普遍科学的纯粹逻辑,排除一切本质性学科,之所以要置入括号,是因为它们以自然思考的态度产生了一种“概念转移”的悖谬,但是,置入括号的现象学还原并不是要去除一切,“观象学的突出特性就在于,在其本质普遍性范围内包括进一切知识和科学,而且尤其是在有关一切可被它直接洞见的对象方面,或者至少必定会如此,如果它们是真正的知识的话。”一方面,置入括号只是意味着让自然态度的设定失去作用,但是这个自然世界还是持续地“对我们存在”、“在身边”存在,作为被意识到的现实也是永远存在着的;另一方面,被现象学加括号被排除的东西仍然属于现象学领域,而且经受了排除作用的实在和观念的现实,将通过“整个意义和命题的复合体”将再现于现象学领域内。不管是置入括号还是再现于现象学领域,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目的是达到一种“科学”的认识,“即赋予它理论的形式和掌握它,使它成为一个从纯本质直观中产生的关于概念和法则陈述的体系。”
当排除了整个自然界的心理无力世界,那么还留下什么?留下的就是“绝对意识的整个领域”,胡塞尔认为我们的目光就指向“在其自身绝对独特存在中的纯意识”,纯粹意识就是先验主体即纯粹自我的意识,在胡塞尔看来,纯粹自我是某种本质必然的东西,是作为在体验的每一个实际的或可能的变化中某种绝对同一的东西,它完完全全生存于每一实显的我思之中,一切的背景体验都属于它,也是自我所有的一个体验流,在转变为实显的我思过程或以内在方式被纳入其中,就像康德所说,“我思必定能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所以纯粹自我就是现象学材料,而且,“一切超出此界限的与自我有关的理论都应加以排除。”那么,纯粹自我的意识即纯粹意识,又如何在直观中把握本质?这就涉及到纯粹意识的一般结构。
首先,“绝对的”存在的先验意识王国,在现象学还原中产生了,它是一般存在的原范畴,“一切其他存在区域均植根于此范畴,按自己的本质均相关于此范畴,并因而在本质上完全依赖于此范畴。”只有通过现象学还原,作为意识的存在才能在纯粹性中达到和证实。而在纯粹体验领域的最本质特性中,反思无疑具有普遍方法论的功能,现象学的方法完全在反思中起作用,反思指向自我体验并成为自我的客体,反思是体验,而作为反思它又是新反思的基地,以此形成了一种无穷的反思过程,它以“体验流”的方式形成了一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意识流内的自我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反思在每一种“我思”中都将特定意义的每个行为都具有了自我行为的特征,“在反思中我将自己领悟为人。”而另一方面,体验流也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学时间,“每一单一的体验,如喜悦体验,均可开始和结束,因此界定了其绵延。但是体验流不可能有开始和结束。每一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体验都是其纯粹自我的体验。”
体验流是纯粹自我的体验,是现象学时间的体验,当然它也是意识流,是意识的统一体,这里就涉及到胡塞尔的意向性,意向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现象学结构名称,他指出,一切知觉形式均以意向性意识结构为前提,意识与世界之关系亦应在此意向性结构中考察。胡塞尔强调的是,意向性是自我的活动,体验中的超越性客体均为自我活动功能之“成就”,意向性于是就是意识生产性行为和能力之条件,它既不是物质性关系也不是内在于主体的特性,而是一切意识活动之条件。对意向性的各种界定和描述都离不开自我和对象这两侧,因而意向性的一个别称是“关注”,“自我对某物之关注”就相当于“意向地指向某物”,所关注之物即行为的“主题”,主题遂成为自我的“目的”,自我朝向主题的方式即为设定之方式。意向性是一种朝向,“对某物的意识”就是纯粹自我为出发点的充分自明的东西,它涉及到意向作用和意向对象,在胡塞尔看来,意向作用是作为构成性的、意义给与性的现象学概念,意向作用侧的分析又称综合学分析,即一切对象均经意向作用而成为综合统一体,它们从此综合作用中取得意义,而意向行为的意义即意向对象,意向对象为一统一性和复合性的对立结构,按此结构意义复合体被赋予一个单一客体。换言之,统一体为主词,复合体为属于主词的一个谓词系列,此意向对象结构存于一切意向意识中,包括虚构意识。
意向对象就是“意向性客体”,当意向的体验在意向性客体中构筑了意向关系,也就产生了对象的意义,意义就是一切意识的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就不是一般体验而是有意义的体验,这种意义一方面表现为:意向对象本身就在自身之中,通过它自己的意义有对象性关系,而另一方面,意识的意义又如何达到对象?胡塞尔在这里指出了“意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意识在意义或通过意义相关于某种作为“意识的”对象的对象物,也就是说每一个意向对象都有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它的意义,通过意义相关于它的对象。这一意义的重要性就在于:每一个意向对象中有固定的内容被界定着,意识既是其“什么”,也都有“它的”对象物,“正如它被意指着一样”,意义也就不再是具体的本质,而是内在于意向对象之中的抽象形式。正因为每一种意向体验都有意向对象和在其中的意义,意义和对象相关,而对象即使是作为现实面对的对象、谈论的对象、可能发生的对象,都必定是意识的对象,“这意味着,不论世界和一般现实可能是什么和被称作什么,它们必定通过充满着或多或少直观内容的相应的意义或命题,再现于现实的和可能的意识框架内。”
也就是从这一层重要性的发现中,胡塞尔开始了向理性现象学的过渡,那些本来被排除而置入括号里的实在和观念的现实,就能通过整个意义的复合体再现于现象学领域之内,而这才是胡塞尔的目的,“赋予它理论的形式和掌握它,使它成为一个从纯本质直观中产生的关于概念和法则陈述的体系。”理性的现象学就是在合乎理性中认识对象,它们是“有根据”的、“明示”的、直接“看见”的或间接“洞见”的,也就是说,不是设定的偶然情况和偶然事实,而是普遍本质理解中把真正存在的观念与真理、理性、意识的观念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意义和对象都原初被充实的意义和对象,“对象正是在充分直观中被把握为,被设定为原初性自身的东西,它由于原初性而是洞见的,而且由于意义的完整性和完整的原初意义充实化遂为绝对洞见的。”这就是还原之后的再现,它所通向的就是科学的道路,“因此须要如我们已经在做的那样去研究与意识的普遍结构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但是,胡塞尔立下的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成写作,有关由自然科学、心理学和精神科学诸学科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以及尤其是有关它们与现象学关系的当前大量思想所涉及的争论问题,并没有以这样的方式纳入克研究的范围,或者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也变成了他的一种“悬置”。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