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18《资治通鉴(十四)》:举之以众,取之以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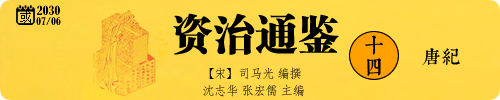
《资治通鉴》第十四册记载了《唐纪三十九》至《唐纪五十二》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763年癸卯七月,尽于公元805年乙酉。
【政刑日紊】
安史之乱爆发于唐玄宗末年,这是安禄山和史思明背叛朝廷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七年多的安史之乱使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内锐减,这也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宝应二年春天,随着田承畴献莫州投降、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在林中自缢身亡、雨下叛军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安史之乱始于唐玄宗,终于唐代宗,在宝应元年时,唐肃宗病死,李豫被宦官李辅国等拥立为帝,是为唐代宗,唐代宗命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仆固怀恩等打败史朝义部叛军,收服洛阳及河北诸郡,次年彻底平定安史之乱。唐代宗在位期间,又遭遇吐蕃趁乱攻占河西、陇右之地,吐蕃又于广德元年长驱占领长安,唐代宗出逃陕州,随后起用郭子仪击破吐蕃。永泰元年,又用郭子仪等平定仆固怀恩之乱,而此后由于藩镇势力壮大,唐朝又陷于藩镇割据之乱。
唐代宗室唐代历史中的关键人物,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了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和击破吐蕃之史事,但也指出了唐代宗最大的弊病,那就是宠信佛教。对于唐代宗如何会从相信佛教到好佛,《唐纪四十》记载了这一过程。大历二年,“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甚,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可以说,戴总从未甚重佛到重新佛教,受到了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很大的影响,当时的唐代宗问他们:“佛信报应,果为有无?”元载等人的回答是:“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富液观所传达的就是典型的因果报应,他们举例说,安禄山和史思明翻盘朝廷,最后被他们的儿子杀害,仆固怀恩叛乱才出门就得病而死,回纥、吐蕃大举进攻,最后也是不战而退,所以种种都是“小灾”,并不能对唐朝的福业产生破坏,由此他们对唐代宗说:“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
于是,“上由是深信之”,这深信表现在诸多方面:他在宫中设斋,供养一百多名和尚;有敌人进犯就名和尚宣讲《护国仁王经》,以此祈祷免灾,当敌人撤退之后又赏赐给和尚丰厚的礼物;那时有个胡人和尚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宫中连权贵们都要看他脸色;京畿地区的良田和获利大的事业月多归佛寺所有;戴总还下令不得鞭打和欺负僧尼,还在五台山关键早金阁寺,所耗资金数以亿计;王缙将中书省的文书发给和尚,命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到全国各地募捐集资,用来建造佛寺。大历二年六月,宦官鱼朝恩奏请以自己获赐的宅第为章敬寺,为章敬太后吴氏祈冥福。该寺修造得极其宏伟壮丽,浪费大量木材,以至于要拆毁曲江及华清馆,进士高郢上书劝谏这一劳民伤财的行为,李豫仍置之不理;大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七月丙戌,“内出盂兰盆赐章敬寺。设七庙神座,书尊号于幡上,百官迎谒于光顺门。自是岁以为常。”
由此,唐代宗崇信佛教达到了顶峰,在唐代宗的影响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对于唐代宗废人事而奉佛,奉佛而“政刑日紊”,也表达了司马迁一以贯之的佛教观。
【不素餐兮】
《唐纪四十一》中司马光还发表了一些议论。“元载、王缙之为相也,上日赐以内厨御馔,可食十人,遂为故事。”在大历十二年八月癸卯,常衮和朱泚层就此事上书代宗,“餐钱已多,乞停赐馔。”认为应该厉行节约,制止这股歪风。当时的代宗表示同意,常衮又想辞掉自己宰相的封邑,以更彻底的方式停止对官员的赏赐,当时的同僚们认为不行,常衮才了事,但是他们讥笑他说:“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
同僚的讥笑其实表明,制度性的改变才是关键,俸禄供养贤人并没有错,错的是供奉的太过丰厚,所以更为彻底的不是取消俸禄,而是辞位。对于这一事件,司马光评论说:“君子耻食浮于人;衮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他认为,和那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贪图俸禄的人相比,常衮至少还有廉耻之心,也就是说,那些贪图享受的人才是真正的蛀虫,引用《诗经》上的话,“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不劳而食的人才应该感到羞耻。
【进退赏罚】
大历十四年五月癸卯,代宗开始患病,辛酉日,下诏让皇太子代行处理国政,当夜,代宗在紫宸殿的内殿中驾崩,遗诏让郭子仪总摄群臣,辅助朝政,癸亥,唐德宗即位。唐德宗即位之后,常常住在服丧的地方,而政务交于崔祐甫处理,这种方式在司马光看来,具有很大的隐患。
至德年间以后,天下用兵之权由元载、王缙掌控,于是四面八方前来行贿的官员盈于门庭,官大的出自元载、王缙之手,官小的则出自卓英侍等人之手。到了常衮担任宰相的时候,他想要革除这一弊端,以此杜绝人们侥幸得官的途经,所以他对各地上奏的请求,一概不予考虑;在崔祐甫取代常衮出任宰相的时候,他为了收罗当时有声望的人,引荐推举者每天不断,担任宰相不到两百天,就任命了八百名官员。可以说,常衮和崔祐甫同为宰相,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用人方法,看起来是彼此的弥补,但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用人的适当尺度。有一次唐德宗问崔祐甫,为什么你所任用的官员多沾亲带故,崔祐甫回答说:“我为陛下选择官员,不敢不审慎。假如平时不认识,我怎么能知道他的才干德行而任用他呢?”
司马光认为正确的选人用人观在于:“无亲疏、新故之殊,惟贤、不肖之为察。”贤能与否才是唯一的标准,而不是亲疏、新老之别,如果任用的人不是贤人,但是因为亲朋好友的关系而被录用,“固非公也”,同样,假如是贤人,因为亲朋好友的关系而被舍去,“亦非公也”,所以,“夫天下之贤,固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待素识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遗亦多矣。”担任宰相,最重要的是识人,而识人的关键不是一个人决定,只有“举之以众,取之以公”才是真正的公正,即使被人举荐而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本事,也可以之后将他辞退,“所举得其人则赏之,非其人则罚之。”只有这样“进退赏罚”的制度建立,只有撇除个人的私心,“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遗贤旷宫之足病哉!”
【功盖天下】
建中二年六月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病逝。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吐蕃之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德二年,收复两京有功,加司徒、代国公,又进位中书令;乾元二年,承担相州兵败之责,失去兵权,处于闲官;宝应元年,平定河中兵变有功,进封汾阳郡王;广德元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长安失陷,再度被启用,出任关内副元帅,收复长安;永泰元年,吐蕃、回纥联兵入侵,在泾阳单骑说退回纥,并击溃吐蕃;大历十四年,唐德宗即位后,尊为“尚父”,进位太尉兼中书令。
可以说,郭子仪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而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没有以“臣光曰”的方式对郭子仪进行评价,而是指出了他为什么不被诽谤的原因,“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毁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举例来说,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举家三千人,有八个儿子、七个女婿,都是朝廷中显要的官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都是他的部下,他们虽贵为王公,郭子仪却常对他们颐指役使……
为什么郭子仪可以得到这样的地位?“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
【一新其政】
唐德宗李适在位前期,以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用杨炎为相,废租庸调制,改行“两税法”,颇有一番中兴气象;之后任用幸臣卢杞等,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间架、茶叶等杂税,致使民怨日深;建中二年,李适发动削藩战争,但因社会和政治条件不成熟,反而致使四镇之乱与泾原兵变接连爆发,他被迫出逃,辗转奉天、梁州等地,最后依靠宰相李泌及大将李晟、浑瑊等人协力平乱;执政后期,转而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藩镇多事姑息。
对于德宗在位期间的功过,司马光很少有直接评论的,但是在《唐纪四十九》中,对唐德宗在贞元三年所做的一件事表达了“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的抱憾之情。“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这是丰收的征兆,但是在十二月庚辰,唐德宗在新店打猎,恰好去了农民赵光奇家中,在这次私访中,德总问他老百姓是不是高兴,没想到赵光奇直接回答不高兴,庄稼丰收了为什么百姓却高兴不去来?赵光奇说出了原委,那就是“诏令不信”,以前朝廷说两税之外再无其他的徭役,但是实际上不受两税反而搜刮得比两税时还多;官府又说是收购粮食,但实际上却是强行抢夺粮食;以前说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缴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几百里地百姓的车坏了骂死了人破产了,所以说,所谓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百姓依然过着忧愁困苦的生活。
赵光奇指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就在于皇帝深居在九重皇宫之中,对民间疾苦一无所知。当赵光奇说出了百姓之苦的真正原因,唐德宗便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德宗能够私访民间,听到赵光奇关于百姓生活的真实现状,也是他走出九重皇宫的一次实践,而免除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也是体察民情的一种举措,但是司马光却认为他“难寤”,原因就在于德宗的这种做法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真正症结。“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赵光奇认为君主在皇宫里不知民间疾苦,就在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通处在隔阂的状态中,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百姓并不归向,而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君主也并不知情,长此以往,国家倾危败亡。
这一次唐德宗听到了民间的声音,这其实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正确的做法便是:“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也就是要将管窥到的疾苦变成国家治理问题,调查有关部门为什么搁置诏书,严查那些横增赋敛、盗匿公财的官员,对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要绳之以法,甚至可以诛而杀之。但这也只是表象的治理,要抓住这个问题深入,考察制度是不是真的存在漏洞,如果有,则要“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本质问题,才能迎来真正的太平。
当然德宗并没有从这个小问题入手,甚至他听到赵光奇的诉说之后,只是免除了赵家一家的赋税和徭役,这不是“难寤”吗?“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唐德宗只是将此当做个例,而且解决的也只是暂时的困难。
【财丰欲滋】
《唐纪四十九》记载了宰相李泌的一件事。贞元四年二月,元有直将淮南的二十万钱帛运送到了长安,当时的李泌知道后将这些钱送到了大盈内库,但是德宗还是屡次传旨向地方索取财物,并告知各道不要让李泌知道,李泌知道后,“惆怅而不敢言”。
对此,司马光发表了评论,他认为,“王者以天下为家,天下之财皆其有也。”君主把天下当成自己的家,拥有天下之财,这无可厚非,但是这里的家和财均非私有之家、私有之财,“阜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民,己必豫焉。”这才是正道,而唐德宗要将财产私藏起来满足自己的志趣,这当然违背了君主之德,“夫多财者,奢欲之所自来也。”在指出唐德宗的问题之后,司马光又认为,李泌身为宰相本打算消弭德宗的欲望,所以才充实他的私人财产,这样做同样会使欲望滋生起来,就像禁止出行却打开了大门,所以,“虽德宗之多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司马光认为李泌所做的事情不符合宰相的正道,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了李泌的问题所在?贞元五年三月甲辰,李泌去世,对于李泌的评价是:“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的确,李泌在成年之后曾游历于嵩、华、终南诸山之间,慕神仙不死之术。后来辅佐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又在德宗朝参与内政、外交、军事、财政方面的筹划,对内勤修军政、调和将相,对外联结回纥、大食等国遏制吐蕃,达成了“贞元之盟”,安定了边陲,保证了贞元时期唐朝的稳定。但是司马光在曾经评论说:“泌虽诡诞好谈神仙,然其知略实有过人者。至于佐肃、代复两京,不受相位而去,代宗、顺宗之在东宫,皆赖泌得安,此其大节可重者也。”这一次却又将“好谈神仙诡诞”拿出来说事,认为是被世人所轻的污点,是不是也是司马光正道思想所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116]
思前:手·影·志(Ⅵ)
顾后:《密室》:论隐秘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