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7《历代大师》:他们都代替不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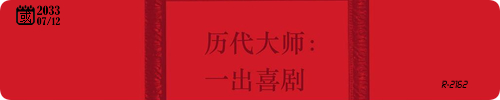
雷格尔说,阿茨巴赫尔写道,好的,我对雷格尔说,阿茨巴赫尔写道,如果这是您强烈的愿望的话,雷格尔说,是的,这是我强烈的愿望,并把第二张票给了我。
雷格尔说道,阿茨巴赫尔写道,阿茨巴赫尔写的是雷格尔所说的话,雷格尔所说的话又是对阿茨巴赫尔说的,说和写构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但是阿茨巴赫尔所写的又是第一人称的“我”:雷格尔对我说,我也对雷格尔说,第三人称对第一人称说,第一人称也对第三人称说,当“我”的故事被阿茨巴赫尔写道,这里有形成了一个关于叙述的嵌套结构:雷格尔和“我”在最内部的层级里,他们彼此都在说;阿茨巴赫尔在外部的层级里,他把和雷格尔所说的话写了下来;而所有雷格尔和“我”的话以及阿茨巴赫尔写的东西,又在更外部的层级里,记录和书写的便是作者托马斯·伯恩哈德。
在艺术史博物馆里的对话、阿茨巴赫尔记录这场对话的文本、伯恩哈德完成这个故事,形成的就是一种嵌套结构,伯恩哈德无疑站在最外层和最顶端,他的记录、创作就构成了一种观察,而关于《历代大师》的文本就是一个不断从最内部逃逸出来的观察者日记,实际上,这个最内部的文本也是一个观察日记:在艺术史博物馆里,雷格尔三十六年来保持着一个习惯,那就是除了周一之外,每隔一天就坐在博尔多内的展厅的那张天鹅绒面料套的长椅上,观察对面丁托列托的名画《白胡子男人》;我与雷格尔不同,没有三十六年来持之以恒,也没有每隔一天来这里,“来还是不来博物馆,得看我正好有没有兴趣。”只是因为昨天雷格尔让我今天来这里,于是我来到了艺术史博物馆,在博尔多内展厅里,观察着集中精力观看《白胡子男人》的雷格尔,他身穿过冬的大衣,双手撑在夹在两膝之间的手杖上,当我采取站立的姿势看雷格尔,我就是在观察他,而且,“我一点儿都不用担心会让雷格尔发现我对他的观察。”
雷格尔坐在那里全身心地观察《白胡子男人》,而我站在后面观察雷格尔,由此构成了关于观察的嵌套结构。而在波尔多内展厅里,除了雷格尔的观察、我对雷格尔的观察之外,还有博物馆展厅服务员伊尔西格勒的观察,就在这个免费开放的星期六,参观者陆陆续续来到展厅,伊尔西格勒用生硬的目光看着他不认识的每个人,这是博物馆监视员典型的“令人不悦的目光”;除了观察参观者之外,伊尔西格勒还和我一样看见了雷格尔,他对坐在《白胡子男人》对面观察的雷格尔进行了观察,于是观察形成了三重结构,“守口如瓶,这是您的强项,我对伊尔西格勒说,我想,同时我在观察雷格尔,雷格尔在观看丁托列托的《白胡子男人》,这时他又在伊尔西格勒的视线之中。”36年来持之以恒观察一幅画的观察者雷格尔,对雷格尔进行观察的我和伊尔西格勒,或者还有我对伊尔西格勒的观察,伊尔西格勒对参观者和我的观察,观察是对观察者的观察,观察是主体的行动,观察也是将自己变成了被观察的客体。
这就是伯恩哈德在这部小说中构建的特殊叙述结构,关于说的嵌套,关于观察的嵌套,一切的嵌套意义就在于在不同层面形成一个样本,但是在说和观察之中,嵌套意义又具有不同的作用。当雷格尔在说,“我”写下他说的话,这种嵌套结构已经将说转变为写,它们具有不同的文本意义,但是在雷格尔和伊尔西格勒之间,却变成了没有转变的“传声筒”,“伊尔西格勒是雷格尔的传声筒,几乎他说的一切雷格尔都已经说过了,三十多年以来伊尔西格勒说的都是雷格尔说过的话。”伊尔西格勒在说雷格尔所说的话,看起来是雷格尔通过伊尔西格勒在说话,但其实是伊尔西格勒在学雷格尔说话,这就是不经过自己头脑的传声筒意义,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雷格尔对伊尔西格勒的讽刺。伊尔西格勒出生在奥地利布尔根兰州的布鲁克,他的童年很不幸,母亲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父亲有了外遇一辈子与酒为伴,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伊尔西格勒离开了布尔根兰州来到了维也纳,当上了艺术史博物馆的展厅服务员。
一方面伊尔西格勒讨厌布尔根兰州,在他看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一辈子就被监禁在那里,“布尔根兰人是囚犯,伊尔西格勒说,他们的故乡是监牢。”而另一方面,当伊尔西格勒成为了艺术史博物馆的服务员,他就是“国家雇佣的艺术作品的守卫”,这个身份更像是监狱中的看守,“自我认识伊尔西格勒以来,尽管他并没有什么病,但脸色总是很苍白,雷格尔几十年来称他为三十五年以来供职于艺术史博物馆的国家行尸。”伊尔西格勒离开布尔根兰州就是逃离了监牢,但是他又成为了博物馆的“国家行尸”,逃离的目的是监禁其他人,这是不是一种巨大的讽刺,而雷格尔将其称为“国家行尸”,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他当成了没有主见的传声筒,“我们将一个很普通的人变成我们的传声筒,当我们把这个很普通的人变成我们的传声筒之后,我们又寻找另一个传声筒,寻找另一个适合作我们的传声筒的人,他说。”伊尔西格勒对雷格尔所说的引用形成的嵌套结构却在自行进行着反嵌套的解构,雷格尔认为他是传声筒,认为他像所有布尔根兰州的人一样,是一个“蠢货”,“我们需要一个蠢货作我们的传声筒,雷格尔说,一个布尔根兰的蠢货是十分合适的传声筒。”
所以说所形成的嵌套就是另一种观察,伯恩哈德在这部小说中,以嵌套结构的方式完成的就是对于世界、社会和人的观察,当然最核心的就是作为观察者雷格尔的观察,他通过雷格尔滔滔不绝甚至絮絮叨叨的说而展开。他认为布尔根兰州的人都是蠢货,他认为维也纳人是欧洲最脏的人,“根据认真的统计,维也纳人每周只用一回香皂,同样也已经过科学的确认,维也纳人每周只换一次内裤,最多换两次衬衫,大部分维也纳人一个月只换一次床单、被罩和枕套。”他认为奥地利是野蛮、堕落和全面混乱的国家;他三十六年来持之以恒到艺术史博物馆看《白胡子男人》,不是对这幅画进行欣赏,而是要找出艺术的不完美和不完整,“每当我把这里挂在墙上的一件所谓完美的艺术作品变成片断,我就前进了一步,我的方法是长久地在这件作品中寻找严重的缺欠,寻找导致完成这件作品的艺术家失败的关键之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以这是他的观察室,也是他思考和阅读室,对于阅读他也持同样的观点,从来没有读完一本书,而是不停的翻阅,“这样一个人宁可翻阅而不是阅读,在读一页之前他可能已经翻阅了几十或几百页了;这唯一的一页他读得比任何人都彻底,会令人难以设想地投入。”这就是雷格尔所说的片段阅读,“如果我们有幸把完整,把现成,甚至把完美变成片断,如果我们这时阅读它,那阅读对我们来说,才是高度的,或许是最高的享受。”不存在完美和完整的作品,因为完美会毁掉我们,杰作会毁灭我们,艺术作品就是片段,“不存在完美的绘画,不存在完美的书,不存在完美的音乐作品,雷格尔说,这是真理,这个真理使像我这样一生都处在绝望中的一个人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 编号:C38·2250804·2336 |
从图书的阅读到艺术作品的观察,雷格尔就是要从“历代大师”中找出问题,这是他来艺术史博物馆观察的目的,而从艺术史博物馆这个凝固的点的观察开始,他也对整个社会、艺术和历史进行了观察。他观察博物馆的参观者,在外国人中他认为意大利人天生具有艺术鉴赏能力,法国人会感到无聊,英国人对一切了如指掌,俄国人则对一切赞叹有家,波兰人带着傲慢的表情,德国人几乎不看原作只按照目录指引,而奥地利人尤其害死维也纳人,“他们只有少数人来艺术史博物馆,不算那成千个学校班级,他们每年按规定必须来艺术史博物馆参观。”说到学校组织的餐馆,雷格尔认为这样的参观对学生是毁灭性的,因为老师用狭隘的教育扼杀了学生的柔情和敏感,学生最终将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从这一点他认为奥地利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老师成为了国家的帮手,孩子则失去了自由,孩子甚至成为了从“国家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奥地利人也都是国家仆人,“国家就是这些让人害怕与恐惧的一切,就是虚伪和谎言。”所以奥地利是一个野蛮、堕落和全面混乱的国家。
国家代表着虚伪和谎言,艺术家也是虚伪和狂妄的人,那些为艺术的艺术家甚至比政治家更加虚伪,“这种艺术面向万能的上帝和所有天神,脱离我们的世界,雷格尔常说,这是艺术的卑鄙无耻。”那些历代大师画出的每一笔都是一个谎言;雷格尔说自己青年时代读过施蒂夫特的小说,但现在发现他的小说是胡诌八扯,而他则是德语文学中最无聊、最虚伪的作者,同样,安东·布鲁克纳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皇帝和上帝,天主教的狂热信仰让他对上帝的敬畏有悖常态,他的音乐和施蒂夫特的小说一样混乱和拙劣,而他们就是上奥地利州被称为天才的存在,“可怜的上奥地利州,她还以为生产出两个最伟大的天才,而实际上是两个被过分高估了的不中用的人,一个是文学方面的,另一个是音乐方面的。”雷格尔还说到了海德格尔,他认为黑的歌尔是可笑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穿灯笼裤的小市民,他把哲学当成廉价煽情的工具,是哲学上的骗婚者,“今天人们仍然没有看清海德格尔的真面目,虽然他消瘦了,但人们仍在挤海德格尔奶。”
在对文学、音乐和哲学的批评之外,雷格尔也谈到了自己的恨,他很太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阳光更让我恨的了。”他恨人,“每逢我晚上听完音乐会回到家里,我经常直至午夜一两点钟站在窗前望着下边的街道,观察那里的行人。”因为父母是一对可怕的夫妻,所以他们相互仇恨,而雷格尔当然也恨他们;他恨童年,“童年就是这个地狱,不管它是什么样,它就是地狱。”所有的恨让他喜欢把一切都变成漫画中的人物,“每当我们长时间地观看一幅画,如果它是一幅特别严肃的画,那么我们必须把它变成一幅漫画,他说,我们才能忍受,同样我们必须把父母变成漫画中的人物,把我们的顶头上司、把整个世界变成漫画,他说。”批评国家、教育和社会制度,讽刺文学、艺术和哲学,仇恨童年、父母和人,雷格尔让自己成为了逃匿者,“我一直等待最有利的时机,我利用了它,从尘世逃遁到艺术中,逃遁到音乐中。”
这是雷格尔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而观察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看见,更是一种发声的评论,“我觉得自己就是艺术家,而且是一个从事批评的艺术家,作为一个从事批评的艺术家当然同时也是富有创造性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说,是富有创造性的从事批评的艺术家。”这是雷格尔观察者的定位,但是当他观察这个世界,他也无疑就是被观察者,当他面对“历代大师”,他自己是不是也是“大师”?在这里就需要从观察者的身份突围,雷格尔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他三十六年来每隔一天就会来博物馆,很多人当然认为他是一个疯子;而在伊尔西格勒看来,雷格尔是一个有文化有智慧的人;雷格尔对文学艺术和哲学发表批评,他是一位没有公职的哲学家;而在我看来,雷格尔是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尤其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迟早有一天会让人以极不光彩的方式灭掉,我对伊尔西格勒说。”我认为雷格尔是一个能够经受住蔑视、仇恨、压制和否认的人,他思想坚定、敏锐、不容动摇。可以说,疯子、哲学家和天才的命名都是被人对他的观察,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也像一幅艺术品一样,他也是“历代大师”——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也将面临另外的“雷格尔”对他的观察和批评,甚至仇恨。
这无疑是一个循环结构,而要摆脱这一切,关键就在于雷格尔对自己的定位,当健康的妻子突然死去,那种死亡拯救了他,“没有人曾像我妻子那样健康,她—辈子都健康地生活着,而我总是生病,一辈子都是个垂死的病人,他说。”在雷格尔看来,健康者代表着将来,而病人代表着过去,但是当将来死去,过去却活着,这意味着什么?对病人的自我定义就是把自己放在“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上,曾经以为生命是一种永恒,但是当妻子毫无预料地死去,才知道生命从来不是为无限而生成的,“像我们大家一样是有限的。”这是对雷格尔身为病人的拯救,这种拯救回到了艺术史博物馆,回到了观察,回到了“历代大师”,对于雷格尔来说,却是另一个开始:对生命的感悟和体验的开始。为什么雷格尔会来这里?是因为他和妻子就是在这个展厅认识的,就是通过那幅《白胡子男人》开始对话的,“雷格尔说。丁托列托的《白胡子男人》您根本就不感兴趣?我问那女人。她答道,是的,我不感兴趣。”从不感兴趣开始,僵局被打破了,对话开始了,于是有了爱情,有了婚姻,有了在一起的日日夜夜,“我忽然娶了一位聪明的、富有的世界公民做妻子,雷格尔说,她用其智慧和财产拯救了我,在我认识这女人的那个时候,我正所谓一蹶不振,他说。”
这就是生活本身,当妻子去世,对于雷格尔来说,再次发现了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自然而然习惯了与一个人相处,几十年爱这个人,最终爱她爱得胜过一切,与她链接在了一起,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个人,的确仿佛失去了一切。”所以雷格尔的观察真正是在观察自己、观察人,“不管我们能有多少伟大人物、能够有多少历代大师作为伙伴,他们都代替不了人,雷格尔说,最终我们会被尤其是这些所谓伟大人物,被这些历代大师抛弃,我们看到,我们受到这些伟大人物和历代大师的最卑劣的讥讽,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与所有这些伟大人物和历代大师始终只存在于一种讥讽的关系中。”妻子死了,雷格尔说自己不想死想要活下去,以人的方式活下去,不追求伟大地活下去,这也许是伯恩哈德把“历代大师”看成是“一出喜剧”的原因,而雷格尔的观察通过自我观察和“我”对他的观察,形成了阿茨巴赫尔的观察,继而成为了伯恩哈德的观察,嵌套的结构其实形成了一种同一性:雷格尔最终邀请阿茨巴赫尔去城堡剧院观看《破瓮记》,他憎恨剧院和戏剧艺术;阿茨巴赫尔和他去看了,最后写道“演出糟糕透顶”;伯恩哈德一定也看了这出戏剧,一定也有了同样的感受,在人的意义上,伯恩哈德是雷格尔也是阿茨巴赫尔,“一个人也好,我们所以特别喜欢他,也是因为他的茫然,他的不完整,因为他的杂乱无章和不完美。”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