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2-06《流俗地》:“我心水清”的自由与倔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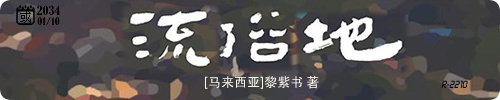
她一再梦见那些被封印在楼上楼里的女鬼,有眼无珠的,怀抱幼子的,她们在黑暗中与她相遇,夹着她并肩站在一起,像是把她也当成了鬼。
——《失踪》
梦里出现的女鬼,女鬼和她相遇,她在梦里变成了女鬼,对于盲女银霞来说,这似乎是对自我的一种异化,而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越来越世故的现实的拒绝,而当她把自己当成了她们接纳的女鬼,这一种拒绝的背后是不是将自己沉入命运的深渊?是不是以自建流俗地的方式反抗着“外部”的流俗地?
是因为她是盲女,永远无法“看见”这个世界的真面目,她必然是处在“边缘”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她可以将自己滑入和女鬼们一起的死亡深渊中,也可以在些微的光亮中往上爬上去,抓住点什么又不在边缘地带,就像那只丢失的叫普乃的猫,曾经就和她在一起,但是一周了它没有再来房间,“也可能是换了个地方,它就以为自己是另一只猫了。”滑入深渊或者越出边缘,看不见世界的银霞似乎也像把自己当成是另一只猫。另一只猫变成另一个自己,银霞或者有时候太用力了,它必须以拒绝的方式逃离困境,但是“流俗地”何尝有一个自我编织、自我幻化甚至自我清净的机会?
“‘流俗’于我,于这小说本身,并不是个贬义词。”作者黎紫书这样解读她所命名的“流俗地”,不是贬义词,它至少是一种生存的现实,而这样一种现实指向的就是“外部”:它是锡都,“多少年过去了,锡都仍然是一个老气的城市,夜里早寝,却又不完全卸装。”它是楼上楼,“楼上楼人口甚杂,一年到头不乏各种传闻和笑谈”,当然还有各种女鬼的传说,因为这就是华人选择的“自杀之地”;它是“邻里之间也都疑神疑鬼不相往来”的美丽园,是飘散着橡胶加工场恶臭的密山新村……它们构成了黎紫书的“流俗地”,在这个流俗地里,死亡就以极端的方式成为笼罩在其上的诡异阴影:怀着孩子到近打组屋跳楼的女学生,就成了大家所说的野鬼,三十年了就被困在组屋里;婵娟正在讲微积分的时候,女学生就从教学楼跳了下来,当场没有死靠着呼吸机维持了几天就撒手人寰了;还有楼上楼流传的那个“有眼无珠的女鬼”,她是开了组屋自杀先河的人,据说她总是会问遇到的人,“你有看到我的眼睛吗?我把眼珠给弄丢了”,而声称见过女鬼的人总会生一场怪病;还有大辉与纯情女学生之间的恩怨情仇,最后也无非变成了一桩跳楼事件和两个冤死的亡魂……按照大辉弟弟细辉的说法,在十年里发生了二十余宗跳楼事件,有的人竟然舍近求远,不从六十多层的光大大厦或者从跨海大桥上跳下,而是不惜做几个小时的车从北方来到锡都,选择近打组屋跳楼,“血和脑浆染在别人的地方,之后还得劳烦家人南下认领尸体。”
这里成了闻名的自杀之地,这也是流俗地的一重解释,而所谓女鬼也变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话题,婵娟在女学生跳楼之后隐忍了两个月去学校,当她的脚踩在女学生坠落的地方,就回抬头眺望教学楼的四楼,会看到学生站在那里探出了上半身,“因为背光,总看不真切是人是鬼。”而在婵娟的梦里,那个女学生总是缠着她和她讨论几何学和微积分,甚至婵娟自己在梦中认真地叫她图形和线条。当婵娟踩在坠楼的死亡地带,当她看见背光中人和鬼的影子,实际上当自杀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阴霾,它也成为了现实“流俗地”的隐喻——小说第一章节是《归来》,第一句:“大辉回来了。这种事,怪不怪呢?光天化日,一个死人,活生生出现在大街上。”大辉作为一个失踪的男人甚至警察也放弃寻找,竟然会出现在大街上,竟然完成了复活式的“归来”,当他出现在百年老庙“南天洞”停车场的时候,“彼时正午,日头高挂,像一盏大灯在严酷拷问天下苍生。”南天洞里有如七十二家房客的各路神仙,人们敬香礼拜,是让他们成为生命的守护,但是面对神仙“肩挨肩,各抱香炉,排排坐食果果”,世间的烦恼也许只能人自己去解决。
大辉作为大家认为的“死人”活生生出现在大街上,出现在神灵坐镇的南天洞,他具有的隐喻意义就是“拷问天下苍生”,而天下苍生就像是被囚禁在流俗地一般。这就是黎紫书所描绘的“外部”生活,“外部”是一连串地名:锡都、楼上楼、美丽园、密山新村、南天洞……它们像被烈日晒得发脆的胶片,一格格铺在银霞的脚边,她却只能以耳代目,把风与回声折成一张“看不见”的地图,“我知道的。我眼睛看不见,我心水清。”银霞这一句“我心水清”,却把“看不见”推到了象征的高台:当殖民统治、“五·一三”事件、金融风暴、换届大选等政治、经济巨浪轮番碾过,马来华人的历史境遇被压缩成“流俗”二字——日常、廉价、可被消费,却无处申诉。银霞的盲,恰好成为这种“被剥夺观看权”的隐喻:她无法看见别人轻易看见的光鲜,却也因此免除了被光鲜欺骗的可能;她不被允许看见,于是反过来成为“被看见”的标本——电台同事拿她当活地图,乘客拿她当传奇,老古拿她当需要被藏起来的女儿。
“锡都六百多平方公里,不是个小地方。银霞自从在电台上班,像记谱一样,把这些地名路名以及大致的方向记下来,心里熟门熟路,像画了一张锡都的地图,但她实在到过的地方却没几个。”但是,地图与身体的错位,构成银霞的第一重“困境”:她能把“外部”倒背如流,却始终无法踏入;她能精准报出每一条通往自杀之地的转角,却无法阻止一具具肉身从楼上楼坠落。于是,梦境接管了缺席的视觉——女鬼们来了,银霞经常幻想自己终有一天会碰上这女鬼,当细辉问她真碰上了,要怎么办呢?“‘她要问我有没有看见她的眼珠,我会说,大姐,我连自己的眼珠都还没找到呢!’”这一声“大姐”喊得亲昵,仿佛盲女与鬼魂之间存在着某种同病相怜的户籍:她们都是被外部剥夺视域的“有眼无珠”者,也都是被叙事划作“他者”的流俗居民。当银霞在梦里被女鬼夹道并列,“像是把她也当成了鬼”,其实是一次象征性的认领:你既然看不见,那就加入我们;你既然被现实除名,那就一起在阴册上补录。
“看不见”不再只是生理缺陷,而成了历史债务的印记——华人移民被马来本土政治、被全球化资本、被族群分化层层边缘,他们的“眼睛”在历史叙事里被挖走,于是只能以鬼形鬼状回来索账。银霞的盲,恰好成为整座族群“失明”的缩图;她与女鬼的相遇,是集体创伤在个体梦境里的回魂。然而,黎紫书并未让银霞止步于被认领,她给盲女造了一座暗室——黑暗不是空缺,而是洗相的药液,当她把外部世界推挡在眼睑之外,内部世界才开始显影。银霞的父母说她先天失明,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是看见过的。”银霞对顾老师说,“也许在刚睁开眼的几个小时,也可能是几分钟吧,我可能是看得见东西的。以后当人们对我说颜色,说形状,说线条,说光,我都觉得自己能意会,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一“前使命”式的看见,为银霞争取到一种逆向的合法性:她并非天生缺席,而是曾被赋予却又被剥夺,于是她的生命任务便是把那一瞬的“看见”从记忆里打捞出来,让其在黑暗里持续发光。
如何打捞?那就是:学习。“银霞对学习盲文和点字有着过人的意愿……伊斯迈便向院长争取,让她每天下课后到那个收藏点字机的小房间里,用一个小时练习打字。”点字机噼啪作响,像一架微型印刷机,把语言的铅字反铸成凸点,她指尖的每一次下压,都是对“看见”的重新排版,而且,“她征得家长同意……下课后与伊斯迈待在小房间里,由伊斯迈口述,再由她打字,将《古兰经》转成布莱尔盲文。”宗教经典的转译,暗示银霞的“看见”并不止于私人记忆,而是伸向公共伦理:她要让神圣的文本在自指尖流出,也要让“他者”的语言在胸口穿过。于是,黑暗被凿出一排排光的铆钉:她熟记整座锡都的街巷,用好听的声音在电台报站;她背诵乘法表,与拉祖、细辉一起把蛇棋玩成飞行棋;她甚至把迦尼萨的断牙故事也背得滚瓜烂熟:“断了的是右牙……断掉的右牙象征迦尼萨为人类做的牺牲。”右牙的缺口,成为银霞“看见”的第二重象征:牺牲带来洞见,残缺孕育智慧。
| 编号:C44·2251105·2385 |
银霞的“倔强”便在于,她拒绝把黑暗当成终点,而是把它当成磨光的凹面,越凹陷,越能聚光。但是当外部世界的暴力撕开暗室,戏剧性骤然升级——“拉祖没来得及反应,那一根‘棍棒’被高高扬起,顶梢忽然闪出寒光,他才意识到那是刀。那是刀。”为穷人打官司、把私会党头子送上法庭的拉祖,倒在自家门前;他的死亡只占华文报“极小篇幅”,仿佛一记闷棍敲在盲人院的小铁门上,声音被黑暗吞没。右牙的隐喻在此完成:正义被折断,社会缺一角,众人都成了“看不见”的同谋。紧接着,另一根“棍棒”刺入银霞的黑暗——“我十六岁时在盲人院里被人强奸了,一直不知道是谁干的。”强奸发生在“收藏点字机的小房间”隔壁,同样是学习之所,却被暴力篡位;凸点尚未成形,便被撕成伤口。“黑暗是滚烫的铅,从她的头颅灌入……让她成为一具被黑暗填充的木乃伊。”木乃伊意象极其残酷:加害者不仅夺走她的身体,还试图用黑暗替她塑形,让她永远成为暴力的标本。
然而,银霞的“倔强”再次显形,“三天以后,银霞腹中的胎儿便被拿掉了……银霞离开那房间的时候,有点像落荒而逃,心神七零八落。”落荒而逃,却也是逃出生天;她拒绝让暴力在自己体内结胎,拒绝让黑暗再生产黑暗。堕胎之后,她仍学习、仍工作、仍把锡都的街巷背得比司机还熟;她仍微笑,仍与顾老师“到婚姻注册局跑一趟,宣个誓,之后大笔一挥便就是合法夫妻”。“看不见”的是黑暗,被滚烫的铅灌入,是另一种黑暗,“银霞,我真为你高兴。真的。”细辉的祝贺像替整部小说按下快门:断牙缺口处,黑暗终结处,终于露出一丝光的齿根。
若说“断牙”是银霞与暴力的正面交锋,那么“猫”“女鬼”“丈夫”则是她迂回的自我复制——通过替身,她把黑暗一次次推出体外,又一次次认领回来。“银霞听到它的身体钻过铁花的空隙,落地时踩着什么,发出细微声响。她心里一紧……‘普乃?’她睁开眼睛。房里先是一片静寂,然后那猫说——喵呜。”最后一句是失踪的普乃的复返,像一条暗线丈量银霞的“边缘”宽度:猫可以跳窗而去,也可以破窗而入,她则借助猫的弹性,试探自己能否越出“铁丝网圈定的范围”。“银霞暗地里为她庆幸呢——既然带着一个孩子,应该不至于像别的孤魂那样寂寞而无所事事。”她把女鬼当成姊妹,甚至当成另一种“尚未被黑暗填实”的自己;与鬼比肩,是她对“边缘”的反向利用——既然世人都把黑暗当深渊,她就把深渊当阳台,把“看不见”当翅膀。“银霞要嫁人了……细辉当然知道。”顾老师是谁?小说着墨极少,只留一个剪影:教书的、有房子的、愿意陪她去注册局的,与其说他是一个具体人物,不如说他是银霞替自己挑的“导盲杖”——一根可以随时放下、却永远指向前方的棍子;婚姻是她把“内部看见”外化为“公共承认”的仪式,也是她向流俗地发出的最温柔、却最倔强的宣言:黑暗可以填充我,但不能定义我;我可以把黑暗翻译成点字,也可以把它折叠成婚纱。
|
| 黎紫书:写的是我这一辈马华人的经历 |
小说末尾,黎紫书在后记里自白:“把一群平凡不过的人放在一起,说他们最平凡的(可能也是庸俗的)人生故事。”她放弃“大历史”的俯拍,选择“低处”的平视——让银霞、细辉、婵娟、蕙兰、拉祖、马票嫂依次路过镜头,像一条被雨水泡软的胶卷,颜色褪淡却轮廓清晰。于是,戏剧性不再仰赖大起大落的情节,而藏在“平凡”的裂缝里:大辉“复活”归来,却只是让停车场上的日头“像一盏大灯在严酷拷问天下苍生”;拉祖被一刀毙命,却只在报角占两栏;银霞被强奸、堕胎,却“有点像落荒而逃”,连哭腔都收在喉咙里。这些裂缝不事张扬,却足以让历史漏光:当“宏大”被拆解成日复一日的呼吸、脚气、纸牌、猫叫,真正的戏剧性恰是“平凡”本身——它让暴力与慈悲都回到地面,让“看不见”与“看见”成为同一条河床上的两条暗流,互相渗透,互相稀释。
银霞最终没有复明,也未曾真正“看见”女鬼的眼睛,她只是在梦里、在点字机里、在猫的回声里,一次次把黑暗折成纸船,放进更大的黑暗,然后等待——不是等光来救她,而是等自己长出光的棱角。“世界悄然无声。细辉对着这一片鸦雀无声,仿佛看见面前由平地大道至远处一波一波的山峦站立着成千上万个屏息以待的群众。”那群山峦,是流俗地堆砌的集体剪影,那成千上万个屏息以待,是读者,也是书中所有“看不见”的鬼魂,银霞用她“被黑暗填充”却未被黑暗驯服的身体,替他们、也替我们,完成了一次“低处的光”的示范:她依旧看不见,却不再需要被看见,她已把黑暗嫁给光,把自己嫁给“倔强”,把“流俗地”嫁给“前使命”——银霞成为银霞,一个始终“看不见”却真正“看见”的盲女,一个被历史欠债却拒绝用债务定义自己的马来华人,一个把女鬼、猫与点字机统统收进体内,却仍能让世界在她胸口听见回声的平凡人。
而实际上,银霞也是黎紫书自我的一种印证,《后记》的标题“吾若不写,无人能写”就是银霞“倔强”式的宣言,她说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十年前的“病毒”再次回来,从最初的耳鸣到后来的眩晕,再到之后的呕吐,“几乎倒地不起”,可以说,写作《流俗地》就是黎紫书和疾病为伴、和痛苦同行的经历,“随着《流俗地》写到最后的十章八章,病发得日愈频繁,病况也越来越严重。”这就是如银霞一样身体被抛入深渊的黑暗,但是她还是完成了这部小说,对此黎紫书对“最残酷的词”——现实的阐述是:“写作长篇首先必须面对现实”:不仅仅克服身体之痛带来的不适应和百般阻扰,而且也是证明马华文学的一个考验,而这就从银霞式的先天性、身体性盲眼上升到了马华文学的历史性、地域性困境,她说,马华作家创作的条件匮乏,也缺故事、却发表园地,缺出版的机会,更眼中缺乏读者,所以自己就是像银霞一样的“边陲作者”,只有以倔强的方式完成自我命名,才能在看不见后看见,也才能让全世界都看见。
但是黎紫书的倔强从自信偏向了某种自负,她相信自己的小说比大陆和台湾的作家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灵活性,也更有可能写出“无疆界”的作品,“让整个中文世界都能欣赏,甚至在翻译后也能打动非中文读者的作品。”而这才是打破边缘人、边陲作者身份的唯一办法,“风急天高,岌岌可危,若不抱着自己可以茁壮成树的信念,何以坚持?”但是这种“偏向虎山行”自信却是建立在一种偏执和虚妄之上的,她在后记中提到大陆的长篇小说时,就认为很难看到让自己从心里佩服的作品,那些所谓的“巨著”完全是迷信于字数本身等同作品分量,以此证明作者的付出。黎紫书批评大陆很多作品东拉西扯、花言巧语、语言索然无味、流于煽情,的确是很多小说的弊病,但是将这种弊病陷于“巨著”制造的字数神话,当然是片面的,这部《流俗地》不也正是有476页、30余万字的体量?不正是长得令人生畏的“巨著”?其中难道没有东拉西扯、作者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评判作品优劣从不是字数多少,从不是厚薄如何,就像银霞残缺不残缺也都是作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的存在,甚至不要倔强,不要虚妄,“我心水清”也便可以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59]
思前:陌生花园里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