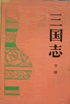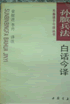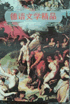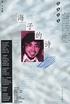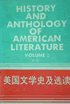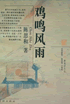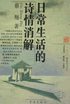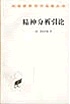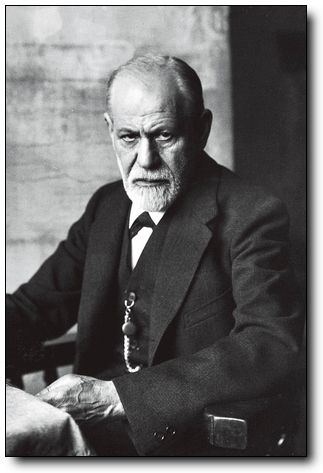|
编号:B39·1960421·0275 |
| 作者:W·考夫曼 编著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7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8.70元 | |
| 页数:353页 |
W·考夫曼在介绍存在主义时说:“ 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只是一个标签。”只不过这个标签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人性的观察角度。这其中有尼采的“权力意志”、卡夫卡的悖论、海德格尔的“战胜形而上”以及萨特的“本质先验论”。这是一种思潮,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关于欲望、原罪、恐惧、死亡,以及最本质的“存在”,但谁也没有站在纯理性的高度远离“存在”。 本书为思想家论文选集,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齐克果、尼采、里尔克、卡夫卡、雅斯培、海德格尔、萨特、卡缪的论著。
然则,如果我能要求在我的坟墓上有一个墓志铭,我唯一的希望乃是“那个个人”。
—《三、齐克果:关于他自己》
“存在主义”,一本书的名字,一个带有“主义”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标签化的产物,而面对这个标签化的书名,作为一个读者,我是应该带着一种进入的方式去阅读它,还是以一种旁观的角度在进入之后从容走出?翻过写有“”存在主义“的封面,翻过白色纸张的内页,翻过每一篇节选,翻过“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的序列,似乎在时间行走的线性轨迹里看见他们在行动,听见他们在说话,可是当最后一页被合上,我是不是只是走过了一段历史?是不是只是熟知了一个标签,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自我,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否定,他们的反叛,是不是都在“存在主义”的标签下成为一个传说?
其实,把他们编著在一起的W.考夫曼也是一个读者,把考夫曼汇编的文章的译者也是一个读者,所有的读者似乎只是在打开、合上的过程中走过了一个时间序列,即使把克尔凯郭尔译成齐克果、把海德格尔译成海德格,把雅斯贝尔斯译成雅斯培,把萨特译成沙特,把形而上学叫做形上学,也只是在语言意义上产生了陌生感,我们的编著、翻译和阅读,其实进入的只是被定义的那个叫做“存在主义”的概念,而我们,也像是用一点点的陌生产生的刺激世界里成为他们之外的“群众”,所以一种标签化的“存在主义”在标签化的我们面前,“那个个人”就像是死去时代的墓志铭,远离了一种存在的现实和真实。
当齐克果定义了作为“我”之死亡的最后命名,其实他希望的是一种个体意义本身,“那个个人”是指向别处的,仿佛和自己无关,仿佛是旁观的状态,而当死亡之后的“我”被抽离而成为“那个个人”的时候,曾经活着的生命状态就是在“他们”的世界里。考夫曼第一次翻译齐克果的《关于他自己》,是《作为一个作者,我的作品之观点》一书的组成部分,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重新回到“他的人格成分”,就是找回“作者愿意”,或者是猜度也好,或者是走近也罢,在观点属于作者本人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像齐克果一样能够从死去的“那个个人”的命名中发现“关于他自己”的意义。
齐克果是在自言自语中说出那句话的:“你必须做点什么!但由于你有限的能力不可能使事物变得更为容易,你必须以相同的人道主义者的热忱,试图把事情弄得困难一些。”自言自语是不需要听众的,在取消了旁观者的言说中,却又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可能的“你”,而这个可能的你显然是逃离现实中的我,我是一个攻击基督教的基督徒?我是一个身体畸形的人?或者我是一个哲学家、一个作者?不管是我的使命,还是我的作品,最终在齐克果那里,我要成为一个可能的你,就必须拥有一种“存在的情态”–“人们将需要困难。”就像在宴会中真正的需要是那个给食客准备了呕吐药的人,因为只有他洞悉了可能,洞悉了困难,洞悉了存在。
然而这样一个你,这样一种困难的存在,齐克果将他“匿名化”了:“忧郁如我,无可解救的忧郁如我,在灵魂的深处忍受不可言说的痛苦,绝望地与世界以及一切属于世界之物断绝关系,从最幼年即被严厉地教养,以一种预感,以为凡是真理都要忍受痛苦,要被嘲弄,要被贬抑。”匿名是因为在对面是一个群体,一个让个体成为完全不知悔改及不负责任的东西的“群体”,是把责任切成了碎片而学监了个人责任感的“群体”,是以一种虚妄的概念建立一种抽象的、虚幻的、非人格的“群体”,所以从群体中逃离出来,找到可能性的你,就是齐克果要寻找的自己,一个人,是被尊重的一个人,是成为真理的一个人,是写在墓志铭里的“那个个人”。
齐克果在畸形的世界里寻找个人的意义,而对于存在主义来说,它首先遭遇的一个问题是:人是什么?或者存在是什么?海德格命名自己的那本书叫《存在与虚无》,沙特则取了《存在与虚无》,两个“存在”或者就像这本被编著的书名一样,只是一种标签化的名字,甚至概念也说不上,但是他们却从“存在”的命名出发,开始了对人的命名。无疑,海德格的存在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考夫曼在论述中说,海德格的兴趣不在人,他的学说不是关于人类学的,他所关注的是“基本的本体论”,是研究存有的。存有是什么?“在一切时候,存在事物之所以为存在事物都是在’存有’之光中呈现的。”存有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是属于本体意义的真理,但是它要达到“无蔽”状态,那照亮的光在哪里?光照亮存有,才能让我们“见到”事物,而在这个命题里,作为存有之形式的人和““见到”存有的我们,显然是两个概念,在海德格看来,只有形上学表现为存在事物时,存有就是被光照耀,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认为,人必须表现出其存在性的意义,才能意识到这种形上学,也就是说,人必须回到自己的本质,“就他是一个人而言,人表现为那样的东西。”那样的存有,那样的人,就是在本体论上完成了形上学的命名——“们的思维活动,在适应于它的一个行动中,就显得更为纯粹,回到它所意指的东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回到那早已意指的东西。 ”
这是海德格的存在论,而在沙特的存在主义那里,存在是先于本质的,虽然在海德格看来,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仍然是沿用柏拉图以来“本质先于存在”的命题,倒置过来仍然是属于形而上学的语句,“它仍然未显出存有的真理。”但是在沙特那里,存在并不是一种本体论的存有,它其实是一种更具体意义上的人的生存,甚至当存在先于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人作为存有的一种本体的倒置–沙特的存在主义关注的人主体意义。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完全可以看成是沙特的一种妥协,而在他的早起著作中,存在主义并不是在界定一种人本主义,而是在凸显存在的荒谬性,在自由人性意义和牢笼般的社会意义之间,一直又一堵让人恐惧的墙,“我想,那时我多想钻进墙去,然后把背靠着墙……使尽全力,但是那墙壁仍屹立不动,象在恶梦中一样。”汤姆想进入墙的世界,其实是被墙隔离在无意义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死亡才是真实的,站在墙那边,然后八根枪对准自己,喊出一声“瞄准”,还有谁能逃过这死亡的劫难?这是一种战争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对于死亡的恐惧让人取消了人的意义,汤姆尿裤子,璜“我不要死,我不要死”的哭泣,都在把人变成进入死亡系统的一个目标,在这样的状态中,谁能追求幸福,谁能追求女人,谁能追求自由?甚至连谎言也变得毫无价值,我对卫兵说雷蒙躲在墓地里,一开始是骗人的话,甚至是为了逃避,但是当最后雷蒙说“我就躲到墓地里去”的时候,不是巧合的惊异,而是被预言的可怕,人完全在墙的世界里变成了无法逃避的存在。
所以面对这种荒谬性,沙特提出了“自我蒙蔽”的存在方式,“意识不但不把它的否定向外面导引,反而转向它自己。”我对自己隐藏了事物的真相,那么欺骗者和被欺骗者在双重意义中变成了不存在,“一方面是意图将隐藏之物指出,另一方面却又压抑它,伪装它。”这是一种悖论,而这种悖论在沙特看来,是为了在一种分别中实现超越,超越什么?超越蒙蔽,超越欺骗,超越悖论,超越那堵墙,在对立面中发现先于本质的存在,引用费加罗的话,就是:“证明我对就是承认我可能会错。”也就是“意识到他人其意义乃是意识自己之所不是”。存在是显示,存在也是否定,去相信就是不去相信,所以沙特对于存在的定义是:“意识这一存在物乃是由自己而存在,又由此而超越过它自己。”
超越其实是人从物的状态回到自我意义,也就是说人的存在是一种主动超越式的改变,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是一种主动的行为,但是在“反犹太者的画像”的悖论中,人的存在荒谬性却反而成为一种政治意义的态度,反犹太者选择的是恨,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激情,它的本质是一种摩尼教,就是以善和恶的原则来解释这个世界,它是对立的,所以沙特为反犹太者绘制的画像就是一种罪恶:“在我的知识之中仅有造物是完全自由而又献身于罪恶的,那就是罪恶精神,亦即撒但自身。因之,犹太人是可同化于罪恶精神的。”这种罪恶精神就是对于人类命运的惧怕,就是把个体放在一种毁灭的世界里从而消灭人的合理性。
这是人存在的荒谬性,人作为主体面对这个世界其实是无能为力的,这种无能为力在尼采那里,就是“生活在险境中”,那是由社会、政府、宗教和舆论组成的权力体系,那是一个暴政无处不在的生存世界,所以尼采借用那个在权力体系之外的疯子的口气说:“上帝在那里,我告诉你们。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全都是他的谋杀者。”上帝是最神圣和最权威的东西,上帝却让每一个人生活在险境中,所以当我们成为谋杀者,宣告上帝死了,就是消灭暴政,就是消灭权威,就是取消神圣,而当这一切都去除之后,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甚至死才能在一种意志中成为自由的死,“我的死,我向你赞颂,这是自由的死,因为我要它时,它便走向我来。”
查拉图斯特拉教人们“死得其所”,其意义却是生得其所,也就是生命意义在于一种破坏的自由,在于寻找生命意义的超人:“这一个时代,特别会重向英勇致其敬意的。因为这一时代将为一个更高的时代铺路。它将聚集这个更高时代有一天所需要的力量——这个时代是要把英雄主义带到对于知识的追求上以及为了思想及其结果而战。”但是闪烁着酒神精神的尼采,当他以一个同谋者呼吁人们杀死上帝的时候,是不是人就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上帝死了,是打破了一种神性的权威,而超人和英雄是不是另一个上帝?当否定虚伪的圣人而把自己当成一个怪物的时候,这样的存在是不是还是一种荒谬?
为什么在地下室的我,还是看见了无处不在的罪恶?甚至我自己就是一个恶人,“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我是一个不漂亮的人。”所有的否定都是以社会的那堵墙为标准的,在地下室这样一个肮脏、臭烂的地方,四面的墙就是把人推向了罪恶,“无法通过的意思就是石头墙!什么样的石头墙?当然是自然律,是自然科学的演绎,是数学。”这是反理性的态度,和尼采的破坏欲望一样,是为了要杀死统治意义的上帝,但是地下室的我显然不是采取一种杀死上帝的行动,他采取的是一种绝望之后的恶,“四十年的时间他一直记得他所受的伤害,一直到最微小的最屈辱的细节,而每一次他都自己给它加添一些更屈辱的细节,用他自己的想象恶意地取笑并折磨自己。”嘲笑自己折磨自己,仅仅是一种个体的方法,而且他说谎,他想成为那一只陷入“冷酷的,歹毒的,以及——最要紧的——永恒的恶意之中”,因为这是一种绝望的乐趣,所以我才会在地下室里喊出“为什么我不能变成一个虫豸”?
人变成一个虫豸,这是绝望的乐趣,这是罪恶的欲望,那是对于卡夫卡《变形记》的一种遥远呼应,但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虫豸论不同,卡夫卡是在寓言中否定这种异化的现实,K永远无法进入城堡,是因为在上帝死了之后,一切都变成了无意义的规则:没有上帝,也没有英雄,没有国王,也没有皇帝,连法律也变成一个空洞的词,“老伯爵确实是死了,这样,年青的一位就得继承;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在历史上有了个停顿,代理人走入了空虚之中”。意义就如那个城堡的主人Westwest伯爵一样,德文的“west”意思就是“腐烂”。
上帝死了,所有的意义在腐烂,进不了城堡的不是K,而是所有人的存在,存在却不知道存在的意义,这才是最大的荒谬。而面对这种荒谬,人的主体性是不是也被取消了?里尔克的《马尔特札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关于荒谬的样本,那就是“第三者”,上帝和人之外的第三者,它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自己,而是去掉虚伪之后真是的自己,“我们要把我们的装扮拿掉”,装扮的东西有时是上帝有关的宗教,有时是社会之内的权力,有时是四面墙的地下室,有时是谋杀了上帝的超人,而现在把一切的装扮都拿掉,就是取消了使我们进入虚妄世界的所有入口。而卡缪也在把一切的装扮拿掉,甚至把荒谬性本身也拿掉,那个推着石头上山却又一次一次被滚落的西西弗斯,终于在无意义的神话里发现了自我的命运,“他的命运属于他,他的巨石也归于他。”只有他自己,只有他推动并属于他的巨石,只有他存在并属于他的宇宙,“无意识的,秘密的呼唤,从所有的脸上发出邀请,这些都是胜利的必然的回转和必须付的代价。没有太阳就没有阴影,而且有其必要去认识夜晚。”
所以在卡缪那里,人的荒谬性不是被置身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而是把自己当成了荒谬世界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不能把阴影当成是真实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能把沉重当成是快乐的一部分?“挣扎着上山的努力已足以充实人们的心灵。人们必须想象薛西弗斯是快乐的。”其实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我永远不要有读者”,还是齐克果的“我唯一希望的是‘那个个人’”,不论是尼采的“我们全都是他的谋杀者”,还是沙特的“证明我对就是承认我可能会错”,他们都在人的主体意义上定义存在,与海德格在存在的本体意义上探寻存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存在主义”,但显然,无论是本体还是主体,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人的存在所面对的是作为客体的我们,是作为一种规则的他们,无论是上帝还是权力,无论是荒谬还是恐惧,当人被置身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体系中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否定者,一个反叛者,一个变革者,所以在“从陀斯妥也夫斯基到沙特”的历史轨迹中,考夫曼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存在主义做出的一个定义是:“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体系)的充足性,将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它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