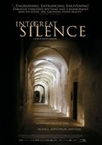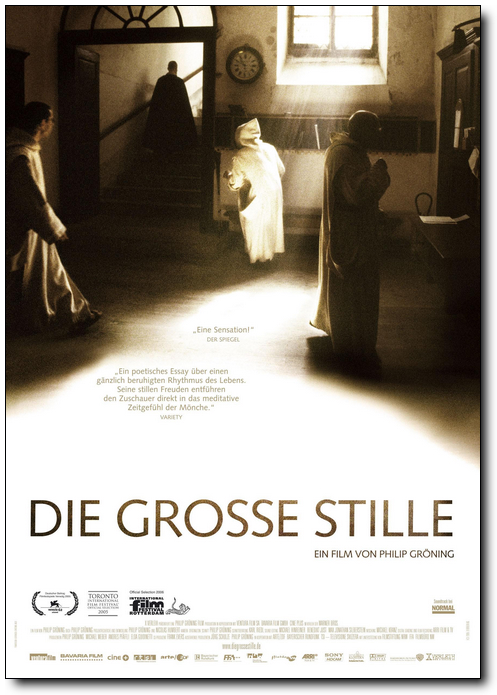2015-11-30 《大宁静》:谁听见了上帝的声音?

停留在111分钟,是被手指触动的停止,是被时间中断的分割,前面和后面,过去和未来,在一部电影里划分出一条不可见的细线,这一条细线就是现在,现在,我离开屏幕,现在,我走出房间,现在,我度过周末——细线总是在电影被中断的时间里扩大成一秒、一分、一时,以及一天,甚至变成一种断裂,而人为的断裂处,站着一个没有进入其中的我。直到几十个小时之后,当我再次启动播放键,再次观看电影,再次进入时间内部的时候,那种现在已经不可寻,不可见,不可命名。
和纪录片保持足够的距离,将一部电影分割分裂成两种时间状态,对于我来说,不是拒绝,不是逃离,而是寻找不到“遁入”的迷惘,Into Great Silence,“Into”是个动词,是进入,而在进入之前必须打开,但是在波兰语的叙述中,我完全被隔离在那扇进入的大门之外,是的,就像那只打开一条门缝的黑暗里,其实对于我来说,是看不见里面的精彩的,只有无限扩展的黑暗,只有吞没光亮的黑暗,黑暗蔓延,黑暗扩展,像时间和陌生的解说一样,用一条门缝的距离将我隔开在观者的位置上。
|
| 导演: Philip Gröning |
 |
我,当然不是主体,甚至,所有的主体都不存在,只有电影本身,只有声音本身,只有图像本身,只有时间本身,成为它们应该成为的自己。是的,在阿尔卑斯山顶的这个修道院里,时间仿佛就是静止的,就是它自己。雪飘落下来,覆盖在山上,覆盖在树林,覆盖在屋顶,覆盖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白色的屋顶和白色的山峰融为一体,当世界以这样一种方式统一起来的时候,自己的时间完全是一种虚拟状态。似乎云也停止了移动,似乎树也停止了生长,似乎人也停止了呼吸,在唯一的状态里,一就是全部,全部就是一,“I am the ONE who is.”甚至当雪花吹进窗户,吹进屋子的时候,也没有惊扰,就在那里,以极自然的方式飘落,像一粒粒的尘土,飘落,然后寂灭;而当冰雪融化的时候,时间依然是自己的时间,冰化成水,水汇成河,每一滴水都有自己滴落的声音,每一条河也有自己流淌的行动,没有阻隔,没有破坏,就这样让季节以自然的方式转变;夏天到来的时候,有雨落下,滋润大地,洗净尘世,甚至河水暴涨而化为激烈的声音;而在树木成长之后的秋天,叶子上又有了那一层的霜,不论是曾经的枝繁叶茂,还是现在的枯枝败叶,都走向它自己的状态。最后有一次下雪,有一次覆盖,有一次统一,整个世界在白色中沉睡,在白色中寂静,在白色中沉默。
|
|
| 《大宁静》海报 |
冬天而春天,春天而夏天,夏天而秋天,秋天而冬天,是时间呈现的自然序列,没有人为的影响,没有人为的打乱,而在时间的序列里,那些修道院里的僧侣也仿佛和这自然的山、自然的水,自然的雨雪一样,成为它的一部分,甚至这古老的修道院,也仿佛已经完全融入在这天地之间,山水之间。“但他们样的修士,已经这样生活了980多年了。他们就这样每天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已经延续了980多年,他们会这样继续下去的。”导演格罗宁说。980多年,对于天地来说,只是一个瞬间,对于山水来说,只是一个片段,但是在春夏秋冬,在白天黑夜这样日复一日的寂静中,完成了“遁入”。
遁入不是一个结果,是一种过程。当世界被打开的时候,这里的黎明,这里淡蓝的天,这里白色的雪,都以裸露的方式呈现出来,而那一个年轻的修士,跪在房间的一角,以虔诚的方式打开属于自己的一天。他是他们,他们是他,众多的修士完成晨起的动作,然后走出房间,走向礼拜堂,晨钟被敲响,在寂静的山间悠然而成为一种仪式的开始,修士们走向半圆形的圣水器边,然后用手指蘸一下,留下濡湿的指印,留下荡漾的水纹。然后进入那条门缝,通过黑暗的这边进入光亮的那边,然后祈祷,然后诵经,然后静默。
遁入是完全的状态,遁入是进来的虔诚。老的修士用标尺丈量,用剪刀裁剪,然后做成一条僧袍,给新来的僧侣穿上,那个黑人僧侣进入到这个世界,他穿上黑衣,再穿上白袍,他被剃掉头发,这是进入的仪式,只有在仪式之后,才开始那遁入的历程。于是,他们引导着他,他追随着他们,他和他们一样读经,一起礼拜,一起进食。遁入是融入,是抛除曾经和自己有关的一切,是从此将自己安放在应该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的门打开,是接纳,是汇聚,是一体。
一体的世界再没有外来者,尽管那山顶之处会有白色的飞机掠过,尽管他们会使用电脑,会弹奏电子琴,尽管这一区域还有游客的打扰,但是那扇门永远隔离着两个世界,这里是寂静,那里是喧哗,这里是修行,那里是俗世,但是他们的世界从来不是抵抗,从来不是对立,而是容纳,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是一种状态,所以在修道院里,他们把一切纳入到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开窗,可以看见对面的山峰,可以沐浴吹进来的风和洒落的阳光,可以感受四季的变化;他们种植果蔬,制作面包,他们自己锯木,自己劈柴;他们在漫天星空下点亮烛光,在幽暗的深处看见不灭的火。甚至,在白雪覆盖的时候,他们踩着厚厚的雪来到山腰,然后快乐地滑雪,在自然的馈赠中感受乐趣。
但是从来没有喧哗,即使有一天走在室外,他们也是讨论着经文的意义,这是他们很少发出的语言,而这些语言似乎也成为自然之声的一部分。自然之声,包容了一切,转变了一切,下雪时有雪花落地的声音,降雨时有雨滴掉落的声音,读经时有手指翻动书页的声音,集合时有轻踩楼梯的声音,厨房里有切菜的声音,以及理发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锯木的声音、水流的声音,一切都像是自然的声音,不扩张,不扰乱,不撕裂,轻柔而富有节奏,缓慢而具有韵律。也只有声音,才让人感觉到时间的走动,才让人体味季节的变化,才让人感触自然的机缘,才让人遁入一种寂静。
“Behold the silence. Allow the Lord to speak one Word in us...that HE is.”是的,寂静是上帝的声音,他让我们说,他让我们听,听见上帝的声音,也听见自己的声音。起床,祷告,礼拜,读经,劳作,休憩,这些悠缓的生活里,都有着严谨的作息与纪律,都在和上帝对话。每一个修士的小室里,除了一床一几一椅,四壁徒然中,跪凳上方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却总是虔诚的方向;而在钟声悠扬飘荡的时候,修士们弥撒中倾听上帝的语言,也和上帝对话。而每日的夜祷,他们在上帝的言说中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午夜的幽暗礼拜堂里,那匀净绵长的吟唱直抵冥想的境界,那摇曳的红烛,照亮每一个人的心灵。持续两三个钟头的夜祷,一宿又一宿,使山林更为寂静,使世界更为安静,使生命更为宁静。
只有声音,没有音乐,只有烛光,没有灯光,只有自然,没有布景,只有字幕,没有旁白。在这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导演格罗宁仿佛也是“遁入者”,为了拍摄这一部纪录片,从提出申请到最后同意,历经了十几年的等待和准备,而最后只允许一个人进入其中的时候,对于格罗宁来说,也变成了抛却一切技术主义的困境,但是既然是遁入,格罗宁似乎也在这样的状态中接近心灵的宁静,“Our entire life, the whole liturgy and everything ceremonial are symbols. If you abolish the symbols, then you tear down the walls of your own house. ... The signs are not to be questioned. We are.”灯光、音乐,或者都是俗世的符号,都是生命中的那堵墙,所以进入就是拆除那道墙,就是放弃一切,上帝说:“不放弃一切的人,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所以只有在这样一种遁入的状态中,才能听见上帝的声音,才能接近自然的世界。孑然一身用4个月时间记录那些光影,那些声音,那些时间,有用两年半的时间剪辑,最后是164分钟的寂静。而对于这个整体来说,不只是属于格罗宁一个人,它属于每一个听见的人,每一个看见的人,每一个坐下来遁入寂静的人。
可是,为什么我会在111分钟的时候关闭声音,关闭图像,关闭电脑,甚至关闭时间呢?世界打开了一条缝,是让人缓慢地进入,让人缓慢地感受,让人缓慢地聆听,可是在被世俗切割成不同时间而存在的人,那道门缝是一道断裂的缝,断裂成你和我,断裂成存在和放弃,断裂成离开和回来,而在断裂之后,时间已成为一个废弃的符号,上帝在远处说:周末是感恩节。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269]
顾后: 世界已遁入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