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30《避暑》:仿佛等候某人的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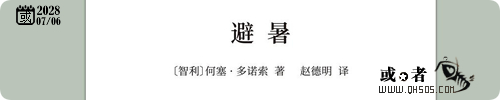
但这让我有点想笑,因为我亲眼看到她的灵柩被放入墓穴之中,后面是一堵墙,周围有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茔。
——《夫人》
夫人过世了,夫人入葬了,夫人却没有消失,“我想到还会看到夫人从我眼前走过:两眉相连,身披绿色的雨衣。”比如在某一个街角,会遇到“夫人”,或者会看见翻版的“夫人”:两眉相连,身披绿色的雨衣,从我面前经过。大约是某种想念,大约是想念之外的一些想象,总之逝去的夫人总是会出现,无法抹除,就像她还活着一样。
但这多少有点感伤,因为我知道夫人已经过世,就像那个曾经点着蜡烛的房间,低沉、安慰的话语声最后都滑向了一个不知不觉的尾声,“熄灭了我对夫人的全部思念”;而且我还参加了葬礼,跟随送葬的队伍沿着十里长街缓缓前进,人们都保持沉默,人们都为她悲痛,我也一样陷在这种悲痛里;甚至当我以为会遇见夫人或者夫人的翻版,我就觉得有点想笑,因为我亲眼看见她的灵柩被放入了墓穴之中,死亡已经被确定了,那一切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甚至是一种幻想,那堵墙隔开了生者和死者,隔开了现实和幻想,而墙周围是“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茔”。
一堵墙隔开了两个世界,夫人在别处,一模一样的坟茔也湮没了夫人的坟墓,死去而消逝,就像被成百上千座坟茔所吞没一样,再也不会有单独属于夫人的世界,连同街角的遇见,都不再可能发生。对于我来说,“夫人”何尝不是一个最后必将被吞没的意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夫人”的称谓本身就是一个无所指的符号,我没有和她有过对话,只是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看见了手拿湿雨伞、头上戴着实用帽子的女人,五十多岁,不美也不丑,不穷也不富,当然姿色也一般,只是眉毛连在一起成为她那张面孔最突出的特征。偶遇的夫人,擦肩而过的夫人,被看见的夫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夫人”慢慢扩展成为了一种生活,占据了我那时的一切,“渐渐地我有意寻找她了。如果一天没见她,就会觉得缺了点什么。”再次见到她,手拿一束合欢花的夫人脸上露出了微笑,这甚至成为了我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后来失去了线索,后来听说她去世了,后来参加了她的葬礼,后来的一切都被一堵墙隔绝了,后来的她也湮没在成百上千座坟茔里。对于逝去的一切,哀伤总是难免,但是对于我来说,“夫人”不只是某一个人,不只是某种经历,她是一种记忆,她是一种生活,她是混杂着思念与哀伤的存在——而对于何塞·多诺索来说,对“夫人”的复杂感觉也是《避暑》这本小说集的思想主线:她曾经出现,她曾经引起了思绪,她最后消逝而湮没,但是对于经历了这一切的人来说,即使生活就是由成百上千一模一样的坟茔组成,复数的世界也留着专为“夫人”这个独特的存在而保留的位置。
“献给玛尔塔·希伯尔”是《夫人》这部小说的献词,而小说集《避暑》的题辞上,何塞·多诺索写着:“献给特蕾莎·贝尔加拉:她不识字”,后面的注解是:“特雷莎曾经是我父母的女佣,是她把我带大。”无论是玛尔塔·希伯尔,还是特蕾莎·贝尔加拉,都是何塞·多诺索笔下的“夫人”,一种混杂着记忆和某些伤感的存在,一个逝去之后还留着位置的夫人。“避暑”的那段时间是闷热的,夏季属于黏黏的汗水,但是沙滩边的破房子大约是提供了“避暑”的绝好位置,保姆胡安娜回答罗莎的问题时说:“不是什么宫殿,纯粹是小孩子的傻话,是一间破房子,海边常有。”但是这个破房子对于劳尔来说,却真的是宫殿,他每天下午都会和海梅一起去沙滩,面对大海,肯定没有燥热的感觉;当然在那个夏天,他也和保姆卡门在一起,卡门吻他的前额,劳尔则搂住卡门的脖子,“她感受到他温润的嘴唇贴在她嘴上。”
| 编号:C64·2220919·1872 |
胡安娜和卡门,两个保姆对于家里太太的事总是不会去打听,当太太罗莎问起劳尔的“宫殿”,也做好了解释;劳尔对于母亲和父亲的事,也没有参与,他只是看见母亲在教堂的钟敲响十一下的时候推开了他卧室的门,进门前熄灭了香烟;再后来,劳尔问母亲,“我爸爸下来是因为海梅走了,对吗?”罗莎反问:“你怎么知道他们走了?”很多事情在发生,很多人在其中,但是在那个夏天,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或者夏天像“夫人”周围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茔一样,吞没了很多东西,比如那座宫殿,比如和卡门的吻,比如在海滩的海梅,后来在夏天剩余的时间里,劳尔坐在沙滩上,孤独一人,“他聚精会神地盯着海平线,仿佛等候某人的归来,盼望着什么事情的发生。”
劳尔变成了一个人,他的“避暑”就是在等候某人的归来,等待是因为那个位置空着,是因为那个位置只属于某人,和《夫人》一样,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茔湮没了所有,大海和沙子也吞没了所有,但是在心里那个位置却永远留着,并等候某人的归来——但是,很多人再也不会回来了。《查尔斯顿舞》里弥漫的也是对逝去时光的无限伤感,我想起了和海梅、麦莫三个人去舞厅的那个晚上,那次是三个曾经的发小在一起,都是二十三岁的他们在舞厅里听到了响起的“查尔斯顿舞”,但是三个人却在那里喝酒,“把我们三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更为重要的东西是大家对酒的嗜好。”喝酒在我看来,就是生活的一种乐趣,其他的乐趣是和朋友一块玩,或者还有那些女孩——去舞厅可以喝酒,和朋友在一起,也可以和姑娘交上朋友。但是回忆中的那个晚上并没有这些生活的乐趣,“每当我回忆他的时候,心里就感到一阵恐惧,或者厌恶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谁?一个胖子,在跳舞的时候突然就摔倒在了地上,当肥大的身躯倒在地上,我感到像是有什么东西破裂了,而在地上的他也不再是一个醉汉,“更像是一具尸体”。
查尔斯顿舞曲还在响着,男人和女人还在跳着,那个晚上的生活还在继续着,但是胖子倒地而像一具尸体,对于我来说,却是如《夫人》和《避暑》一样,有什么东西被吞没了,挥之不去,“每当从酒吧走过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仿佛世界上所有的酒都有了那个夜晚充满酒吧的那种可恶的味道。”突然发生的事,和生命有关,那时的我们只有二十三岁,都还很年轻,从胖子倒地看到了自己成为老人的那一天,“像跳查尔斯顿舞的胖子那样血压升高的时候,那时再关心自己的健康不迟。现在还不需要。”我这么想,我还要了三瓶最贵最好的葡萄酒,是把胖子发生的那一幕抹去,是把那种厌恶的感觉去除,也许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再想起被吞没的存在。但是,它却在那里,它已经发生,它还将发生,“更像一具尸体”也许真的不再为生命留着一个等待的位置,因为很多东西,离开了真的再也不会回来了。
《同名的人》里的胡安和胡安娜,在西班牙语中是同一个名字的阳性和阴性形式,当胡安在南德斯先生的商店遇到还不到十七岁的胡安娜时,就说:“我不是阿根廷人。可我最大的抱负是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您不想去吗?胡安娜。您跟我同名啊!”同名的人找到了对话的方式,后来胡安有一次摸了胡安娜的大腿,胡安娜浑身发抖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在想象中;后来胡安娜挣脱了胡安的怀抱跑回柜台,她听到了他撒尿的声音;再后来胡安告诉胡安娜自己要去安第斯当兵去了,那晚他抱住了她,她让他亲吻,他还解开了她的衬衫……同名的人在一起,胡安就是从“咱俩同名”开始接近胡安娜的,埃尔南德斯商店的老板娘罗莎告诉胡安娜“你恋爱了”,之后胡安摸了胡安娜的大腿,之后胡安亲吻了胡安娜的嘴唇,之后胡安还解开了胡安娜的衬衫,对于胡安娜来说,那的确是“恋爱”,是同名而在一起的状态。
但是,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有着美好结局的故事,胡安没有钱也没有工作,当兵也许是他唯一的出路,胡安娜这份工作是教母给她找的,那时的母亲和一个酒鬼同居了。胡安和胡安娜是同名的人,似乎也是同命运的人,“你恋爱了”又能改变什么?他还是要去安第斯当兵,他吻了她解开了衬衫,她却感到身上的剧痛,她想明天告诉罗莎她终于有了“信物”,但是这又有什么用?撒尿的声音,浑身发抖的身体,身上的疼痛,也许才是最真切的,明天不是可以向罗莎说起“信物”,而是同名的人分开了,而是恋爱就像是一场梦,而那个从此空着的位置,是不是还会有人来,是不是还需要等待?“同名”之阴与阳的形式,不是在一起的标志,而是隔阂的象征,或许安第斯山的战斗最后会出现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茔一样,吞没而让一切消逝。
但是,在《安娜·玛利亚》和《“中国”》中,何塞·多诺索却在淡淡的悲伤中带入了一些暖色。不到三岁的女孩安娜·玛利亚在栗树和胡桃树的绿叶掩映间忽隐忽现,老人的目光在寻找她,“他觉得林中的无序状态已经吞没了她,寂静中唯一的住户就是蚊虫的嗡嗡声以及流经杂草和灌木丛中间溪水的潺潺声。”但是安娜终于没有被吞没,老人给她吃的,“他让她点火热茶。然后,二人共同分享面包,偶尔有块肉,洋葱和西红柿。”老人照顾她,“安娜·玛丽亚于是冲他笑笑,如同往日美好的时光里一样,用深沉发亮的蓝眼睛望着老人。”安娜的父母遭遇了什么,自己又经历了什么,似乎一切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从无序的林中走了过来,重要的是老人从铁丝网那边抱她回来,重要的是有面包和其他事物,重要的是安娜的目光中有微笑,“她领路,牵着老人的手,说:‘走……走……。’老人跟着她走了。”
总之没有被吞没,总之留着了位置,总之等来了某人的归来。《“中国”》中的男人碰到了母亲的帽子说:“天啊,这好像在中国!”或许那只是日本商品,或许“中国”永远是一个想象的国度,或许“中国”也会消逝,“当然了,还有一个真正的中国。”那些东西和记忆都被贴上了“中国”的标签,不是真正的中国,却也成为了带着美好想象的存在,当终于有一天从国外回来的我问弟弟,“什么地方能搞到一部我特别喜欢的书”,弟弟笑着回答说:“在‘中国’……”对于弟弟的回答,“可我不懂……”中国被误读,中国在别处,中国曾被遗忘,但是那个位置却一直空着,它等待着那个中国甚至放在括号里的中国回来,它是一顶帽子,是一本童话书,是一条街,也是记忆,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它会在那里,永远在那里。
《安娜·玛利亚》和《“中国”》里是不被吞没的意象,何塞·多诺索就是在一种等待中去除了那些隐隐的伤感,那些逝去的悲痛,然而也只是微弱的光,就像三岁女孩安娜的微笑,在树叶越来越隐秘的公园里,即使现在不被吞没,慢慢长大的一天也会最终无法被找到。小说集里最触动那种无奈而悲伤情绪的是《两封信》。两封信本来对应的两个人,其实只需要来来回回的一封信,从写信人到收信人,再从收信人回信到写信人,永远是点对点的输送,他们在一条线上构筑了永不错失的“一封信”。但是一封信变成了两封信,两封信变成了没有收到的信、寄错的信、丢掉的信,以及再也不会回来的信。写信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约翰,一个是智利人海梅,两个人写信,是写给彼此的信,他们写了十年。十年来他们都写了一封信,但是十年之后,约翰离开了开普敦,之后穿越南非大草原和原始森林,最后定居在肯尼亚。肯尼亚种植园主约翰写了一封给智利律师海梅的信,这时距离他们共同学习已经过去了十年。
信里约翰说起了自己的种植园,说起了妻子和孩子,说起了果树,没有什么大事。但是这封信没有送到海梅的手里,它投错了邮局,寄给了古巴圣地亚哥和海梅同名的人,打开信他才发现不是写给他的,本来他想把信再寄给律师海梅,但是他因为其他事情忘了这件事,于是信丢到了杂物中,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信丢了,后来约翰也丢了,“若干年后,约翰、他妻子和几个子女被毛毛族杀害了,住宅和粮食被付之一炬,大火照亮了非洲明亮的夜空。”而律师海梅呢,在约翰写给他信的同时,他也给约翰写信了,信中他说起了自己的生活,“我那时庆幸自己活在智利,活在这个笼子里,远离那人类悲惨的经历。我天天看报,详细了解情况,关心战斗的轰鸣声。可是就连战争也没有打动我。为什么呀?也许你知道答案。”但是海梅想想并没有将信寄出,他撕掉后本来想重新写一封短信,但是他还是没有写。
一封信投错了地方最后被丢了,另一封信撕掉之后没有重写,一封信会变成回信,最后还是一封信,而两封信再也无法送到收信人那里,它们真的成了无关的两封信。十年之后是另一个十年,约翰已经被人杀死了,海梅也像是忘记了这个最好的朋友,他只是在读报纸的时候会偶尔看到肯尼亚,偶尔想起约翰,他不知道那个叫约翰的朋友已经死了,就像“夫人”一样,周围都是成百上千座一模一样的坟茔,位置空着,却永远不会有人归来,“又过去了若干年,两三年,或者三四年,海梅再也没想起约翰。他不知道很久以前非洲风暴早就把约翰的骨灰吹散到世界各处的天空中去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