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3 风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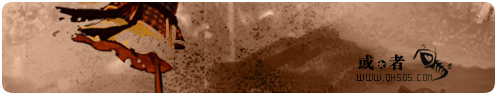
大家就这样,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着日常生活,有人反思,有人不反思;一切似乎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连一切都处于危险时的极端情况下,大家也继续这样生活,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歌德《亲和力》
日常生活之外,一定是听到了什么。成都之行,以及之后的九寨沟、黄龙之行,我都是带着一种离开日常生活的方式进入其中,山和水,文化和历史,以及虚构和传说,把自己放在一个纯粹出行的位置上,多少带着一点逃奔的态度。但是从来都是要回来,从来都是要继续日常生活,也从来都是要按部就班地把自己放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
即使飞机之上,也还是避免听到风声,隔着玻璃看见云朵,看见阳光,看见另一架飞机,却从来不看见风。我在天上,仅仅在某一高度里遗忘风声。但是飞机下降,走出机场,车行驶在回家的高速公路上,风似乎也没有进入到日常生活。120码以内的速度,也是按部就班,我以为那是安全、封闭和自由,但其实在向前的速度里,我是与风保持一种逆行的方式,逆行而成为阻力,但是当窗户还是被关闭的时候,我依然无法把握风的力度和方向,甚至,行驶的汽车是在制造一种风,但是那种风也无法进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只是吹到脸上给人以凉爽的空调风。
回家,便是结束一种出行,便是开始日常生活。但是在听到那风声之前,明明是先看见了什么。本来是想继续开始某一种锻炼方式,像没有离开之前进入某一块塑胶场地,在夕阳的照耀下,在热风的吹拂下,甚至在用速度制造的逆风中,完成身体的形而下定义。但是那一张告示明明写在那里,大门左侧,底面蓝色,文字变成一种拒绝,和那扇紧闭的大门一起组成了回来世界的全部命令。是的,离开之前和离开之后,仿佛就是两个世界,仿佛经历了巨大的蜕变,仿佛上演了复杂的剧情,而我只不过像所有以为回到日常生活的人一样,其实早已经被拒绝在看到的世界之外。
“实际上见不到人影——当然,我算一个,然而我几乎不在现场。”不在现场的封闭主义,连风都带着那么一点隔绝的味道,但是世界应开始开放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的现场。转身、左转、直行、然后右转,离开那个看见命令的地方,走向陌生却有风声的地方。是一条只有细微流动的溪流,是一条被陌生的人行走的道路,甚至是一座坐于其上等待风来的廊桥,它们是流动的,他们是运动的,反思或者不反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回到原先的状态,可以让身体行动起来,可以在耳边听到进入夜晚之前凉爽的风。
自西向东,4公里,跨越七座横卧在溪流之上的桥,穿过逆行的人群,超越同行的每一个人,然后再自东向西,依然是4公里,依然是跨越七座横卧在溪流之上的桥,依然是穿过逆行的人群,依然是超越同行的每一个人——相反的过程,相反的方向,以及听到相反的风,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制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中心,而当这个中心变成自我的一部分,其实所有的人群,所有的环境,以及所有的风,都变成了一种虚设的背景,甚至嘈杂和多变,也都成为身体的一部分。
是有风吹拂过来的,水的流动带来空气的流动,空气的流动带来风的生成,但是风是没有方向的,甚至是盲目的,当吹在身上的时候,分明感觉不到凉意和柔软,而汗水湿透的衣服其实密不透风,它像一个封闭的大门,拒绝了所有可能的进入者——“风硬起来,我们从下坡又慢慢走回来”,而最终风成为一个敌人,竖立在前面,阻挡我完成夜晚之前的身体动作,阻挡我改变日常生活的努力,而在看不到任何出口的情况下,世界的结局只有一个:“没有避风港。到处是危险。”
从危险的黄昏进入危险的夜晚,从危险的大门进入危险的大堤,从危险的日常生活进入危险的自我中心,风在背上,是一颗无声的子弹,它呼啸而来,进入身体,进入日常生活,于是耳朵里都是危险的毒,开始侵蚀听觉,开始改变生活,开始制造恐怖。始终找不到另一个出口,即使逃离那没有方向的风统治的世界,耳边依然传来命令的子弹,让身体和思想无处可躲。
就这样了,危险而极端的风是无法从夜晚抹去的,耳朵也无法关闭每一扇大门,听说和看到,以及亲历的,都是有关风的传说,风声日紧,我只带着受伤的身体,站在那里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那个成语,就像身体,被截去了一半,终于成为一个残缺的词语——只说到了“风声”,它便被咽下了肚子,在残缺的身体里成为一个死去的意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890]
思前: 《德国姐妹们》:她们都有一个孩子
顾后: 《天涯沦落女》:没有目的的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