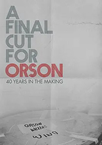2024-08-23《献给奥逊的最终剪辑:40年制作历程》:完成的“未完成”

依然是一个关于“完成”和“未完成”的辩证论题:当100小时的电影素材变成120分钟的“成片”,当40多年前奥逊·威尔斯的意愿得以实现,当普通大众能够完整地欣赏《风的另一边》这部电影,它的确已经完成了,但不管是电影时长上对完整的界定,还是剧情结构对完成的注解,或者是威尔斯的意愿在“停,很好”中被实现,其实都是一部电影在物理状态中的完成,而当一个第一无二的创作者早就先于电影本身离去,无论如何这样的完成都是一种“未完成”。
Ryan Suffern的这部纪录片只有短短38分钟,作为记录,它只是还原了《风的另一边》从素材变成电影的过程:2007年4月,保存威尔斯这部生平最后一部电影的仓库被打开,这是电影完成的新起点,从这个起点回溯的是1971年在亚利桑那州凯尔福利拍片的场景,回忆者是弗兰克·马修,当时的他和威尔斯在片场拍片,“大家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之后是在电影中扮演汉纳福特助理奥特雷克的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的回忆,“他很难相处,但是你必须爱他。”正是在拍片时,威尔斯对彼得说:“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完成这部电影。”当时的彼得不解,但是隐约感觉到了什么,而威尔斯讲出这句话,也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某种预判,果然,威尔斯只是剪成了40分钟的片段,之后由于电影投资方面出现的问题,电影并没有完成,由于投资方伊朗公司陷于政治问题,这部电影的素材被封存,1985年随着威尔斯的去世,电影成为了一部未完成的遗作。
2007年的重新发现,在更大意义上是彼得和马修想要完成30多年前威尔斯的意愿,于是,重新被发现的电影便走上了“完成”的历程中,纪录片详细记录了电影制作的全过程:2017年3月17日,LTC电影资料馆巴黎实验室破产,素材被移出了仓库,最后运抵了洛杉矶;3月16日,制作正式开始,他们找到了拍摄的清单,然后进行匹配,剪辑师莫干和福托克将不同尺寸的胶片进行了数字标记,经过粘合、缝接、扫描之后,将胶卷数字化;3月27日,日落高尔工作室里,从克罗地亚运来的85个工作底片被开箱,和此前的底片进行了配对;根据威尔斯生前完成的40分钟片段,确定电影的叙事风格,然后以他的风格为锚点,进行余下片段的剪辑;通过彼得的录音,完成电影开场的叙述;在加州影城,通过算法匹配每一帧的兴趣点,人工要八九个月完成的工作计算机用了两天半完成;2018年2月,在旧金山完成了部分特效,尤其是射杀假人的部分,重新加入到电影中;之后找到了米歇尔,对电影进行配乐,当年3月分别在比利时马尔梅迪和巴黎完成配乐;在缺失了0.63厘米的磁带后,重新进行了拟音,丹尼尔·休斯顿为已经逝去了父亲约翰·休斯顿配音,约翰·休斯顿在电影中饰演的就是导演汉纳福特;2018年4月30日,在派拉蒙工作室播放了已经初步完成的电影,在场的弗兰克·马修非常激动,“我完成了导演的意愿,这让我再次拥有了美好回忆。”而彼得则说:“威尔斯很久以前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将永远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最后大家的共同希望就是让这部大师的最后影像能够得到公映。
| 导演: Ryan Suffern |
从2017年打开影片素材保存的仓库,到2018年4月完成电影的制作,这部跨越40年的电影终于在2018年8月31日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与观众见面,而同年的11月2日在美国公映。历时40年,威尔斯的意愿得以最终实现,它以完成的方式对“未完成”的遗憾说再见。但是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部成型的电影就是威尔斯想要的电影?它带有多少威尔斯的“理想型”成份?其实当威尔斯去世,电影就永远是一部无法完成的作品,在2018年被制作完成之后,电影的导演栏中只有“奥逊·威尔斯”一个人,这是对他的尊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来说,这其实是带来了一个问题:那些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加入的威尔斯之外东西,是不是在主观上认为和威尔斯保持了一致?或者说,这依然只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一种体现?
其实,在制作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属于制作者的“原创”,比如电影开头的设计,大家对这个问题普遍存疑,威尔斯的笔记中也没有说明最后的成品该有怎样的开头,最后大家决定以彼得的旁白开始,从他讲述的汉纳福特的死亡开始,这是不是一种创造?比如米歇尔的配乐,完全在威尔斯考虑之外,当米歇尔设计了前卫音乐,是不是也是威尔斯之外的创作?这些问题也许误解,但是一定是在威尔斯之外的制作,如果配乐和拟音等部分,只属于技术上的处理,那么电影开头一定是一个体现创作的过程——谁知道威尔斯是不是同意让奥特雷克通过讲述一场车祸让这个故事登场?
让未完成的电影成为一部成品,这是对威尔斯这位大师的尊重,更是让他的天才之作得以存在的需要,但是完成永远是一种“未完成”,而未完成的状态也许更代表着一种可能性,或者在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样的完成也是无数“未完成”中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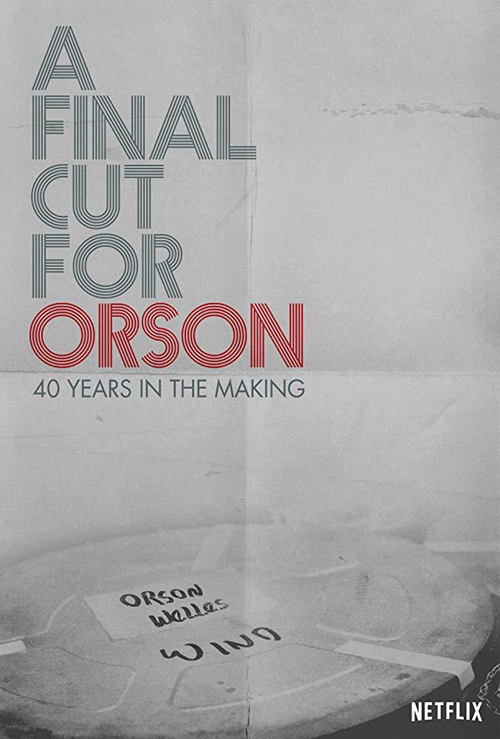
《献给奥逊的最终剪辑:40年制作历程》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