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23《游牧主体》:让女性一直“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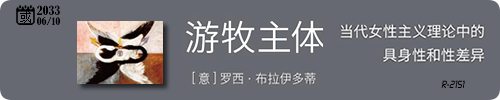
也许第三个千年,将找到自己20世纪60年代时的愿景,让想象力夺权。
——《背景和年代》
从意大利到澳大利亚,再到法国、荷兰,地理空间的不断变化构成了罗西·布拉伊多蒂作为女性主义者的一种生活轨迹;作为一个有性别的、终有一死的物种,在多重经历中也拥有了多种语言、多重区位和归属,这更让布拉伊多蒂成为了一种多元存在,或者可以将这一切的“背景和年代”都看作是她对“游牧主体”的一种实践,但是布拉伊多蒂“自豪并理应自豪”的不是时间所产生的结果本身,她把自己命名为“在过程中的女人”,是在成为“游牧主体”中引入了行动并展开了行动,“在过程中的女人”就是“在行动中的女人”,而游牧主体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恰恰就是在具身性和性差异中构建一种主体性伦理。
当然,地理空间的变化、多种语言和多重区位的拥有,只是“游牧”的一种表象,她所表述的“背景和年代”为女性主义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亲身经历了1968年的重大事件,“1968”完全超出了时间概念而具有一种“基本政治神话”的意义,在布拉伊多蒂看来,1968的事件确立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本体论,规范了从性和亲缘制度到宗教和话语实践各个领域的社会互动事件,政治本体论带来的就是对主体性的强调,“1968年一代对主体性的强调,作为解释欧洲历史近期事件道德和政治走向崩溃的一种方式变得更发人深省,更具道德紧迫性。”在女性主义上,它从“个人即政治”的理论“位置政治”发展为一种多重“位置视角”,这种视角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一脉相承:即完成了“自身去认同化”,这既是一种危险,因为它意味着失去了以往思考和宝贵习惯,但是这种追求变革政治的困难和痛苦,也给女性主义创造了条件:1968重新定义女性主义,不再将自己视作波伏娃口中的“第二性”,而是渴望于其他社会实践对其的赋权,以实现“生成-女性”的目标。
经历了1968重大事件,布拉伊多蒂的“背景和年代”为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赋权找到了合理性,她就是沿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这一“过程”,就是在启发和改变中参与“行动”,从而构建“后1968年代”的游牧主体:“这是—个质的飞跃,它开拓了积极的生成轨迹,因而可以用一种生产性的方式应对焦虑和不确定性,并协商向可持续的未来转变。”在她看来,这种向未来的转变甚至预示着人类第三个千年将实现1968年代的愿景:“让想象力夺权”——构建“游牧主体”为什么是一种“夺权”行为?从赋权到夺权,布拉伊多蒂口中的“想象力”到底是什么?
“我认为这本书算得上是我的哲学宣言,它深得我心。”在2024年的《中文版序言》中,布拉伊多蒂直接指出了这本书对于她来说的重要意义,游牧主体当然不是仅仅地理空间上的游历,并不仅仅将1968变成自己的背景和年代,也并不仅仅在过程中成为行动的女人,“游牧主体”就是通过游牧思想构建主体性存在,首先,游牧思想是由流动性和复杂性所定义的,它所抵制的是“一”的逻辑和单一身份的神圣化,它反对的是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它批判的是量化的商品化、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和对威权主义价值观的崇拜,所以不仅仅是流动性,游牧主义代表的是异质的多样性、差异性、唯物主义和交叉性,并进而构建一种生成的主体性,“游牧思想表达了在全球流动性、地缘政治位置、交叉的阶级与性别关系、种族和年龄段、共同的谱系和历史的框架内,对构建我们主体性的多重生成生态的认识。”但是在对“一”和中心主义的消除中,技术互联的全球化时代是不是意味着在没有挑战系统的基础权力结构时,“一”将会被重新确立?
所以布拉伊多蒂提出了“想象力夺权”的想法,她将这种想象力的力量命名为“造型”,“它作为对推理理性工具的一种补充,目的是深入阐述并充分表达与主流观念不协调的当代主体性模式。”游牧主体哲学不仅仅是批判的,也是创造的,不仅仅要有归属,更要有差异,不仅仅要持有异议,更要维持批判性的公民身份,既要深度思考,又要理解时代问题,布拉伊多蒂将这种想象力理解为肯定的力量,这就是“具身性”的游牧主体,它的核心就是欲望,而欲望作为本体论价值与“生存意志”相联系,也就是说,布拉伊多蒂将游牧主体看成是由生存意志或潜能这样一种肯定性的本体论欲望所驱使的伦理学,“我将主体性重新定义为具身的和嵌入的——我也称之为肉体物质性——这成为游牧主义认识论项目的第一步。”这种具身性不是生物决定论中的身体理论,而是让身体成为主体的化身,在多重共存层面与他者形成关系的汇交点,“作为哲学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共同构建充满希望的社会视野。”
| 编号:B89·2250705·2323 |
在本书的“前言”中,布拉伊多蒂更加深入地阐释了“造型”概念,造型不是隐喻的思维方式,而是对“嵌入和具身的社会位置”进行唯物主义绘图,从而对当下政治知情进行解读,“游牧者的造型作为一个动态和变化的实体,在一个非同一且多层次的视野中呈现出了主体的形象。”这就是布拉伊多蒂的“绘图学”,它以理论为基础,运用批判性思维为分析和注释工具,对当下政治、伦理进行解读,“绘制多重归属和权力关系的地图有助于识别潜在的地点和抵抗策略。”所以每一个造型都将变成一张鲜活的地图,从而构建游牧主体。那么什么是布拉伊多蒂的“绘图学”中的理论?无疑“游牧主义”就来自于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的理论,布拉伊多蒂吸取了这一理论中的概念人物、逃逸线、块茎等观点;福柯的权力理论构成了布拉伊多蒂的绘图计划,尤其是福柯提出权力的生产性意义,俄日布拉伊多蒂的“赋权”找到了肯定性力量;游牧主体的生存意志是对斯宾诺莎政治理论的发展,所以主体的生命是具身性的核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女性主义的不同观点,她引入了女性主义的“位置政治”,以此说明主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是女人,是女性主义者,是女同性恋,甚至是男同性恋,更重要的是,布拉伊多蒂把主体看成是一种“成为”的存在,在单一主体衰落和传统主体观解体之后,游牧民就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是移民、流民、难民,是旅行者、流动劳工、非法移民、侨民,是邮购新娘、外国护工、联合国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也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这些不再存在的国家的公民。
在布拉伊多蒂看来,游牧主体是当代主体性最合适的理论“造型”,她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化就是:“我扎根,但我在流动。”在女性主义主体性意义上,布拉伊多蒂提出的是两个视角,一个是具身性,一个则是性差异,它们如何构建“游牧主体”?具身性中的身体具有唯物主义的基础,也是生命主义的体现,它超越了阶级、种族、性别、年龄,就是人类既有扎根又有流动的能力,它是情动、欲望和想象的转化者,是与他人互动的情动场所,“换句话说,女性主义者对具身性的强调,与对本质主义的彻底拒绝是紧密相关的。”对本质主义的拒绝,在某种意义上所体现的就是差异理论,而性差异是游牧主体对人本主义主体观的一种批判,按照女性主义者伊利格瑞的观点,女性主义就是一个“将女性的女性主义主体”进行再现的过程,只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死亡中才能打开女性主体性表达的个可能——她把这种女性主义主体命名为“女性性”,一方面,性差异理论坚持主体起源的“非一性”,即每个主体内部的非一性,由此形成了女人之间的多元性和多重差异,另一方面,差异理论也是旨在将“大他者中的小他者”带入再现的政治过程过程,女性主义者作为中介者而存在,它实现了新女性的人性和神性的再现。
|
| 布拉伊多蒂:造型是一张鲜活的地图 |
而在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性差异理论更是成为了“自我反身性”的分析模式,“它的目的是表达对话语中的权力的批判,同时肯定女性的女性主义主体的另类视角。”它重构思想与生活、思想与哲学的关系,以超越女性特殊结构为更开放的可能,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的性差异不再是一个生物范畴,也不单纯是社会学范畴,而是“身体、象征和社会之间的一个重叠点”——从“她-自我”变成“她-她者”,“通过这种飞跃,一个在政治上强制的集体主体,即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我们女人’,可以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赋予主体性生成的力量。”所以对于布拉伊多蒂来说,游牧主体不是超越性别,而是承认差异,甚至把巩固差异作为一项计划,“我的女性主义游牧主义计划的出发点是,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是对主体虚假普遍性的批判性对抗运动,而且是对女性渴望制定主体性不同形式的积极肯定。”它既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是女人当中的差异,也是每一个女人内部的差异,她提出了“小写复数女人”就成为作为性差异的女性女性主义主体,而这也是游牧主体“生成-女人”的需要。
但是在社会状况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当具身性的塑造面对规训和控制技术,性差异下的女性主义如何成为“游牧主体”?这里出现了新生殖技术下的“无身体的器官”,它是去物质化的身体,是可互换的器官,它形成的是绝对的平等,按照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说法,“一个子宫就是一个子宫就是一个子宫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女性主义如何体现生命和权力,如何生成-女人?和“无身体的器官”对应的则是“无想象力的图像”,视觉政体走向了想象力的缺乏,可见的一切在可视化中让图像自己活得了生命,“无想象力图像的肆意流通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但是在布拉伊多蒂看来,这也为女性主义的主体介入创造了条件,“它需要我们努力发挥知识创造力,并进行深刻的批判。”无身体的器官在这种主体介入中形成了具身性的器官,而无想象力的图像也在批判中渴求着想象力的图像,这或者才是差别理论对于主体构建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在《母亲、怪物和机器》一章中,布拉伊多蒂从“怪物”的案例分析,认为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畸形学,而畸形学所具有的差异性不正是女性主义的一种面向,“怪物他者既是阈限的,又在我们对标准人类主体性的认知中,处于结构性的中心地位。”它是在控制身体的权力内爆后所形成的机会,那就是建立新的联系和协商,重新划定女性身份——这就是“生成-女人”的理论。
游牧主体的思想无疑和德勒兹有关,但是布拉伊多蒂却在分析了德勒兹的生成论后认为,他所设想的“生成-女性”是一种普遍性存在而没有考虑它的特殊性,“一个差异的理论却没能考虑到性差异问题,这让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批评者感到怀疑和困惑。”德勒兹的差异反而是将两性置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中,布拉伊多蒂称之为一种矛盾,“性差异打开了通往重新定义思想普遍结构的道路,而并不仅仅是女性特有的结构。”这也许是布拉伊多蒂站在一个女性的立场对差异问题的解读,更具意义的是,她没有像很多女性主义者那样,把男性赶出女性主义,把女性主义的空间变成自足而封闭的,而是探讨了“女性主义中的男人”。一方面,女性主义所反对和拒斥的就是父权制话语,这也是她们受害或历史压迫的原因所在,所以女性主义并不能从历史的现实条件中分离,也不可能以拒绝的态度让男人消失,而另一方面,男性依旧在生成女性化的行动中扮演着驱逐者的角色,布拉伊多蒂甚至数落了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勒兹这些男性思想家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不过是旧形而上学食人主义的当代版:它表达了男性渴望延续他们所固有的霸权传统,它揭示了他们不顾一切地依附他们传统的发声位置。”
所以女性主义世界里要有男人,也必须有男人,还是引用伊利格瑞的话,“为了生成,人需要有一个性别或一个本质(必然是性化的)作为视域。”男人是作为生成-女人的需要而存在的,只有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生成才能实现一个人可能成为的全部,才能形成真正的游牧主体,“女性主义者在我心里是一个斗土、一个赢家、一个(再)复仇者、一个活动家、一个社会人物。”这就是女人之“在”,“她是政治改革派:想要让女性一直‘在’。”男人在女性主义中构建了差异性,女人一直“在”则在具身性中不断行动,并成为真正“在过程中的女人”。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