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3《仪容之三》:传承还是最后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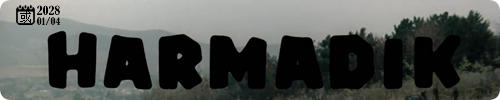
黑屏,字幕被打出,是1965年的Lefkovics Erno和Roth Bernath,是1978年的Louy Tamas 和Deutsch Laszlo,是1986年的Raj Tomas、Gerendai Endre和更多孩子的名字,时间和人名组成了“仪容三部曲”最后的“仪容”,但是“Lefkovics Erno”这个名字上,画上了一个方框,这是逝者的标记,仿佛和这个日渐倾圮甚至最后湮没的犹太教堂一样,在时间的行走中只剩下了最后一面墙,生命流逝,仪容易老,纪录仍在。
从1965年到1978年,再到1986年,教堂的“仪容”经历了什么?从曾经的倾圮,到后来的废弃,再到1986年的湮没,22年呈现了一种动态的死亡:墓碑还在,铭文还在,甚至遗址还在,但是已经杂草丛生,曾经还可以从门那里走进来,曾经还保留了约柜,曾经还有遮风挡雨的墙,而现在,没有了门,没有了约柜,只有最后一面墙还矗立在那里,仿佛用最后的倔强记录着最后的死亡。22年似乎一切都在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对于教堂的“仪容”则是一种遗忘:远处的火车驶过,再也不是曾经的蒸汽火车,再也不能激起某种和历史有关的记忆,它只是在行走,红色的机头如此鲜艳,奔驰的速度如此快速,这是时代前进的一种象征。
| 导演: 米克洛什·扬索 |
在火车的疾驰中,教堂的遗址还留在了原地,甚至加速了它的覆灭。但是,米克洛什·杨索用22年的时间记录了“仪容三部曲”,情感一定是复杂的,就像教堂,是不是一下子就走向而来倒塌甚至死亡的命运?人的出现,是杨索标记时间的一种做法:1965年的时候,走进来的是两个老者,他们让教堂发出了诵经的声音;1978年的时候,光临的是两个年轻人,他们一样举行了仪式;而1986年的时候,是更为年轻的孩子。他们在杂草丛生的石碑前,仔细查看碑上的文字,甚至还用手去触摸;他们来到只有一面墙的教堂,在石碑前点上拉蜡烛;他们还和大人一起在旁边的破屋中举行了仪式,那个孩子还念念有词主持着仪式,而其他的孩子跟着他一起诵经,然后是切面包,然后是吃圣餐。
孩子们到来,孩子们注目,孩子们诵经,孩子们参加仪式,这是1986年的独特风景。从1965年的老者到1978年的年轻人,再到1986年的孩子,不同年龄的人走进来,像是对时间流逝的某种逆反——时间向前,教堂在变老,但是来这里的人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活力。对于时间的逆反,就是一种传承的象征:蜡烛被点起,经文被诵读,仪式被保留,声音也在响起,似乎这里并没有死去,甚至它有着恢复的可能。但是,传承或者是表象,孩子们的目光中除了好奇什么也没有,孩子的行动中除了机械也不再有什么,他们甚至还不停地看着杨索的镜头——仿佛这是配合纪录片拍摄而再现的演出。
从老者到孩子,不变的就是改变,和石碑中的杂草一样,和疾驰的火车一样,和只剩一面墙的孤独一样,在被改变的现实里,一切都不可阻挡,即使孩子们来了,以群体的方式来了,以仪式的方式来了,但是他们终归要离开。落日的光线照在最后一个窗口,接着便是下移,便是消失,便是黑暗,就像这座教堂,最后只剩下历经22年的仪容——那个像是老师的男人,走过最后一面墙,然后低头,然后鞠躬,然后离去,他用最后的仪式完成了对于仪容的书写。时间改变了一切,有时候某种传承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遗忘,一种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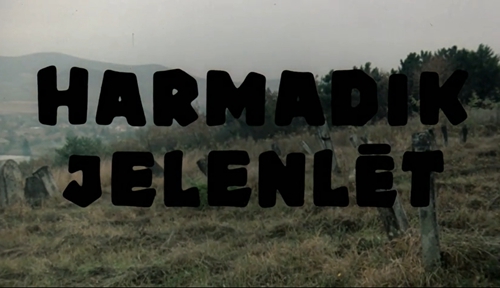
《仪容之三》电影片头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4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