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07 我梦见我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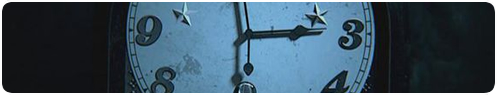
“我梦见我醒了。这是最古老的梦了,而我刚刚做了这个梦。”引语,第一人称被放在引号里,独自一人做梦,独自一人醒来,独自一人说话。以为是安全的,因为封闭的引号里独自一人,只有第一人称的“我”。单独的我,一定是在复数之外,而我之外的不是“我们”,是“他们”——照样被放在引号里,却是另一个语境,他们不在梦里,不在醒来的梦里,不在凌晨三点醒来的梦里,不在我一个人在凌晨三点醒来的梦里。他们就在对面,蜂拥地站在对面,密集地坐在对面。
他们说G,我却说B,他们说B,我却说Y,两种相异的引号,其实是隔开了两个用字符隐喻的世界,所以个体之于集体,单数之于复数,以及第一人称之于第三人称,必然会有那种疏离感,那种隔阂感,以及那种不被同流而产生的空洞感。还好,当夜晚弥漫开来的时候,当黑暗笼罩起来的时候,其实所有人都在分裂却一体的世界里梦见自己醒来。但是,当没有了暴露的细节和个体的体验,”我梦见我醒了“的背景其实是模糊的,是我只是梦见我醒来?还是我在醒来的时候梦见自己醒了?或者是我在梦中梦见自己醒了?是还在梦中,还是已经醒了?是醒来作为梦中的一部分,还是梦境作为醒来的一个结果?
梦和醒,就如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单数和复数一样,分割在不同的引号里,所以它们是对立而矛盾的,但是这种对立和矛盾你根本看不出来,它们在一体的句子里被反复说起,最终成为了小说的一部分,被锁进那本《10½章世界史》里。最后一章,最后一句,最后的我,最后的梦,那本书就放在我左侧的桌子上,在没有“他们”打扰和影响的时候,那本书被夹在各种学习资料、会议文件、活动方案之中,叠起来的纸张已经放得很高了,它远远超过了10½章,所以它们看起来像是竖立在那里,和桌子保持着垂直的距离。
而其实,这个夜晚也是垂直的。凌晨三点,时间呈现出一种垂直的状态,“死了的两姊妹:时针和分针/僵冷的臂膀,画着最后的V”,一句诗就定义了许多“黑十字架的夜晚”,僵冷的臂膀就在那里,本来应该按照规律一分一分地走动,一时一时地爬行,但是到了凌晨三点的时候,却在僵冷的臂膀伸出的时候,停滞在那里,并且永恒地成为垂直的时间。凌晨三点,灯光和黑暗是垂直的,走廊和楼梯是垂直的,桌子和地面是垂直的,当然,桌子和纸张也是垂直的。
垂直的距离最短,垂直却只有唯一的一个点。所以当我在凌晨三点中躺在那张用来户外休息的床上的时候,我和世界,也就只有唯一一个点保持着联系,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需要一个点的支撑,然后被放大,被扩散,到最后整个身体都躺了下去,变成了和桌子平行、却和纸张垂直的状态。时间已经启动,睡眠已经启动,梦境已经启动,可是我却还醒着,醒在凌晨三点之前,醒在两姐妹的手臂僵冷之前。时间会向前推过去,再向前,直到看到“他们”蜂拥地站在我的面前,看到“他们”密集地坐在我面前,甚至,直到我变成他们的一部分,和他们一起说起G,说起B,说起Y,和他们在被定义好了的引号里。
是的,和他们在一起,全部都是不说话的寂静,甚至拆掉了所有安全的引号,因为他们本身就会成为安全世界的一部分,没有风吹来,没有风改变方向,世界是统一的,所以那时候的寂静就是一种不被打破的梦:“寂静好像麻风病,寂静好像共产主义,寂静也像一面有待填满的洁白屏幕。”梦里只有寂静,没有议论,没有批评,没有否定,没有怀疑,没有在醒来的时候梦见自己醒了,也没有者在梦中梦见自己醒了。寂静的夜晚甚至没有一声电话的铃响,就在走廊的一侧,就在窗户的半面,它保持着等待的姿势,等待着有人传递声音、指令,等待着有人在凌晨三点之前说一声:“喂,你好。”
寂静是凌晨三点之前的永恒状态,而凌晨三点之后呢?那垂直的时间,那10½章的书本,那僵冷的手臂,其实是被翻过去了一页,我是在醒来的时候坐起来,然后开门,然后站立,后面的那一条走廊里没有电话,也没有寂静。距离我不远的地方是一棵树,距离树不远的地方是一盏灯,距离灯不远的地方是一只猫,有风吹来树叶在摆动,有光亮起打破了黑暗,当然有一只猫的存在,让我的手臂不至于无声无息的僵冷下来。但是,一棵树、一盏灯、一只猫,以及一个我,都是唯一的单数,都在逃离了四面封闭而寂静的世界,所以那时候,他们是不存在的,符号是不存在的,误解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也许一切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发生的。幻觉。”就像一个梦,却是真实的梦,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树叶重新恢复了绿色,灯光熄灭在自己的范围里,而那只猫舔了舔自己的脸,走向更广阔的那条路。凌晨三点已经过去,垂直的状态已经过去,他们已经过去,引号也不再重复,我梦见我醒了,我梦见我们醒了,那时我听到一个节气开启的声音:“悲秋将岁晚,繁露已成霜。遍渚芦先白,沾篱菊自黄……”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