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07《印度之歌》:他他他,和她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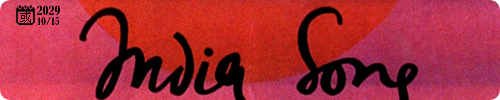
在场的是原野,是原野之上的天空,是天空里的落日:空无一人的原野,慢慢暗下去的天空,以及还呈现为红彤彤的太阳,它们构筑了一幅极美的画面。但是太阳慢慢在降落,随着太阳的下沉,天空也越来越暗,最后完全隐没。4分15秒的长镜头开场,在表现自然风光动态变化的画面里,在场的除了原野、天空和落日,还有讲述的女声:“她是个乞丐,她不是印度人,她是从缅甸,从沙湾拿吉来的,因为她在那儿出生……13个孩子都死了,她丢弃了他们,把他们卖了,忘了,来到了孟加拉湾,她17岁就有了生育,之后就不再生了,她被赶出了家门……”讲述之后传来女乞丐唱出的沙湾拿吉歌声,嘹亮,空灵,与落日一起构筑了辽远的意境。
在场的是原野、天空和落日,是讲述者的声音,是女乞丐的歌声,当然也有女乞丐的故事,但是,当这一切在场,也意味着更多的不在场:不在场的女乞丐,不在场的人生,不在场的遭遇。在场和不在场构成了一种叙事的断裂,它通过声音和画面两个维度形成了分离。而声画分离正是玛格丽特·杜拉斯进行的一场叙事革命:和其他的电影一样,玛格丽特将声音系统和画面系统各自独立开来,声音在讲述,声音在对话,声音在议论,但是谁在说、说时的状态和表情如何,从来没有在画面中得到体现,而画面中的人物在行走,在跳舞,在镜子里,在对望中,都不发出一点声音,他们是沉默的,他们是无语的。说和不说完全分离开来,声音在画面中缺席,画面也在声音中缺席,但是和声画分离的极端例子《恒河女》相比,玛格丽特·杜拉斯还是将声音和画面被一条逻辑线串联起来,声音讲述的是和画面相关的故事,画面也表现了声音的相关叙事。
声音叙述了安娜的红自行车,画面中那辆车就靠在网球场的围栏外;声音讲述了和安娜相关的三个男人:她嫁给了法国大使馆的大使,她是大使夫人,她有一个叫米歇尔的英国情人,法国驻拉舍尔的副领事爱上了她,女乞丐被她收留——除了女乞丐只是以歌声为借代“出场”之外,其他和安娜有关的三个男人均有画面上的呈现:他们和他一起躺在地毯上,裸露着身体,或者一起走出去,在大门外守望着,或者在竖立着一面大镜子的房间里跳舞;除此之外还有一起跳舞的青年随从,这名奥地利来的随从还不适应这里的环境。甚至在安娜和他们跳舞的时候,画外音完全变成了安娜和其他男人的对话,他说:“那就回巴黎吧。”她说:“我不回去。”她问:“漫长的雨季你会干什么?厌烦吗?”他说:“是的,但是可以寄给她一些书。”安娜说:“在印度什么也干不成,既不容易也不困难,既不受罪也不享福,一切都无所谓。”
当画面中副领事走了进来,站在安娜的身后,青年随从的声音:“他一直在看你。”后来安娜慢慢走出了画面,副领事却最近了大镜子,然后站在镜子面前,安娜又走进了画面之中,她经过了副领事,也照着镜子,副领事则走近了她,两个人一起跳舞,画外音是安娜和副领事的对话:她说:“我爱米歇尔,在爱情中我没有自由。”副领事的声音:“可我同样爱你,你就在我体内,我将和我一起向麻风病人开枪,我也想和你单独在一起……”但是安娜在画面中慢慢松开了手,然后离开他走了出去,接着副领事慢慢退出了画面,画外音中的“你”也变成了“她”,而且开始了大声喊叫:“今晚我要和她在一起,只要一次,我要留在这儿,留在法国大使馆,这辈子除了她我再没有爱过其他人……”然后在空镜头里,传来的是派对上客人的议论声,传来的是副领事歇斯底里的喊声,传来的是画外音对副领事故事的讲述:“他被他们带走了……”即使在画面中安娜再次出现,副领事的故事还在被讲述:“后来他去了戴尔塔岛,辞去了职务之后就失踪了……”在讲述中还不时传来副领事的叫喊。
| 导演: 玛格丽特·杜拉斯 |
从一开始两个女声以对话的方式讲述安娜的故事,到后来安娜的声音、男人的声音交替讲述故事,甚至变成了对话,声音和画面之间建立了关系,如果说画面是一种展现,那么声音则是叙述,但是声画依旧是分离的。声画之间这种形式意义的分离,玛格丽特·杜拉斯显然建立了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当声音为主体时,画面就是声音的补充,就是声音表现的对象,而当画面为主体时,声音就变成了画面的补充,就成为了画面表现的对象,或者说,画面外的声音会指向一个画面系统,画面系统就是一个封闭的存在,同样,当画面需要声音来补充的时候,画面也不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封闭却不知足,这是声画分离带来的一种“结构主义”,而实际上,玛格丽特·杜拉斯用这样的形式也在表现关于《印度之歌》的主题。
安娜是叙事中最核心的一个点,由她向外辐射,是三个甚至四个有关的男人,丈夫、情人、追求者和青年随从,他们构成了安娜多维度的关系;而未出场的女乞丐却在沙湾拿吉的歌声中和安娜形成了一种映射,也完成了对安娜命运的一种注解。女乞丐是从缅甸来到印度的,而安娜是从法国来到加尔各答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从欧洲来到温热潮湿的印度,这一种远离对于她来说,也是对于殖民主义而和女性主义生活的一次具体书写;女乞丐从17岁开始生育,生下的十三个孩子也都死了,她成为了流浪者,而安娜18岁成为大使馆夫人之后,也受到了冷落,大使斯特雷泰尔将她带到了亚洲各国长达17年之久,这17年和女乞丐的17岁形成了一种呼应,18岁这个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年纪也在这种非故乡流离生活中耗损殆尽,对于安娜来说,她再也回不到欧洲回不到巴黎,意大利的记忆也变得虚幻,而在爱情中,她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的自由——这是一种几乎是窒息的感觉,就像加尔各答漫长的雨季,所以她才会说出:“在印度什么也干不成,既不容易也不困难,既不受罪也不享福,一切都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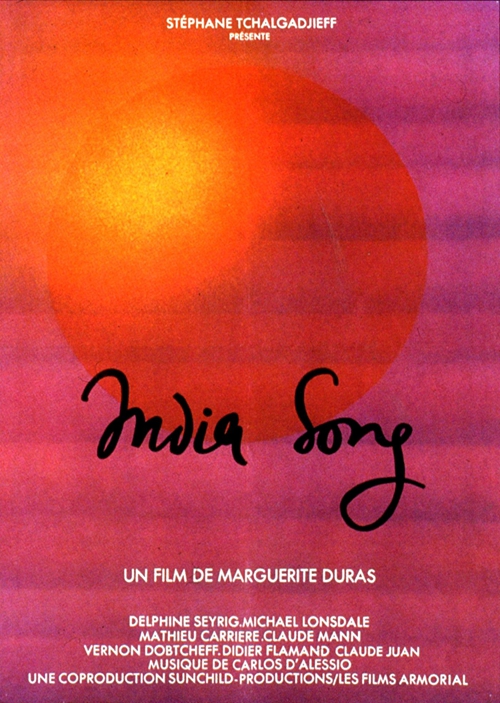
《印度之歌》电影海报
在她死后,她墓碑上刻着的姓不是丈夫的“斯特雷泰尔”,而是母姓的“卡尔蒂”,这是一种对婚姻的绝望。除了丈夫,在她生命中出现的另一个男人是副领事,这个总是神经质的男人渴望她的爱情,他曾经像沙里马尔花园的麻风病人开枪,“这里的麻风病人像沙子一样多。”也向狗开枪,当然他把枪也射向了自己,当安娜拒绝了他之后,他在派对上歇斯底里,副领事的疯癫是殖民文化的一个代表,他无法适应印度的观念,他无法融入印度的生活,最后他的精神崩溃了,射向麻风病人然后射向狗和自己,说明在这里他也生活在病态中、生活在如狗一样的世界中。当然,副领事的疯癫和病态对于安娜来说,也形成了一种外来的威胁,也变成了对于欲望的异化。而情人米歇尔呢?从一场舞会认识,安娜渴望的是自由的爱情,但是当丈夫在自己去尼泊尔狩猎时将她送到了戴尔塔岛,米歇尔和随从也一起上了岛,但是岛上的生活一样不是一种解脱,在威尔士亲王旅馆里,安娜想起了威尼斯,说起岛上的雾是紫色的,听说了世界各地蔓延的战火,“他们想尝试一起死去……”但是按照恒河边男女的约定,只有一方死去才会有彼此的自由,于是在米歇尔和随从从岛上返回驻地的时候,安娜最后选择了投海自杀,“沙滩上留着她的睡袍……”
“我爱你,直到什么也看不见,直到什么也听不见。”死亡是对于爱的一种表达,死亡也是对于自由的一次实践,这就是一首死亡之歌,也是一首“印度之歌”,钢琴上放着的曲谱就是《印度之歌》,“《印度之歌》是关于爱的歌曲。”但是在死亡的覆灭里,爱一样和高声唱起沙湾拿吉歌曲的女乞丐一样,是不在场的,印度,加尔各答,戴尔塔岛,它们构筑了一个他者的在场,这里是沉闷,是潮湿,是压抑,是湿漉漉,是半梦半醒,更是疯癫,是疏离,是迷失,在一个找不到自己、找不到爱情、找不到自由的他者之地上,一切都是不在场的,最后他他他和她她的故事在浓郁的夜色中,在无人的长椅上,在声画分离的叙事中结束,所有人都像那一个游走在印度地图上的点,永远找不到最后的目的地,除了死亡。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