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9-07《漫无目的的爱》:第一行总会保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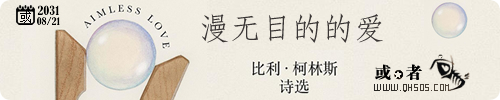
最后一节很简单,就像这首诗
以这样一个意象来结束:
——《巴黎的一月》
冒号,一定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但是它却是结束的“最后一节”:美丽的孤儿、揉乱的床,大眼紧闭,头上方的画,画中的山谷,山谷里的牛群。这些意象属于诗的最后一节,属于“冒号”后展示的东西,当然它属于保罗·瓦莱里的诗歌,或者属于保罗·瓦莱里描绘的巴黎,但是当最后一节的意象以如此富有诗意的方式呈现,它当然不是一种结束,就像那个意象中的孤儿,在被遗弃之后,大眼紧闭之中,却能看见那个如梦中的美丽世界。
美丽世界,当然不是一种结束,它是对于“遗弃”的颠覆,“诗从来没有被完成过——只是被遗弃了。”瓦莱里曾经这样说,巴黎的那些乞丐和扫大街的人,以及“衣不遮体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漫游”的人,和瓦莱里所说的诗歌一样“被遗弃了”,连同他在巴黎写的诗歌一样。但是当诗歌以最后一行或两行的绚丽颠覆被遗弃的命运,是不是一种“结束”的开始?是不是奔向完成?它是由一个叫比利·柯林斯的人完成:我看到了大街上的那些乞丐和衣不遮体的人,看到他们从燃着的垃圾桶旁散开,看见那些消失在阴影里“瘦弱而残缺的幽灵”,但是我也相信一首诗的完成就在于诗人的重新出场,他会让美丽的孤儿看见那幅画,如此,从瓦莱里到柯林斯,诗歌便在着交替中走向了完成:“我在一旁靠窗而坐/黎明时分吸着烟卷,吞云吐雾。”
结束而未结束,未完成而完成,这就是柯林斯传达的诗歌的意义:当诗歌遭遇被遗弃的命运,它需要有人“靠窗而坐”书写新的意象——这大概也是柯林斯写诗的目的所在。但是这首《巴黎的一月》在瓦莱里和我之间构建的关系,更像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另一个作者之前不正是要成为不被遗弃的读者?诗集题辞般的那首《读者》独立在那里,柯林斯把读者叫做观望者、注视者、翻阅者,或者也称之为“一目十行者”、“舔了手指翻书的人”、“认真研读的人”,也包括每天读纸质书才过瘾的你,包括嚼笔头的人、做笔记的人、用勾和叉做边注的人,还有初到者、重访者、浏览者,甚至包括飙车的人、英语专业生、准备起飞的女孩、满脸忧郁的男孩、隐性伴侣、小偷、初次约会者、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柯林斯把这些人都看成是读者,形形色色,各行各业,总之和一本书有关,和一本诗集有关。除此之外,柯林斯还想象从林荫树下推着婴儿车或牵着一条狗走过的人,想象有着“无法想象的号码”的人,在地图某个角落的人,甚至坐在火车站的长凳上,“还是昏昏欲睡,书正向地板滑落。”
那么多人都是读者,和诗集有关的人,诗人想象的人,无疑,柯林斯在《读者》中构建了一个群体,当最后一节出现一个意象,“读者”也并非是走向了他的结束,一本书在读者的昏昏欲睡中向着地板滑落,或者正像瓦莱里诗歌中美丽的孤儿一样,在大眼紧闭中看见了如梦中般美丽的世界。“读者”是多样的,读者让诗歌不断“完成”,那么诗歌如何呈现一种多样性?《漫无目的的爱》是柯林斯的第二本自选集,收录了从以前出版的四本诗集中遴选出来的90首诗歌,和英语系教授、幽默感的诗人、由中年进入老年的男人、爱尔兰裔、过着安稳舒适的中产阶级文化人的多样身份一样,诗集中的诗歌以多样性呈现给读者,比如《九匹马》的这一辑就体现了戏剧性,《诗歌的困扰》一辑和诗歌有关,《子弹飞行研究》和阅读有关,《死者的星象》和死亡有关——但这些并非是每一辑唯一的主题,柯林斯的诗集背后本身就藏着不同的读者,他们甚至构成了诗集的主体。
| 编号:S55·2240611·2135 |
《九匹马》中体现的戏剧性,就像柯林斯在用诗歌写不同的小说,有人物有情节有冲突。《乡下》中的那只老鼠沿着冷水管道蹑手蹑脚爬行,然后在墙纸背后用尖针一样的牙齿咬住了一根木火柴,在拐了一个弯后蓝色火柴头就在粗糙的房梁上划过,于是火苗突然腾起,老鼠成为了点火者和火炬手,成为了“小小的褐色巫师”,从而找照亮了某个远古的黑夜,而这只被抛到了时代前列的老鼠,和同伴们一样还闪着充满惊奇的袖珍表情,面对着突然出现的一瞬。柯林斯用诗歌构筑了一种叙事,让乡下老鼠点燃了火柴,照亮了黑夜,充满戏剧性的故事背后其实是一种关于“乡下”的情感,“他们一度都安居在/乡下那栋曾经属于你的房子里?”这乡下不正是你的乡下?或者也像诗歌一样,被遗弃在远古的黑夜中,是老鼠将其所有的记忆点亮,它是完成叙事诗的诗人。柯林斯在老鼠的戏剧性演绎中发现了故事背后的故事,那首《漫无目的的爱》所表达的不正是这种戏剧性背后的爱?爱是什么?柯林斯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我对爱的对象的多样性构筑,发现爱的本质:我早上湖边散步时爱上的是一只鹪鹩,之后会爱上被猫丢在餐桌下面的老鼠,还迷上了缝纫女,迷上了一晚高汤,“爱板栗/爱卷檐的软呢帽,一只手握着方向盘。”甚至当老鼠死了,我将它送到树林的落叶里,回来站在浴室的洗脸池旁,我也爱上了那块香皂,“当我感到它在我打湿的手里滑动/同时还闻到薰衣草和石头的淡香。”
漫无目的的爱,是随处可见的爱,也是自由自在的爱,“不需要补偿,也不需要礼物,/没有刻薄的言辞,没有怀疑,/也没有电话上的沉默。”或者这种爱“没有等待,没有烦躁,也没有怨恨”,正因为它就是爱本身,所以它是满无目的的爱,是随处随时可以爱上的爱,而这种对物保持着的热情和敏感,也正是柯林斯对诗歌的爱:似乎什么物都可以入诗,似乎什么境遇都能激发诗意,而这是不是就是让诗从日常中走出来而不被遗弃?比如在笔记本里画下速度线,让速度充满我们的生活,如此简单而又如此富有激情,“我们必须不断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一切事物”;比如在美国乐雅的打字机里感受“乐雅贵族”的状态,不是像孤单的猴子那样打出哈姆雷特的开头,而是在夜晚的寂静中发现声音的美好,“只有我打字的声音/和天上的几颗星星/唱着它们还是婴儿时母亲就在唱的歌。”比如对生活的态度,每天太阳升起总会有冲动“想拿着一把锤子/去敲碎客厅茶几上/放着的那个玻璃镇纸,//把里面的居民/从大雪压顶的小屋释放出来”,让他们手拉着手然后看见外面蓝白相间的穹顶,这不是遥远的梦想,这就是生活本身,“那么,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就像妻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九匹马”一样,它是沉重的,悲哀的,古怪的,甚至是我们种种过错的可能,但是,这不正是日常生活的写照?在把我们系在每个日子身上的时候,“当它奔驰而去,马蹄迸出火花踏进夜幕。”
在《九匹马》诗集中,柯林斯写到了像一个故事的《爱》,火车车厢上的男孩张望着,他在等待女孩的出现;女孩拿着黑色大箱子走进车厢,箱子里是一架大提琴;他在爱面前手足无措,但是他却感受着她的快乐,她如此单纯,却是完美地存在着——而种种发生的一切都在我的观察之下,“我看到那男孩抬眼望着她/目睹她的一举一动/就像画里的圣徒那样睁着双眼”,这目光中有爱,诗人就是发现、捕捉这种爱,“当他们抬头看着上帝/看他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件表明他就是上帝的事。”像读到了一篇情节简单却感情真挚的短篇小说;柯林斯也写到了死亡,这不是悲痛的、沉郁的感情,它在《临界点》中成为了对于时间“小小的移动”的触动,美国爵士乐手艾力克·杜尔斐三十六岁去世,广播上播报的时候,死亡已经发生了三十六年,三十六年前去世,三十六年后纪念,“从杜尔斐出生至今
|
| 比利·柯林斯:我们忙于无所事事 |
已经过了两个人生”,这就是时间的一种对称关系,它给柯林斯的灵感是:“我们都在时间上/冋前整整迈出了杜尔斐一步,/又掀开了新的杜尔斐一章?”继而更微妙的感觉是:穿过了人生正中心的那一刻,就像在黑夜中乘船越过赤道线的时候——是不是穿过本初子午线更具象征意义?但不管如何,在时间组成的人生序列中,生与死被具象化,这就是所谓的“临界点”,它甚至抹平了死亡的印记,成为时间的一次“小小的移动”。而对于死亡,柯林斯还有另一首更直接的诗《讣告栏》,报纸上的《讣告栏》里都登载着死亡的消息,它和年龄、死因、生平和轶闻有关,对于每个人来说死亡都是公平的,“但终有一天你也许会加入/这样一个群”,死亡也无非是一种日常,甚至渡船的诺亚也只是一个“留着络腮胡,眉头紧皱,警觉地站在每个船头”的普通人。
爱发生在日常,死就是日常的一部分,而文学呢?《文学人生》中柯林斯写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康文垂·帕特摩,他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但是柯林斯却在早上醒来时想到了这个名字,却不知道他是谁,“谁是康文垂·帕特摩?”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忘记康文垂·帕特摩,但是和一个诗人的名字无关的生活却正变成“文学生活”,“然后在厨房里站了一阵,/巡视着银色的烤面包机,碗里的柠檬,/还有那只白猫,它的神情/就像是刚刚写完了自己的传记。”《诗歌》更是将“诗歌”变成了生活本身的自传,生活就是抱怨烟草的价格,就是传递滴着汤水的长柄勺,就是给笼子里的鸟唱歌,就是“忙于无所事事”——“忙于无所事事”像一个悖论,而文学和日常的组合在吊诡中却抵达了真实,“我们为此需要的只是一个午后,/蓝天下的一条小船,//也许还有人在石桥上钓鱼,/或者,干脆,桥上什么人都没有。”
关于爱、关于死、关于诗,柯林斯其实为之后的各辑诗歌做好了铺垫,在一切都成为日常一部分的时候,后面的三辑诗歌其实是对于主题的铺陈:《诗歌的困扰》就和“诗歌”有关,和诗人有关,但是诗人何为?诗歌何谓?《星期一》中的确有一个诗人,他总是在窗前,这是一个诗人的标配,看着窗外的鸟和树,寻找中国诗人和美国诗人对月亮的吟咏,或者“看到供鸟儿洗澡的小水盆开裂了,树枝被风吹落”。当诗人站在窗前寻找诗歌的灵感时,职员们在他们的桌前,矿工们在他们的井下,编辑们在做着校对,厨师们在切芹菜和土豆,钓鱼的人在船上颠簸,架线工爬上电线杆,理发师在镜子和椅子前等待……每个人都在生活,而他们难道不是诗人?回到窗前的诗人,其实什么灵感都没有,当诗人穿上外套推开门意味着他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意味着诗歌在生活中打开了门,而所谓的诗还关在门里,还在一面墙上,“我说的是一堵冷冰冰的碎石砌的墙,/中世纪的十四行诗描写的那堵墙,/女人独有的那颗石头般的心,/卡在她写诗的恋人喉咙里的那块石头。”同样,《漫长的一天》里的诗人准备些一首“夜曲”的诗,在想起字母表的那些字母后,在浴缸里苦思冥想中,诗人的生活恰恰是:“于是转身/伸手去取离得很远的浴巾。”
《诗歌的困扰》就是对诗歌的提出的问题,诗歌总是激发人们去写更多的诗,诗歌能让人快乐和忧伤,诗歌让诗人充满写诗的冲动,甚至有“破门闯进别人的诗歌”的冲动——诗人有时候像小偷,像扒手,像盗贼,就在诗人漫步在海滩上思考关于“诗歌的困扰”的时候,“这个意象我直接从/劳伦斯·费林盖蒂那里偷来”,它真的成为了“诗歌的困扰”,但是回到记忆之中,诗歌也存在于旧金山“那位爱骑自行车的诗人”身上,他有一本游乐场的小书,之后就进入了我的口袋,“一直在我高中校服的侧兜里/陪我在遍地欺诈的学校楼道间走来走去。”偷来的小书,偷来的意象,一切像没什么改变,而想写更多的诗、让人快乐和忧伤、成为小偷、扒手或盗贼,不正是所经历的日常,不正是不被忘记的记忆?诗歌的困扰是日常的困扰,那么诗歌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当然也是诗歌。
诗歌就是日常生活,所以阅读也变成了和诗歌一样,对于日常的不遗弃:柯林斯在《寻找》中读到了那本巴塞罗那专著里“患了白化症的大猩猩”,和历史有关?和变异有关?就像不断燃烧的苍白火焰,“你才是为什么/我一直点灯读到深夜/来回翻动那些书页,上下把你寻找。”柯林斯在诗人菲利普·拉金的诗歌里读《四个月亮的地球》,“但想想海滨上的那两个情侣吧,/他伸出胳膊抱着她裸露的肩膀,/格外激动今夜他们能亲密如此/而他和她各自望着不同的月亮。”在《第一晚》中读到了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死亡,“至于死亡,最糟糕的肯定是第一晚。”当然在瓦莱里的诗歌中读到被遗弃的时代……阅读的意义并不在他人的文本里,当目光打开,就像飞行的子弹,于是阅读变成了《子弹飞行研究》——柯林斯用动态的、戏剧化的手法描写了一颗子弹穿击一本诗集的过程:子弹以每秒两千八百尺的速度,穿过了诗人“讲述他可怜的童年的那些诗”,穿过了“那些哀叹世界是如此糟糕的诗”,然后再穿过作者的照片,“穿过他的络腮胡,圆形的眼镜,/还有他喜欢戴的特有的诗人帽子。”穿过是一次阅读,更是对这个“我不太感冒的某人”的诗集的处决,当那些可怜童年的诗歌和悲观主义的诗歌被子弹击穿,柯林斯是不是写在表达诗人的使命问题?
对于死亡也一样,《死者的星象》所描写的死亡并非是沉重的、哀痛的,压抑的,《坟墓》中面对父母的坟墓,诗人竟然在寻找“静寂”,耳朵贴着柔软的草,然后翻过身贴上另一只耳朵,实际上死亡本身就构筑了静寂,“夜半客船的静寂,/莲花的静寂,/那是静寂的古寺晨钟的近亲/只不过更深沉柔和,像花瓣,在它最远的边际。”对每个人来说,“终有一死”,死亡意味着“不再有奋斗目标,不再有罗曼史,/不再有钱、孩子、工作或重要的任务”,但是在“死者的星象”中,死亡并非是无,而是另一种有,“不是朝南或朝北飞行/向是从大地垂直升起/穿过黄道十二宫的巨大圆圈。”而在柯林斯的《墓地骑车行》中,和死者有关的墓地变成了一次经过,那么多死者的名字,那么多的墓碑,它们的背后都有故事,而骑车的诗人经过墓地,就像去见陌生朋友一般,“真想用我的放物筐带上你们大家/在这个明媚的四月天去兜风”,听自行车的铃声,看乌鸦飞过蓝天,或者“两个车轮的辐条映着让人眼花的阳光”闪过,仅此而已,死亡就是另一种存在。
在对爱、死和诗进行戏剧化处理、日常化书写和幽默的消解之后,在“新诗”中柯林斯更是在诗歌形式上探索更多可能,《在一群刚刚抵达的旅客里找一位友人:十四行诗》中,柯林斯将“不是约翰·威伦”重复了十三遍,最后第十四行就变成了“约翰·威伦”,整首十四行诗就是喊了友人名字的行动之诗,十三遍的“不是”最后抵达了寻找的终点;《十九行诗》更是关于诗歌写作的“十九行诗”,“第一行总会保持不变,/但中间那几行可以消失,/而第三行,就像第一行,得反复出现。”保持不变的第一行和反复出现的第三行,是诗歌写作的规则,但是在规则之外其它则变成了对规则的消解,“但诗人又怎么可能真的别开生面/或者像浪漫船夫那样唱得兴致淋漓/如果第一行总是不变/而第三行一定要做最后的发言?”《葬礼之后》所写的是修饰词和名词之间的契合关系,朋友想要喝“是酒水的酒水”,于是来到了“称得上是酒吧的酒吧”,回忆了刚才参加的“是葬礼的葬礼”,还说起了“真称得上是朋友的朋友”,酒吧里还有“是调酒师的调酒师”,最后在午后的斜照里,看酒水晶莹如琥珀,“很恭敬地发出称得上是叮当的叮当一声。”《转折词小议》中柯林斯将此外、其次、再者、如前所述、尽管如此、然而、无论如何、其结果、不管怎样、随后、最后、综上所述、举例来说、总而言之这些转折词看做是写诗的禁忌,但是当这一首诗完成,禁忌词在诗中却又构成了非禁忌的存在,甚至在这种悖论式的表达中具有了更强烈的戏剧张力。
柯林斯的诗幽默、灵动、轻松和简单,他就是将诗意全部化解在日常用语中,“漫无目的”的爱就是无处不在的爱,但是在纪念9·11一周年而作的《名字》,柯林斯的态度却有过和他那些诗截然相反的风格,在2002年9月的时候,身为美国桂冠诗人的柯林斯朗读了他“为911事件中的遇难者及其身后的亲人而作”的《名字》,这是他作为公众诗人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次朗读,那些“就如暗夜中滴落的水珠”的名字,那些“打印在夜的穹顶上的名字”,那些“绕着水湾悄悄流过的名字”,那些具体而鲜活的名字,“公民的名字,工人的名字,母亲和父亲的名字。/两眼闪亮的女儿和头脑机灵的儿子的名字。/开阔地里一排排绿色的按字母排列的名字。”所有的名字也许都成了死亡的名字,即将消失的名字,“如此多的名字,心中的四壁已经无处容纳。”诗歌传递出的哀伤、悲痛的确一反柯林斯的风格,所以在那之后柯林斯拒绝在公共场合朗读这首诗,也表示不会将其收进自己的诗集。但是在2013年,柯林斯将重新校订的《名字》收入了这本诗集里,并将它放在最后——柯林斯态度的转变,也许是另一种对诗歌的宽容,诗歌是“第一行总会保持不变”的诗歌,是不该被遗弃的诗歌,但也是面向和“名字”一样多的读者的诗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