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12 《八仙全传》:息虑营营,乃可长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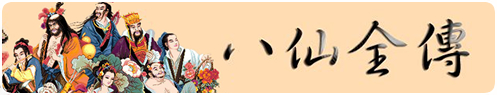
昔人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就是这个道理。从实质讲来,先是一刀一枪,你生我死,四面八方地混战一番,名为大乱,实在还不算真乱。因为这等乱事,所乱者只是一个事字。事尽管乱,人还是人,必致人心皆死,人化为鬼的时代,那才算得真正大乱。
——《第八十回 发预言张天师被废 践前约吕纯阳诞生》
不是牢骚之言,不是玩笑之谈,张果老对天师谈及天地之道,是阴阳转变的因果论,是人鬼相博的善恶论,是天地治乱的发展论,而在大道世界的预言里,道最终的指向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人心之道分开善恶,分开正邪,分开治乱,当然也分开了人和鬼。而要避免世界最终走向天道逆行的末世,也唯有人心可以解救。但是在这终极目标为达成之前,就如张果老所说,“人心欺倒,天道反变。”这八个字就是“乱”字最好注脚,因乱而机诈之风盛行,因乱而官不顾公家,因乱而孝道废除,因乱而不问廉耻礼仪,因乱而人也与鬼同类,“所谓乱在人心,而不在人事。称为根本之乱,不是枝枝节节,一地一时的小小乱事可比。”最后是天地必将复合为一,再入浑人时代。
这是一种末世论,按照张果老的说法,这个时代是至乱之世,不在当时,不在现在,“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内外”,时间上的寓言或者只是小说之作的一种虚构,但是里面却隐含着一种道,一是这样的时代并非不会出现,“虽有大智大圣,如玉帝、元始老君、王母、西方佛和东方朔,也不能为之挽回变化者也。”世界必将进入一种“二次开辟”的轮回。但是另一个意义上,这只是一种按照乱的发展轨迹做出的预言,如果能守住人心之道,也可拯救,正如众仙之祖师太上老君所言:“至道之精,方方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道无所,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净必清。毋劳尔形,毋播尔精,毋狎尔性,息虑营营,乃可长生。”
“毋劳尔形,毋播尔精,毋狎尔性”,此为善,此为阳,此为人心,所以将一切的欲望,恶念都熄灭,“乃可长生”,也就是说世界将进入一种恒久得道的状态中。这是一种终极目的论,而无垢道人用小说写出“八仙全传”,其主旨或者就是要寻找这一种人心之道。又称“八仙得道传”,其“自序”中就不无担忧地指出:“各书既成,复念道统失绪,于今为甚。”数典忘祖是道家之忧,却也是吾身之责,所以他要在八仙从凡人得道的故事中构筑一种人心之道。
人心之道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太上老君的观点中,道可以分成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形,无垢道人开篇就引用一句话说:“神仙们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也就是说,不管是仙人还是凡人,殊途同源,“原是一个来头”,也正是这一个源头,凡人可以成为仙人,但是这凡人成道仙人却必须有缘。缘是善缘,也是孽缘,前生孙仙赐成张果老,嫦娥为孟姜女前世,王月英和蓝采和“生生死死都有联带关系”,李玄收徒杨仁,也都是一种缘,“你可知道仙家最注重的是个‘缘’字,缘之所结,谁也分拆不开。”这缘便将凡人和仙人从同源中分开。但是可成仙之人也还是有着道之形,形是肉体,是俗身,李玄在老子的点化下变成又黑又丑、一只脚儿长一只脚二短的死叫花子铁拐李,无非是形的一种外化,“凡人秽在心,汝独丑在貌,将来周游四大部洲、三界五狱,平常人就很难认得你这丑形怪状的大罗金仙,你就可借此考察人家向道的诚虔虚实,岂不大妙?”因着形而寻找缘,也是得道的一条最基本的路。
有形之后,道的第二个层次是器,大凡成道过程中,仙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器物,老子收李玄为徒的时候,就交给他一柄宝剑,“用之则长,卷入极细,放之可达万里,收之便在眼前。除却上界真仙,无能当此剑锋。”宝剑为的是对付妖魔,而同时教授一些功行,亦是器的层面,“我在三年前即命你多游山水,如今正可做此一步工夫,顺便做些功德。”而何仙姑单身独居在衡山石室内整整修炼了一百多年,也是一种器物层面的修炼。器之上为术,当初老子交给李玄的玄门道经三卷,“上中两卷,能呼风雨,驾云雾,召神兵,致雷电。下卷能穷变化之奇,识未来之事。”这也都是法术。而蓝采和因为日日接近尘网,“见念越重”,去除身上“为官作宰,耀祖荣宗”的意志,而历经磨难,也是术之一种。韩湘子的叔叔是韩愈,作为官宦人家,韩愈要求韩湘子“你要做我韩门令子,须听为叔的指教,把三年来所学的异端之学,完全丢却。”最后韩湘子九度文公,使韩愈得道,也是术之一种。
|
| 编号:C25·2160920·1329 |
由形而器,由器而术,由术则为势,这是道的另一个层次。这个势是一种形势,也就是一种得道的方向判断。道从道家而为道教,在道家之外则是儒家,蓝采和“见念越重”,就是一种从小读书长大为官的念头,“一个人哪能没有上进之心?我们读圣贤书,为的什么?不是想立身朝廷之上,替皇家做些事情么?为甚么不想做官呢?”也正是这样一种功名观,对于成道是一种阻碍,所以要在性灵不昧的王月英的助力,而王月英不能独自成道也是一种缘的表现,一种情的体现,“皆因双方历来的关系太深切了,觉得同生同死,同转凡胎,同入仙界,乃是必然的道理,一定的情势,如有一人不得成道,其它一人,万不能舍之而去。”而这种情也指向人心。而吕洞宾的父母也指望儿子能继承宦业,但是对于父亲把孔孟之道作为长治之道,却提出了相反意见,““孔圣之学是入世正道,其言平易近情,可供为人楷模。人人如此,天下暂可太平,而非永久常治之道。至于出世妙义,还在老君《道德经》内,人人习之,则万年常治,永无乱事。”把《道德经》列于孔孟儒家之上,认为道术正宗才是人生最高学问,其中的逻辑其实是一种俗世之论的鄙视:“今之自命通人者,反鄙而勿道。此大道所以不行,而天下所以常乱也。”
所以无垢道人并非是尊道贬儒,而是鄙视和否定泯灭人心的做法,钟离权曾对未得道的吕洞宾说:“三教异途,而其理则一。儒家训人,最重忠孝。我们既要修道,尤其应该把忠孝大节,时时记在心头,能够如弟子所言,把人生责任一一做完,然后入山修养,那是最好没有的了。”“其理则一”寻找的共同点也依然是关于人心之善。在《八仙全传》的开篇中,平和就是一个孝子,“儿子孝顺父母,都是应分之事。像娘一生忠厚贞节,还得这等毛病,那是不应分的!儿子要能上天入地,无论如何,必要查明这个原因。弄些仙药,治好娘的眼睛,才肯罢休!”他为了治愈母亲的眼疾,冒死硐孽龙口中得到飞珠,用这颗飞珠,不但治好了母亲的眼疾,而且也给周边的贫苦人家治疗难治之症,这便是一种德行。道儒合一,就是超越了器术,超越学派,就如铁拐李对费长房说:“修道既成,道心纯一。俗魔外道,不能破坏,尽你心所欲为。出入进退,无不如志,也无不合度。儒家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者,其理可以路通也。”
而道之势的第二个层面则是劫数论,“天地之间,正邪二气,各有相当声势,正有正派,邪有邪党。自常理论,邪不能胜正,偶遇劫数到来,正人君子往往不能自全,邪气乘机倾陷,亦未尝不能败正。”正和邪,善与恶,以及治和乱,都有一个劫数,劫数未到,那道也就无从谈起,何仙姑曾经问钟离权,“秦皇如此残暴,师兄这样的道术倘能一剑了当,岂不为民除去一个大害头儿。何必零零碎碎、辛辛苦苦的做这等事情呢?”而铁拐李的回答是:“大凡劫数所在,休说免除不得,就要把劫数收小一点,期间缩短一些,也是断断办不到的。秦皇生性残忍,当然不作好事,然而这也不是他自己所能作得主的,老实说,他也不过是应劫而生,替劫数作个运行使者罢了。”铁拐李也说:“秦皇即位以来,自恃天命,残暴凶横,草菅民命,比七国时候更甚。果然这都是劫数所定,非关秦皇一人之事。即如秦皇本人,也是应劫而生的一个魔君。”而最后八仙过海的时候屠龙,却并未让玉帝高兴,'当有元始老君率同大弟子火龙、缥缈二真人,说明二龙大闹天宫和截断地脉二事,应得果报。”
劫数论可以看成是因果论,而将善恶看成是劫数,却容易陷入未知论,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逻辑是:“当以尘世之刑,代替天庭之罚,君民两方都为劫数所支配,不由本身作主。”不由本身做主,由天庭决定,而天庭之命却是一种天道,所以道的最后一个层面自然是天道,天道看起来依然存在着一种不可知论,但是天道之存在,就在于廓清正邪、善恶、阴阳、治乱,“比诸尘世就是治乱两事,世不能常治而无乱,即可知天道不能有正而无邪!现在你我所见的蛟精如此凶狠残忍,以为杀不可恕,岂知天地之间此等万恶妖魔正不知多少,其生也原于劫数,其行事却也未尝没有一种因果的道理在内。”于是又回到了人心的终极,正如三姐所说,那些损人利己之事,“岂天道所能许可?”
为什么会有万恶,会有至邪,会有极阴,会有打乱?那就是失了天道,失了人心,“而自无心念可言,方才可以悟于大道”,所以张果老的末世论所看见的就是千年之后人鬼无别,人而化鬼,就是人心皆死,“人心至此,可称乱极。合到上古的浑人时代,才可称得一治一乱。从此以后,天地必将复合为一。又须经一番开辟工夫,再入于浑人时代,为再治之开端。天道如此,莫可如何。”但是这将来之事或许是一种预言,八仙得道,从形开始,至器,至术,至势,最后也遵于天道,得于人心,“自此天庭安宴,海宇澄清。天府既无事可记,本书也就此完结。”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42]
思前: 《死亡诗社》:洞穴里的浪漫主义
顾后: 身上流淌着绿色的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