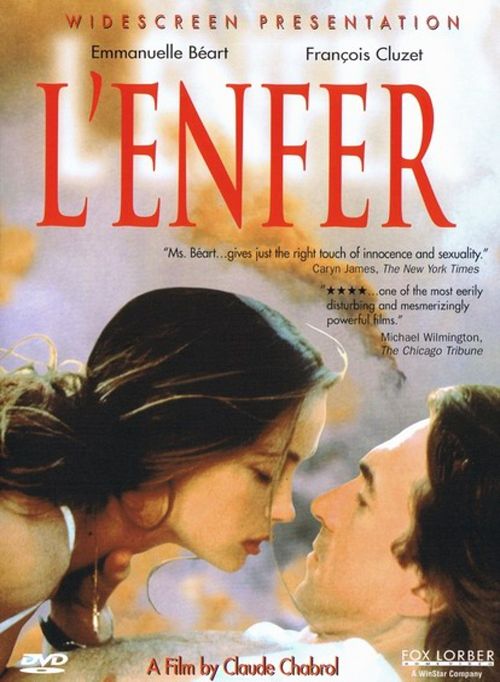2019-08-12《美丽的折磨》:你的伤口又裂开了

几乎平淡且平庸地铺陈了90分钟,夏布洛尔却把高潮放在了最后:雨天,夜晚,绳子、药物、镜像、鲜血,以及最后字幕里的“未完”,在揭示一种病态的生活同时,又制造了影像的开放性:被绑住的妻子奈莉有没有在早上醒来?拒绝去心理医生诊所的布里有没有逃离?甚至,奈莉是不是最后成为了布里臆想症的牺牲品,而布里是不是在焦虑和折磨中走向了终点?
一个夜晚,两个人,是不安的,所有可能的危险都从夏布洛尔诡异的镜头里冒了出来:从医生阿尔努那里回来,夫妻两个人又面对着彼此,奈莉调好了明天起床的时间,因为按照阿尔努的建议,他们两个都将去诊所看心理医生,而布里像往常一样拿了两粒安眠药,本来服用安眠药只是他的事,但是这次奈莉也希望能够入睡。明天去诊所,晚上服用安眠药,两个人的生活在这个夜晚就显示了某种病态,但如果从正常的逻辑出发,他们的行为都是积极的,都想要解决两个人积怨已深的生活。
但是正因为一种病态的存在,于是夏布洛尔的这个夜晚就可能走向开放:到底是布里患上了臆想症还是奈莉被折磨了?在阿尔努那里,布里说起自己为什么要打奈莉的原因:“她天生是个撒谎者,她病人,有了臆想症——她发病时和任何人鬼魂。”当布里说这些话的时候,奈莉坐在那里,受伤的她没有辩解,似乎在默认布里对她的指责,而从这个逻辑出发,奈莉似乎真的患上了臆想症,而且阿尔努提出的建议是:明天两个人一起去诊所看心理医生。面对这个建议,奈莉甚至也是默认的,而布里却拒绝,当他们回到房间的时候,当奈莉调整好时钟的时候,布里再一次强调明天不会去诊所。
布里对于心理诊所的拒绝是明确的,除了在阿尔努和奈莉面前提出明天不去之外,他内心的抗拒也越来越强烈,他打开窗户的时候,看见对面开来一辆车,之后和奈莉争吵之后再次打开窗户,看见车上下来两个医护人员,他们站在车头望着布里的方向,双手交叉在胸前,似乎做好了强制带离的准备;而当奈莉服用了安眠药睡去的时候,他仿佛听到了掉落在地上的电话里传来奈莉的呼喊:“他病人。”而最后,看着床上被绑着手的奈莉,布里一直在挣扎着:“我究竟怎么了?我们要去诊所,我们俩,但我们仍在这儿,像什么?我迷失了,只希望她不要想了……”
布里内心拒绝去看心理医生,似乎都处在理性思维中,而服用了安眠药、沉睡着的奈莉,却是走向了非理性,所以看起来,奈莉更像是一个病人,更需要治疗。这种可能的场景在夏布洛尔那里具有了悬疑的意义,而在最后的高潮里,随着布里那锋利的刮胡刀刮破了脖子,这种悬疑更走向了开放,镜头在跳跃,在闪现,里面是奈莉和男人“鬼混”的画面,是她极具诱惑的身体,当然还有滴落下来的鲜血。刮胡子的场景出现在早上六点之后,布里把还在入睡的奈莉叫起来,“六点了。”他说。然后两个人开始洗漱,“阿尔努快要来了。”布里让她动作快点,然后自己刮胡子。但是当刮胡子划破了脸,当那些跳动的镜头出现,这一幕却又回到了还没起床的夜晚。
| 导演: 克洛德·夏布洛尔 |
夜晚,雨还在下,昏暗的灯光下,布里看到奈莉的手仍旧绑在床上,但是自己的额头却流了血,对着镜子他说:“你的伤口又裂开了。”第三人称单数,无疑布里是在和另一个自己说话,站在镜子前,似乎就形成了一种镜像效果,而那个起床之后的六点,那个准备去心理诊所的明天,是不是也是一种镜像?所以,从闪现的镜头,从镜子前的对话,从奈莉被绑着手的现场,以及最后“我迷失了”的不安,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是布里的臆想:他臆想了不想到来的明天,臆想了门外准备将他们拉走的医护人员,臆想了奈莉起床和他和好的一幕——“我们从头开始吧。”在洗漱的时候,布里这样说。
想和奈莉从头开始,说自己迷失了,布里表达着强烈的意愿:所有发生的一切暴力和猜忌,都只是自己的臆想,而臆想的唯一原因是不想失去妻子,不想在“美丽的折磨”中受到伤害,所以刮胡子而使得伤口裂开的镜像可以不存在,那流出来的血可以被虚构,甚至迷失的自己也可以找到还原生活的方式,但唯一不变的是:自己爱着妻子奈莉,不想伤害她,更不想让她走进心理诊所。在这个意义上,处在内心冲突世界里的布里患上了明显的臆想症,所以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使用暴力?为什么会怀疑妻子说谎并和男人鬼混?为什么要最后把妻子绑起来。
美丽的折磨变成了悲剧,他起先是把门锁住了,奈莉求他开门,理由是要去看一下生病的儿子文森,布里开了门,奈莉还拿走了钥匙,但是她还是回来了,并告诉了他钥匙在铜像下面,当布里拿来了钥匙,又把门锁上,却用绳子将奈莉绑起来,并设计让她服用了安眠药,毫无反抗的奈莉就这样失去了挣扎和反抗的能力,而布里对此的解释是:“我采取的是必要的防范措施。”之后还说了一句:“野蛮的野兽必须被绑起来。”绑起来是防止她离开,是为了挽救爱,所以早上六点中那一幕便成为他的幻觉:“我曾失去了这一切,但很高兴又回来了。”
|
《美丽的折磨》电影海报 |
但是,这镜像,这幻影,都是脆弱的,也正是脆弱,才会使得伤口裂开,才会使鲜血流出,而且越是不想让妻子离开,越是想要占有她,这个伤口就越是容易裂开。但是这个裂开的主体是“你”,布里似乎永远生活在他者的世界里:在休息室里看到妻子和马歇尔在一起看幻灯片之后,忧伤的他跑到湖边,站在木板上对着湖水自言自语,这种自我的呓语因为有一个他者存在,才使得臆想症越来越明显:你开始怀疑,你开始愤怒,你开始暴躁,你开始不顾一切。于是,奈莉说要去镇上看望母亲,他开着自己的车跟在奈莉的后面,跟踪她,并且想象她和马歇尔的约会;在湖边,他穿过树林奔跑着,因为他看到马歇尔的快艇带着奈莉,后来他们甚至上了对面的岛,而重新上船之后马歇尔和奈莉又显得很亲密;在停电的夜晚,布里寻找自己的妻子,后来看到她在给客人发放蜡烛,但是发现她的裙子里蜡油,接着自己上了阁楼,发现了奈莉的手镯,询问奈莉有没有去过阁楼,起先奈莉说没有,后来想起曾经去过,但是为了去看保险丝,但是布里却仿佛看见了妻子在阁楼上和男人幽会……
妻子的每一个举动,他都能找出背后的疑点,妻子的每一次外出,他都无法心安地跟随,在大家观看录像的时候,即使是文森的画面,躲在暗处的布里也想象着奈莉的不忠;当发现妻子不在房间,他几乎一个一个房间搜寻过去,在摄像师杜汉那里看到有两只酒杯的时候,便起了疑心,让杜汉第二天就滚蛋……正是因为不断怀疑,所以对于奈莉的话不再相信,甚至说她一直在说谎,在挥之不去的阴影中,他终于强占了奈莉——在那一刻,他变成了虚构的自己,一个可以强奸妻子的“他者”,“我要像那些男人一样,也让他们看见。”奈莉在挣扎,在叫喊,而他以暴力的方式惩处了妻子,也满足了自己的报复心理。
“漂亮的女孩有折磨我们的权利。”杜汉曾经这样开玩笑地说,漂亮的女人是“小妖精”,是“鬼精灵”,但也是“铁镣”,深深束缚住了布里,他活在镜像世界里,活在臆想中,活在虚构的“他者”里,所以臆想者是悲剧的存在,而被臆想的对象也在无法摆脱的世界里感受到绝望。夏布洛尔如此编织一个双重伤害的故事,其用意在哪里?是探讨婚姻中男女的地位和相处原则,还是用影像制造一种心理悬疑的故事?除了最后高潮部分打开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之外,如果夏布洛尔的用意在第二种,那么显然这个故事在悬疑方面的营造是不足的,夏布洛尔讲述这个故事一直是四平八稳的,布里对妻子的怀疑也并没有设置太多的陷阱,而臆想症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清晰的。
而且最大的不足是,仿佛布里的这种臆想症是突然出现的:一开始影片的基调是欢快的,湖水、游玩的人,乡野,骑着自行车的人,那时的奈莉还是一个女孩,当时的布里也在忙于酒店开张,于是他们结婚,于是他们有了孩子,于是孩子慢慢长大——夏布洛尔用了几个镜头,就把这些时间节点连缀在了一起,仿佛布里的婚姻就此走向了永远的幸福。但是这一切却被突然打破了:那一次布里回到酒店,没有看见奈莉,正当他想上楼的时候,却发现下面的休息室里有光闪过,于是,他走过去打开了门,发现奈莉正和马歇尔在看幻灯片。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对于布里看来说,却成为一种致命的伤害,他就这样陷入到猜忌中,沮丧地走出去,然后来到了湖边,然后开始自言自语,然后开始怀疑妻子,最终变成了臆想症。
在此前,他们相爱,他们结婚,他们生下孩子,他爱着奈莉,奈莉也爱着他,两个相互爱着的人为什么就因为这件事从此被折磨?夏布洛尔显然没有交代更多的原因,仿佛一下子进入到了他预设的主题里——如果要找出一些隐秘的线索,其中之一是:布里曾经说自己为了酒店付出了许多,这是15年省吃俭用加上母亲的积蓄加上贷款而开创的事业,所以他总是感到累,也因此每天要靠安眠药入睡;另一个线索是:当孩子文森出生之后,两人世界的生活被打乱,正当亲热的时候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于是奈莉起来去照看哄他入睡,而那时一个人的布里开始对着镜子自言自语,这或者也是之后文森也被服用了安眠药的一个源头。
但是这两条线索,在夏布洛尔那里都是隐秘的,也没有在之后的情节中变成一种原因,所以最后布里的臆想症变得缺少铺垫,它只是展现在“美丽的折磨”的过程里,当伤口一次次裂开,就像是另一个人在控制,另一个“你”,另一种幻影,而最后几分钟的高潮又像是彻底地撕裂了伤口,在鲜血、捆绑、迷失中演绎为一种惊悚,只是结果太快地抵达,变成了夏布洛尔自己的臆想。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