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6-02 今后大地上的孩子排列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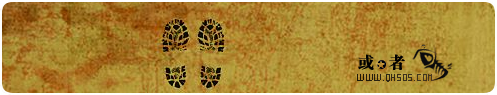
呼呼的火苗一直在
自言自语,却允许了
我们无意的倾听。
——W.H.奥登
夜晚的火苗其实是一盏灯,并不昏黄的灯,亮着,照见身边的事和物,照见昨晚和今晨,照见凌晨的前前后后——却是在别处的灯。当一种夜也以自言自语的方式被覆盖的时候,那亮起的世界里,谁在叙说,谁在表达,谁又在“无意的倾听”?
一切,都似乎是以我作为一个必然的观察者,当规律性的生活在寂静的夜中终结,那从今天走向零点而被拉长的时间里,我仿佛只在一处不醒的梦里。而在反面,他仿佛进入了诗句里,呼呼的火苗在蹿腾,一些文字开始复活,自言自语其实不是讲给自己听的,因为所有的夜都需要另一个人的倾听。隔着两个小时,隔着一个房间和走廊,隔着醒着和入梦的两种状态,夜开始说话:
最后一个六一,最后一次戴红领巾,最后一次游园活动,最后一次写“六一快乐”。终于在这一年,我们告别了童年,但是,时光却无比残忍。他留给世人一座记忆的城堡,但这座城堡却换不回那个和过往一样的昨天。从今以后,世间再无一条路能让我们与童年并肩。过去的,终究不复再来,这是离别的意义。我们告别的是童年,可前方,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着我们。
是小五,是感悟,是发在了朋友圈,是在零点之前的自言自语。其实,在这个“最后一个六一”之后,还有一年多的初中生活,只是在看起来慢慢长大的时间里,对于童年的感怀最后变成了对于时光的感叹:“多年后,当我们笑时,当我们哭时,当我们醉时,你们是否还会想起二月芳草,想起我们的童年,想起曾经的时光,曾经的自由,一起进,一起退。”在零点之前完成了抒怀,零点之前,不如说是十二点之前——十二点永远指向今天,指向节日,指向六一,指向不想逝去的童年。
只是十二点的符号最终被零点所代替,只是六一的节日翻过去却是新的开始,只是在自言自语中即使被无意倾听,还能返回?早上翻看朋友圈时才读到这段话,评论里的那些话大约也是一种挽留:但愿每个人都是孩子。对他,或者对我?仅仅是对于记忆的一种缅怀,当“我们”成为一种主体,看上去还是有些矫情,但是对于小五来说,这或者真的是真情的流露——在“今天”还留在那个节日的时候,他和同学一起参加了游园活动,在红领巾中体验了没有逝去的童年,甚至也收获了不同的礼物:小袋鼠在晚自学结束时气喘吁吁地奔跑而来,只为了交给小五五页关于人生的感悟;小五自己购买的《足球周刊》齐齐整整地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礼物或者是仪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只剩下仪式的节日里,我们似乎以为他已经长大,已经不再回过节日,以为会在转身中面向明天,但是为什么他会在十二点之前说出这些话?为什么我们会在昨天过去之后倾听它们?时间似乎被人为地错开了,就像隔开的两个房间,就像醒着和入梦的两种状态,就像昨天和今天的两个日子。错开,无非是自己走上了那条会留下影子的路,在身后,原先是故意不去看它的:目光向前的时候,小五开始成为初中生;脚步向前的时候,他开始成为住校生,身体向前的时候,他从来不打开日记本讲述学校的故事,甚至那一辆独自骑行的自行车,那背着书包星期日下午返回学校的毅然态度,都变成了独行的符号。
故意不去看身后的影子,是因为他开始学着自己长大,开始剥离另一种被念叨的生活,开始独自面对人和事构筑的世界。但是,在这个一去不复返的节日里,他却转身了,不是为了看见我们,而是为了看见自己不消逝的过去,而在不消逝的过去里,有记忆的城堡,有童年的快乐,有无虑的生活,有自由的向往。“仅仅是过去的某个时刻吗?也许还远远不止。某个东西,它同时为过去和现在所共有,比过去和现在都本质得多。”所以,在转回目光、转回脚步,转回身体的时候,他并非是自言自语,他讲给另一个自己听,讲给不在夜里的自己听,讲给不面对试卷、分数的自己听,或者,是讲给绕过了时间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醉的明天的自己听。
而现在,仿佛是深沉的,是孤独的,是小心的,当写下那些句子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已经走向了明天,在无可遏制的时间里,返回更像是一个童话,只是逗留而已,短短的一天,短短的一夜,短短的几百个字,短短的童年,就这样变成了永远的铭记。而其实,当被带向那个叫做零点的时间之后,我们无需转身,更本质的东西已经在心里,已经变成了不熄的火苗,已经在那里被自己倾听,即使展开的时间叫做“今后”,那行走在上面意气奋发的人还是叫孩子:“梦想将孩子从历史中解脱出来,梦想将他置于时间之外,使之成为时间的局外人。再进一步的梦想,这永恒的孩子,被广为颂扬的孩子,这就是神。”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1991]
思前: 《电锯惊魂》:谁是游戏的观赏者
顾后: 《洞》:关于越狱失败的几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