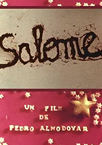2018-09-11 《莎乐美》:我为美而献祭

导演: 佩德罗·阿莫多瓦,而编剧在佩德罗·阿莫多瓦的名字之后则是奥斯卡·王尔德,在这部“合著”的作品中,阿莫多瓦显然慢慢将莎乐美脱离了圣经中那个复仇者的形象,而注入了更多王尔德的影子:当莎乐美说“我是宫廷中的一个舞者”,当优美而疯狂的舞蹈临“太阳看出你了”,当亚伯拉罕可以为她奉献一切,莎乐美完全变成了一个美的代言人,而这种美并非是解构她的宗教性,反而呈现了上帝的多面性,甚至在伦理和宗教的合一中完成了对美的人性定义。
佩德罗·阿莫多瓦的这部电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莎乐美作为一名舞者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作为希伯来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在遇到莎乐美之后,的确表现了对于美的一种痴迷,这种痴迷使得他离开了自己身上具有的伦理性职责。他起先是和自己的儿子以撒克行走在路上,然后教伊萨克吹走笛子。当亚伯拉罕抚摸着以撒克,并教授他方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老师,在这个意义上,他承担的伦理责任,就指向了艺术和知识。但是当莎乐美从那些羊群中出现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这个伦理角色就发生了变化。
他让以撒克自己吹笛子,然后独自走向了莎乐美,那时他不认识莎乐美,只是看到被黑纱蒙着脸的女子,走向莎乐美,只是走向一种男人之外的女性,或者可以命名为“普遍性”吸引,当莎乐美告诉他自己叫莎乐美,是宫廷的舞者,于是在亚伯拉罕那里就开始了另一种命名:“你给我跳舞吧,我愿奉献一切。”看她跳舞,而献上自己的一切,可以视为对于女性、对于美的痴迷,当他提出这一条件的时候,其实隐含着自己忽视的危险,因为莎乐美跳完了那一曲舞蹈,将脸上的面纱撕碎扔在地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作为观众发出了赞叹声,“太阳也出来看你了。”的确,当金色的阳光洒在莎乐美的飘逸的头发上的时候,当她的裙子在微风中舞蹈的时候,亚伯拉罕体会到了一种纯粹的美,而这种美让自己像自然的一切一样,带着欣赏的目光。
|
| 导演: 佩德罗·阿莫多瓦 |
 |
于是问题出来了,莎乐美跳舞完毕,提出了一个要求:“我想你儿子的头放在花盘上。”因为当初亚伯拉罕提出可以奉献一切,那个把以撒克的头拿下来给莎乐美,也毫无问题,“你已经向上帝发誓,请遵守你的誓言。”当莎乐美这样说的时候,她已经将这个电影推向了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上帝的出现,亚伯拉罕当初答应的话就变成了在上帝面前的誓言。于是矛盾出现了,他是一个父亲,以撒克是他的儿子,这是一种伦理的关系;他向莎乐美承诺,莎乐美又把承诺变成了上帝的誓言,这是一种宗教信仰,所以在父亲和上帝之间,亚伯拉罕选择了宗教,选择了信仰。
他告诉了以撒克,而以撒克开始逃跑,亚伯拉罕便开始追他,而以撒克在路上遇到了莎乐美,莎乐美用催眠的办法将他控制,于是,以撒克乖乖跟着亚伯拉罕来到石碓前,然后慢慢躺下,而亚伯拉罕为了践行自己的诺言,要割下以撒克的头,以献祭上帝。在这个第二阶段,随着莎乐美变成一团火,她彻底代言了上帝,“亚伯拉罕,你在做什么?”她问道。而亚伯拉罕回答的那句话是:“上帝,请原谅我怕所犯下的罪。”
为什么亚伯拉罕会认为自己犯了罪?是因为遇到女性而停下来打招呼?是因为痴迷而答应奉献一切?还是因为自己要亲手将以撒克献祭给上帝而失去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伦理责任?宗教超越了伦理,才使得亚伯拉罕认为自己有罪,才认为以撒克必须被献祭,所以亚伯拉罕要对儿子动手的时候,他无怨无悔。但是这里出现的一个悖论是,当亚伯拉罕为信仰而牺牲一切的时候,他自己抹除了人性和伦理上的父亲角色,但是当父亲角色被抹除,他的献祭其实没有了丝毫意义,而这个悖论在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中早就有了解读。
|
|
| 《莎乐美》电影海报 |
那一刻,亚伯拉罕筑起了祭坛,那一刻,亚伯拉罕摆好了劈柴,那一刻,亚伯拉罕将以撒捆绑,那一刻,亚伯拉罕拔出了刀子。摩利亚山上,只有亚伯拉罕和以撒?只有即将到来的死亡?那把寒光闪闪的刀子印照出的只有虔诚的亚伯拉罕?只有害怕而被献祭的以撒?或者即使当献祭被制止的时候,还有一个上帝的使者?还有一头燔祭的公羊?可是上帝在哪里,选中亚伯拉罕的上帝在哪里,考验亚伯拉罕的上帝在哪里?制止亚伯拉罕杀死儿子的上帝在哪里?谁都没有看见,只有亚伯拉罕感受到了恐惧与颤栗,只有亚伯拉罕体验到了不安与忠诚,也只有亚伯拉罕解决了自相矛盾的悖论。
上帝是莎乐美,上帝是一团火,上帝无处不在,所以这个关于信念和信仰、审美和宗教的悖论,就成为无法避免的矛盾,当亚伯拉罕要献祭以撒克的时候,他内心是一种不安,伦理上的不安,因为一个父亲对儿子有着最高、最神圣的职责,而要得到安静,要保持神圣,就必须弃绝作为一个父亲个体意义的行动,所以他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虔诚者,上帝才是他最后的神圣,才是最高的目标。但是这个“恐惧与颤栗”的故事,最终却以另外的方式被化解,“不用在意,亚伯拉罕,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出现的过失是你的本性,只是测试你是否会又凡人的罪,因为我一度觉得你已打破了凡人的本性,莎乐美只是我选择各种各样的人物代表之一,当她跳舞时,你仰慕的是我,唯一的上帝,也是我决定让你献祭你的儿子的原因。”
上帝这样解释,莎乐美是上帝众多形象之一,当亚伯拉罕停下脚步然给她跳舞时,她就是上帝,在女性和美之外是上帝,或者,对女性和美的向往就是对上帝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尽管是凡人的罪,却也是一种本性。所以亚伯拉罕被赦免了,当他和儿子离开时,捡拾起莎乐美跳舞时落下的黑纱,因为上帝说:“带上这些面纱给你遇到的女人,当她们去教堂的时候带上面纱,以示尊重。”最后上帝的话是:“现在回家把,照顾你的儿子。”
亚伯拉罕终于没有将儿子献祭,也得到了上帝的宽恕,当莎乐美变身为上帝,这是宗教对于世俗的超越,而上帝宽恕他,让他变成一个凡人,则是本性的回归——这种对于宗教故事的改写,正是从人性和审美的角度来消除那个悖论,消除恐惧与颤栗。莎乐美在圣经中就是一个复仇者,她在希律王面前舞蹈,希律王答应她给她想要的东西,最后莎乐美在母亲的挑唆下,要希律王索取义人约翰的头,因为做了宣誓,于是希律王就把约翰的头送给了莎乐美。
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提香,就创作了以这个故事为原型的绘画,画中莎乐美就是拿着约翰的头颅,完成了复仇。但是这个圣经故事在王尔德的戏剧里却变成了另一个版本,他彻底改变了故事的原意,融入了自己的唯美主义叙事手法,表达“爱”与“美”、“爱”与“罪”的唯美理念。而这种唯美理念在《恐惧与颤栗》中也得到了体现,“人的本性是激情,在激情中,人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亚伯拉罕又回归到个体意义,他对莎乐美的赞赏,愿意奉献一切的愿望,都是从人性这个角度做出的,而这种人性就表现对于美的欣赏,也就是审美信念。而在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电影里,审美也是亚伯拉罕做出的一个选择:他教以撒克吹笛子,他坐在那里欣赏舞姿,像一首抒情诗,在审美意义上超越了宗教,一样具有精神的意义。
毋宁说,他最终要献祭给上帝,不如说献祭给美,而最后上帝赦免了他,也告诉他这是人的真正本性,“因为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在让他回去的时候,也告诉他把地上的黑纱拿到教堂上去,给那些女人,因为这些在风中飘散的纱巾,不是对宗教的亵渎,而是美的象征,是上帝的信物,而最后让他回去照顾儿子,则是亚伯拉罕返身成为一个父亲,所以关于宗教和伦理的那句话:““傻孩子,你认为我是你父亲吗?我是一个上帝的崇拜者。”完全可以改写成另一句话:“傻孩子,你认为我是一个上帝的崇拜者吗?我是你父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854]
思前: 《禁忌的预告》:以惩罚作为回应
顾后: 《怀旧者》:一镜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