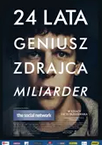2017-09-11 《社交网络》:平等的孤独和冷漠

听说过马克·扎克伯格,听说过Facebook,听说过创造的无数传奇,但只是听说,作为现实一种,隔离在墙后面的那个世界就是一个无法走进的传说,即使它活在大卫·芬奇的影像世界里,也只是以一个旁观者身份,隔着屏幕看见世界的另类精彩。但这不是真正的现实,当2010年的Facebook在207个国家拥有5亿用户,当它的市值达到了250亿美元,但是在这个从王国到帝国的互联网伟大传奇里,马克·扎克伯格还是在一个人的黑夜里,对着电脑屏幕上艾瑞卡的主页,不断地刷新,不断期待新的内容、新的关系在某一个凝固的时间里出现。
他是Facebook的创始人,他创造了这个伟大的“社交网络”,但是却最终以隔绝的状态期待自己被拉进一种网络中,这种网络不是逃离现实,不是虚拟存在,而是切身变成现实的一部分,那个穿着裙子的女孩照片,就在她自己的Facebook上,但却是静态的,固定的,即使马克加了她好友,即使不停地刷新,这个夜晚依然没有发生改变,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黑夜,无法进入的世界是一种孤独,无法互动的状态是一种寂寞。
这或许就是我们生存在社交网络上的本质,他建立了庞大的“脸书”王国,5亿用户在那里获得了某种存在感,但是在5亿这个庞大的数字面前,他还是一个人,一个需要安慰的人,一个渴求交流的人,一个希望拥有爱的人,简单的需求,其实被淹没在巨大的网络中,这或者是马克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而这种被隔离的感觉或者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最冷漠的地方。而马克最初要建立这个网站,他的出发点就是在虚拟世界里寻找一种认同,改善一种关系,甚至培育一种感情。
“你得了俱乐部综合征。”这是马克曾经的女友艾瑞卡对马克的评价,“你不用去上学了,你就念个波士顿大学。”这是马克对艾瑞卡的愤怒。在那间嘈杂的咖啡厅里,他们坐在彼此的对面,情侣这样的身份并没有让他们的观点达成一致,马可谈论的凤凰俱乐部,艾瑞卡喜欢的赛艇队,代表着不同的需求,而艾瑞卡缓慢的叙述,马克快速的语速,又让他们在不同步的情况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间隙,当马克终于在博客上骂她是个“贱货”,只是靠着“半胸内衣支撑”起来的自信,而艾瑞卡也骂他是个混蛋——一种侮辱,其实和相异的观点无关,在现实的对坐中,在网络的互骂中,其实肢解的是现实的关系。而马克最好的室友后来成为Facebook合伙人的爱德华多,他的女友闯入他的房间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在Facebook上的情感状态还是单身?”当爱德华多说自己工作太忙,或者是不懂如何修改,她的女友诧异地问道:“一个Facebook的创始者,竟然连最起码的情感状态也不会修改?”
|
| 导演: 大卫·芬奇 |
 |
这是2003年秋天发生的故事,一个简单的投票系统使网络瘫痪,除了如马克自己在听证会上陈述说是网络存在漏洞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学校的男女生需要这样一个聚合的平台,无论是投票还是其他,其实他们虚拟生活是单调的,所以在马克看来,这一次事件让他有了一种发现市场的快感。而之后卡梅隆和泰勒这两个赛艇队双胞胎的创意,又让马克找到了真正的市场,他们邀请马克开发旨在帮助哈佛学生建立交流平台的“哈佛关系网”。那时候的哈佛大学存在着两类交流体系,一种是加入凤凰俱乐部派对,另一种则是现实中很普通的来往,前一种加入条件苛刻,“一个夏天你能赚30万也未必能加入俱乐部。”而拥有蓝血贵族家庭出生、父亲是花街精英的双胞胎才可能成为其中的会员,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交平台,很多人只能兴叹;而后一种建立在现实之上的普通关系,其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那就是它只是鉴于认识好友之间的交流方式,在时间和空间的错位中永远无法零距离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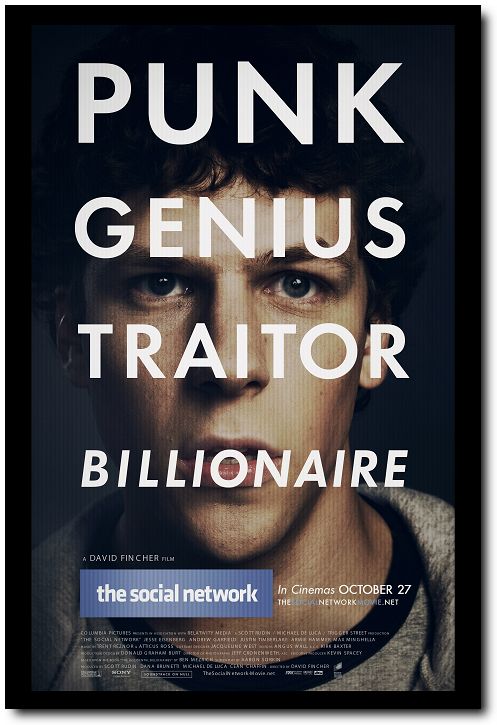 |
| 《社交网络》电影海报 |
所以哈佛关系网对于马克来说,已经超出了一个简单的校园网络的构想,就在他为双胞胎兄弟建设网站的过程中,自己也着手开始建设全新理念的社交网络,而这个创意事后成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它将自发、无序的互联网推向一个有组织、有阶层、实名制的社交网络中。2004年1月11日,Facebook域名注册,在加入了情感状态等重要功能之后,2004年2月4日,Facebook正式上线——从最初的6050人注册,到4000名注册用户,再到突破10万用户,乃至拥有5亿这个庞大的用户群;从一开始的哈佛大学,到美国其他大学,再向世界各地扩张而成为207个国家的社交网络,Facebook几乎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为最大的社交网络,上演了一个互联网的传奇。
但它不是简单的关系网,当在肖恩的建议下把“the Facebook”的“the”去掉正式改成“Facebooke”,其实预示着它将走出“特指”的范围,而成为一种互联网意义上全新的社交模式,不限地域,不限人群,不限国家,而最终它在从王国到帝国的扩张中,必然是为了一种经济利益。在马克最初的动机来看,他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技能,仅仅为了满足一种需要,或者仅仅是为了一种酷——在哈佛大学加入凤凰俱乐部的派对是一种酷,加入“加勒比海之夜”是一种酷,甚至像双胞胎一样成为赛艇队队员也是一种酷,但是当去掉“the”成为“Facebook”之后,这种酷也完全变成了一种投资,一种合作,一种资金的运转,一种关于产出和收益之间的经济行为。
从爱德华多的1000美元起步,然后租用服务器,然后招聘实习生,然后租用办公设备,facebook走上了一条发展之路,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当最初的酷被慢慢解构,新产生的关系让社交网络走向另一种现实。马克在其中面临了两场官司,一个是双胞胎兄弟控告马克盗用了他们的网络,他们认为Facebook的创意就起源于自己的“哈佛关系网”,犹豫马克一再也忙为理由,最后哈佛关系网不了了之,而Facebook却拥有了上亿用户。其实这个官司看上去是一种经济上的纠纷,但是双胞胎兄弟以其高贵出生,实际上是想建立另一种等级,以便让自己拥有掌控权,在Facebook不断创造奇迹的时候,他们寻找各种支撑自己利益诉求的法律和规定,目的就是“我们要把臭小子干掉!”但是当他们拿着哈佛大学的学生手册去校长那里控诉的时候,校长却告诉他们:“这里没有特殊对待。”实际上传递了一种理念,所谓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新的互联网时代,根本没有市场,而这也是Facebook之所以流行的最大理由。
马克面临的另一场官司,则是和爱德华多关系的破裂。从哈佛大学是同住在科克兰公寓的同舍好友,到一起开始创建Facebook,他们都是合作者,马克提供技术,爱德华多提供资金,但是在Facebook壮大之后,马克的酷和爱德华多的盈利之间产生了矛盾,再加上肖恩的介入,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爱德华多一直希望像以前一样保持和马克的良好关系,在他看来肖恩只是一个“租房客”,根本无法成为Facebook的合作者,但是马克的肖恩之间似乎更多共同语言,从他最初采用了肖恩的建议去掉了“the”,到后来搬到加州全身心推广Facebook,以及之后吸引彼得的50万美元投资,都让Facebook不断迈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但是肖恩本身也带着生意人唯利是图的特点,当一百万用户的庆功宴变成一场“伏击”,爱德华多的名字已经从Facebook的首页创始人一栏中删去,而自己的股份也不断被稀释到最低水平。
“我要拿走我的那一部分。”这是爱德华多在“伏击战”中对马克说的话,在那一个值得庆祝的晚上,爱德华多愤然离开了Facebook,肖恩因为和实习生吸毒被抓,而马克坐在电脑前若有所思地说出了一句话:“回家吧,肖恩。”对于三个人来说,是Facebook让他们连接在一起,就像社交网络本身一样,他们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不是只是虚拟的网络?马克真的窃取了双胞胎兄弟的创意?他真的背叛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合伙人?友谊、忠诚、背叛、嫉妒,在Facebook的背后,这些主题又把这个社交网络拉回到赤裸裸的现实,就像肖恩对马克说的:“这就是现实。”
“你不是混蛋,你只是太努力想要变成混蛋。”这是辩护人对马克说的话,从艾瑞卡骂他“你是个混蛋”开始,马克在这一种失恋的状态中开始寻找自己,但是当Facebook变成了社交帝国的时候,他的最初、最原始的愿望根本没有实现,甚至越来越远,最后那两场官司以庭外和解的方式告终:卡梅隆和泰勒接受6500万的庭外和解,并签署了保密协议;爱德华多受到了未知数额的庭外和解,他的名字保留在Facebook首页创始人栏中。6500万和未知数额,其实都是用金钱代替了友谊,谁对谁错,谁胜谁负其实没有了意义。
而这或者正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本质,当马克拥有Facebook这个帝国的时候,他其实也变成了一个符号,他自己在哪里?在爱德华多愤怒的目光中?在肖恩激情的表情里?还是在自己夜晚的孤独中?没有等级差别,没有地域不同,所有的用户在分享信息,在推广自己,在构建关系,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也被数以亿计的用户淹没;每个具体呈现而丰富的主页世界,或者更是异化的世界,而那个孤独的自己,也许只能在一遍又一遍的刷新中找到一种存在感。网络是平等的,孤独也是,冷漠也是。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980]
思前: 《毕业生》:游戏,在路上
顾后: 博尔赫斯:另一个,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