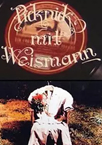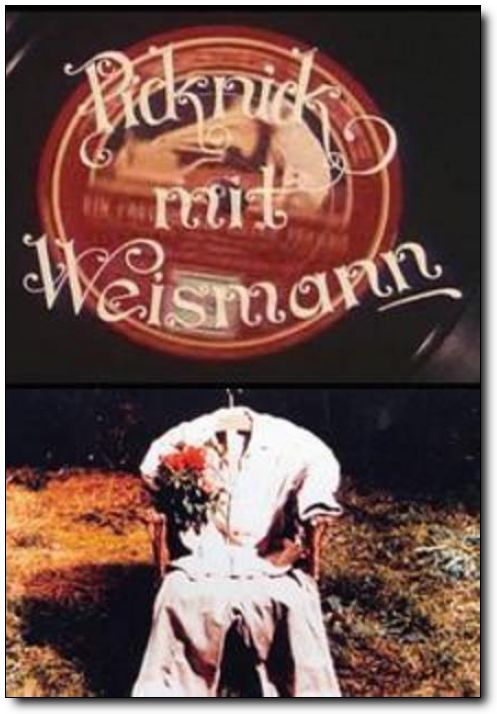2018-10-01 《与魏茨曼野餐》:我只是唱起了一首挽歌

世界是美好的,是安静的,甚至是纯粹的,这里有舒适的阳光,是清脆的鸟鸣,有高大的树木,有平整的草坪。虽然是秋天,但是大自然提供了一切可以抒情的东西,即使是衰败的开始,沉浸其中,何尝不是对生命的感悟,何尝不是对于美的体验?
不管是沉浸,还是感悟,或者是体验,人必须是其中最主要的元素,大自然因为人的存在而具有了一种人文关怀,于是,有了那摆放在那里的椅子,于是,有了敞开着的床,于是有了存放物件的壁橱和抽屉,于是,最能表现人的抒情故事的莫过于那些音乐。把唱片拿出来,放进唱片机,然后手摇几下,唱片开始转动,指针开始转动,音乐开始转动——一种人之存在的动态生活开始了。
在这个秋日,到底有多少人?三张椅子,两张是藤椅,一张是木椅,藤椅上可以坐两个人,他们摆开棋盘,他们在上面厮杀,黑棋和白棋形成的战局,指向的是非此即彼非输即赢的结局;塔罗牌面前,有人正在算命,翻开藏着的牌,然后解释,然后收拢,然后再翻开;床上躺着的是一个人,他的双脚交叉着,正欣赏着音乐,也正享受着美食:一边的盘子里是新鲜的水果,另一边的盘子里是吐出的果核;一个瘪气的球从橱柜的抽屉里跳出来,充足了气,于是开始跳动,在两张藤椅之间传递,在唱片机上跳动,或者在椅子上拍打……
|
| 导演: 杨·史云梅耶 |
 |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是好些人,但是在这个美好的,安静的,纯粹的秋日里,这些人似乎都躲在暗处,无论是棋盘还是塔罗牌,无论是床上还是唱片机前,人都是被架空的,而正是杨·史云梅耶设置的这种被隐藏的感觉,才让人觉得人是无形的力量,控制着这里的一切。那个躺在床上的人只是一套衣服,但是在吃食水果的过程中,无论是从水果变成果核,还是头转动的过程,都在物的运动中呈现出来:衣架从右到左转动着方向,于是右手拿起了新鲜的水果,放在空无的嘴里,然后吐出来,通过那袖子放到左手上,左手再放到盘子里;而那个球的运动也是如此,空无的椅子摆放在那里,球在它们之间跳动,仿佛看到一只手拍打着球,另一边的另一只手却在回击。
空无是物的存在状态,空无是被抽空了人的场景,可是它们都在动,而当一切必须有人存在才能产生效果的运动发生的时候,被抽离的人却又无形之中控制着一切,这似乎是一个背反,当人决定了一切的进程,运动最后的结局还是回到了物的状态:水果变成了果核,饱满的球最后又瘪气,棋盘之外是被杀死了棋子,塔罗牌最后被收好再无打开……当一切又回归到物,那么这些藏在暗处的人到底是谁?他们主宰了这个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
|
|
| 《与魏茨曼野餐》电影海报 |
是对欲望的诠释?是对风景的消费?是对时间的重置?塔罗牌是用来预测命运,但是一张张牌只不过是一个个符号,被牌所控制的命运就是取消了人的意义;而水果,是从大自然中获得,最后在人的欲望支配下丧失了它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就像那棋盘,是人与人之间胜负的象征,也是人与自然,人与时间的逐力过程,而最后剩下的是宛如尸体的那些棋子。只有那唱片机里的唱片不断更换,而音乐也在这秋日里变成了一种情绪的表达。
但,那只不过是一曲挽歌,秋日之挽歌,生命之挽歌,因为所有的时间都在人的隐藏和缺席中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物:那橱柜上贴着的是人的照片,可爱的女孩,漂亮的女人,不算是单独照,还是合影,都洋溢着一种美好,但是当这些美好被定格,当照片泛黄,时间去了哪里?那些曾经发生的故事都被照片所替换,就是取消了时间的真实性,而它们是唯一真实的面孔。但是在这个秋日,这些真实也荡然无存,橱柜后面的照相机开始摄影,于是对着椅子,对着那件衣服在摄影,然后照片取代了这些真实的面孔——人变成了历史,而如影子般的幽灵制造了虚无的时间。
一曲挽歌唱起,再无那些动人的场景,再无那些真实的面孔,再无美丽的画面,人如幽灵般存在,命运就成为一种宿命,宛如这秋日,最后一定是为了埋葬这自然,这美景。于是那个橱柜前的泥土被挖出,于是那个深坑留着了一个死亡的位置,于是大片的落叶掉落下来,椅子、床、棋盘、橱柜都被落叶覆盖,一种埋葬扑面而来,还有什么可以挽留,还有什么可以回忆,还有什么可以美好?
而这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埋葬人:那橱柜的门被打开,掉落出一个人,不再隐藏在物背后,不再如幽灵般存在,他是具体的,他是真实的,但他也是一个物:他的双手双脚被捆绑着,他的嘴巴被封住了,他无法行动,无法发声,当然更无法反抗,一种被束缚的命运就是人之灭亡的象征,于是那个挖好的深坑就是为他的死亡准备的坟墓,掉落进去,埋葬了人,埋葬了秋,埋葬了自然,埋葬了生命——他就是魏茨曼,他就是野餐的主角,他就是死亡的象征,人控制了一切,人也在自我埋葬。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406]
思前: 最后的象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