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0-01《我的最后叹息》:无神论者感谢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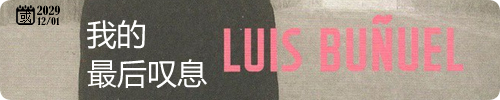
我承认:尽管我讨厌信息,但我还是愿意死后,每隔十年再从死人之中站起来,走到一个报亭买几份报纸。我别无他求。我腋下夹着报纸,脸色苍白,蹭着墙边回到墓地。在重新长眠之前,我看看世界上发生的不幸,然后心满意足地躲在坟墓幽静的隐蔽之处。
——《天鹅之歌》
1982年的路易斯·布努埃尔当然还没有死,也不会从死人之中站起来,不会去买一张报纸了解世界的变化,当然更不会“蹭着墙边回到墓地”而场面,死后以及“每个十年”重新回来,最后“心满意足地躲在坟墓幽静的隐蔽之处”都是布努埃尔的一种想象。但是和对死亡抱有的乐观态度相比,“天鹅之歌”的确像是布努埃尔在生命晚期听到的绝唱,以致他要以想象的方式完成对自己死亡以及死后生活的命名——背后就是他发出的“最后叹息”。
《天鹅之歌》是布努埃尔77岁时想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那时的他和卡里埃尔已经共同编写了剧本,但是最后因为身体的原因并有将它变成布努埃尔的第33部电影;那时的布努埃尔被软弱、恐惧和病态包围,他的视力不佳,他的听力衰退,四年来他没有进过电影院,他从来不看电视;他反复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老年》一书,感同身受于身体的衰老,所以他再也不会穿游泳衣去泳池表现自己,布努埃尔称之为“年龄带来的羞愧”;他有一本叫“死亡册”的笔记本,上面都是已经失去的朋友的名字,当本子上被记录的名字越来越多,他也仿佛越来越近听到了死神的呼吸;虽然布努埃尔称自己对死亡没有什么幻想,一方面他还是羡慕死亡的降临是突然的,就像朋友马克思·奥布,他是在玩牌时突然死去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希望死亡是一种缓慢的过程,“这样允许我最后一次向所有我熟悉的生命告别。”
在“我的最后叹息”中,布努埃尔在让-克洛德-卡里埃尔的建议下写作了这本半自传的回忆录,1982年回忆录正式出版,一年之后他在墨西哥城去世。死亡终于降临,死亡就是消失,但是这本回忆录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布努埃尔所构想的死亡生活:看看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只不过那个“从死人之中站起来”的人不是布努埃尔本人,而是阅读他这本书的读者,以及看过他电影、了解他生活的那些人——所谓回忆录,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给读者准备的,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来说,布努埃尔在“我的最后叹息”中也想通过记忆回到曾经的生活——回忆录的第一部分就是《记忆》,从1970年开始,布努埃尔一直受到健忘症的困扰,很多曾经熟悉的名字、曾经经历过的事都已经慢慢遗忘了,仿佛就在嘴边,但是抓不住,当遗忘打败了记忆,“我整个人在瞬间垮了下来。”正因为遗忘不断去除了记忆,布努埃尔才要激发最后的记忆,在他看来,记忆是内聚力,“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没有记忆的生活不能算是生活,甚至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而另一个方面来说,抓住最后的记忆,可能里面也混杂着错误,叙述中甚至也有谎言,所以回忆也会“步入歧途”——记忆是理性的存在,是行动和情感的见证,记忆也有非理性的表现,错误、谎言,甚至虚无掺杂其中,所以对于布努埃尔来说,理性和非理性组成了复杂的记忆系统,它是矛盾的结合体,“总之,这就是我的记忆。”
所以,“我的最后叹息”对于布努埃尔来说,就是对人生作为矛盾结合体的一种注解,一次回望。布努埃尔的回忆录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度,编织了纵横交错的人生故事集:从“一直处于中世纪状态”的小镇卡兰达,到父亲厌倦了那里的生活而举家迁往的萨拉戈萨,从人生重要分水岭的马德里,到开始了真正电影生涯的巴黎,从美国好莱坞到墨西哥,再从美洲到欧洲,从西班牙到巴黎,布努埃尔的一生是地理空间不断变化甚至是迁徙的一生。但是对于布努埃尔来说,被动地离开或抵达,主动地奔赴和告别,对于人生来说,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不同的朋友和敌人,丰富了他的生活,也构成了他多样化的性格,而这些对于他的创作、他的人生观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其中的关键词是电影、是死亡、是信仰,是自由,是欲望,是超现实主义,是枪支,是神秘,是偶然……
最初有着记忆的小镇是卡兰达,卡兰达有圣周五击鼓仪式,卡兰达是个阶级划分明显的地方,卡兰达一直处在中世纪状态,但是对于布努埃尔来说,记忆之处的卡兰达给他带来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对信仰的怀疑,是生存和权力。对死亡的第一次接触来自橄榄园深处的那只死驴,秃鹫和狗正在享受着盛宴;家里的羊倌和别人争斗时背部挨了一刀死了,死亡更是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信仰也是一样,14岁之前布努埃尔相信人们所说的“卡兰达奇迹”,相信婴儿是从巴黎来的,自己的好友将他引向了神秘的性,布努埃尔发现不管是死亡还是信仰,都有着一种神秘又永恒的关系——甚至影响他以后的创作:在电影《一条安达鲁狗》中,当男人想要抚摸女人的乳房时,画面变成了死亡的面孔,“这难道是因为我的童年和青春成为最残酷的性压迫的牺牲品的缘故吗?”
而在萨拉戈萨,布努埃尔的爱好变成癖好则是武器,而这一切似乎和他的父亲有关。布努埃尔父亲的财产在萨拉戈萨占第三或第四位,在当地也是财大气粗的人,甚至左右着经济,据布努埃尔回忆,那时的“西班牙-美洲银行”如果遇到资金支出的困难,父亲就会把自己的财产置于银行的支配权下,这些钱足以使银行避免破产。父亲的财力当然会遭人嫉妒,不安全感在布努埃尔心理滋生,也是在刚满14周岁的时候,自己弄到了一把小勃朗宁手枪,一直偷偷带着它,从此武器几乎就没有离过身,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守夜的布努埃尔就把那把镶着黄金和珍珠的枪放在枕头下,以防幽灵出现,“我喜欢武器和射击。”布努埃尔说,直到1964年,布努埃尔才把自己收藏的绝大部分枪支卖掉,原因是自己觉得那一年快要死了——布努埃尔曾经拥有过65把左轮手枪和步枪。
| 编号:E38·2230820·1989 |
除了枪,萨拉戈萨的生活对他来说还有知识,斯宾塞、卢梭、马克思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入了他的生活;还有对宗教的怀疑,布努埃尔的疑问是,如果人死后会进入地狱或天堂,那么哪个地方可以容下漫长历史中十亿百亿的尸体?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真有最后审判,那么人死后的那次特殊审判是不是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打开的电影之门,1908年第一次在“法鲁西尼”电影院看了电影,第一次领略了“移动镜头”的魅力;当然还有欲望,“我的童贞丧失在萨拉戈萨的一家小妓院里。”实际上,不管是枪还是知识,不管是对信仰的怀疑还是电影和性的启蒙,对于布努埃尔来说,他们都是对外面世界的一种窥探,都是对自我世界的审视,有些处于本能,有些则是有意识的思考——当然还有酒,不是酒鬼的布努埃尔所想要的是那种微醺的状态,“它不会把你带入酩酊大醉之中,而是进入一个美妙安详的境界,仿佛是用小剂量麻醉品所产生的效果。”
马德里开启的事布努埃尔真正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生活,他开始上大学,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者萨姆·布兰卡特,认识了奥尔特加和卡塞特·乌纳穆诺、巴叶·因克兰及欧赫尼奥·多尔斯,成为了“二七年一代”的成员,当然在他所认识的人中最重要的便是萨尔瓦多·达利。和达利的故事在布努埃尔的回忆录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起初在马德里的大学生公寓里,专修美术的达利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画家”,布努埃尔和达利、洛尔卡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们接触了超现实主义,两人共同完成了《一条安达鲁狗》的编剧,按照布努埃尔的说法,是“我的梦和达利的梦的融合”,它以自动书写的方式表现非理性,从而掀起了电影界“诗意的、革命的和道德的运动”;1929年他们认识了保罗·艾吕雅的妻子加拉,布努埃尔不喜欢加拉,“我最厌恶女人的地方就是她的腿并不拢。”那时的加拉正好走过来,而它的双腿正是布努埃尔所讨厌的样子,之后加拉在午餐时对布努埃尔发起攻击,布努埃尔则把她摔倒在地上并掐住了脖子,是达利下跪求我饶了加拉,布努埃尔在怒火中说了一句要杀了她,之后艾吕雅的身上总是带着一把枪,而实际上加拉后来成了达利的妻子;布努埃尔和达利之间出现矛盾,并不全是因为加拉,“一条安达鲁狗”之后两个人的观点就产生了分歧,“我们友好地分手了”;直到三十年代,达利住在纽约出版了《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在书中他把布努埃尔说成是无神论者,这和布努埃尔把自己看成是无神论者不同,达利的语气是“比共产主义更严厉的指控”,对于此,布努埃尔也以牙还牙,他说达利带有施虐狂倾向的想象,他完全没有情欲,根本没有性生活,“加拉是达利唯一与之真正做爱的女人。”总之,在布努埃尔看来,达利就是极端以自我为中心的代表,“他无耻地拥护佛朗哥主义,特别是他公开声称的对友谊的仇恨。”
和达利关系的恶化,甚至从最初的朋友变成敌人,两个人也都从人格上进行过攻击,这其中谁是谁非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而布努埃尔在书中表达的情绪更像是他艺术人生的一种投影,其中的非理性、超现实主义甚至在对自由的探寻,也是布努埃尔对整个世界的态度。那时候在马德里他练习过催眠术而且轻而易举可以使人入睡;他认为电影的一个功能就是具有催眠能力,“电影的催眠作用首先因为放映厅是黑暗的,另外镜头和光线的转换及摄影机的运动削弱了观众的判断力并使之为它特有的迷惑力所强制。”父亲去世的时候,死亡对于他来说不再是在卡兰达时的恐惧,而是幻觉,独自为夫妻守灵的时候,喝过不少白兰地的布努埃尔看到了父亲在呼吸,之后,“我转过头竟看到父亲站了起来,两手伸向我,脸上带有威胁的表情。”这个仅仅维持了10秒的幻觉却成为布努埃尔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记忆,它带给布努埃尔的是“幽灵”般的感觉,它是令人不安的,却又是神秘的、诱惑人的,和催眠术、电影一起构成了非理性的世界,而布努埃尔真正完成的第一部电影《一条安达鲁狗》就是一部非解析的梦,“拒斥一切有道理的、从心理上或文化上进行解释的想法和形象,为非理性敞开所有的大门,只采用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形象而不追究为什么。”
幻觉是梦,电影是梦,布努埃尔通过梦的融合拒绝理性、拒绝道德,所以那时候他肯定的是超现实主义对人内心的自由探索,它通过影像之梦发出呼唤,“这是一种非理性的、隐晦的、一切源于我们的冲动,我内心深处的呼唤。这种呼唤极为傲慢、热衷于嬉戏,并首次以难以估量的力量和活力在与我们视为不祥的东西进行的不懈斗争中回响着。我从未背弃过这一切。”可以说从打开电影之门开始,布努埃尔就一直在进行这种自由的探索,他用诗意的、革命的、道德的运动构建了属于他的电影世界。在巴黎看了爱森斯坦、帕斯特、茂瑙、弗里茨·朗的电影之后,布努埃尔认识了让·爱泼斯坦,并在拍完《摸普拉》之后成为了让·爱泼斯坦的助理导演,拍摄了《厄舍古厦的倒塌》在埃比奈拍摄的全部内景,并于1929年完成了《一条安达鲁狗》,以“没有标签的超现实主义者”的身份完成了“自动写作”,电影在乌尔苏兰制片厂首映,包括毕加索、科克多、勒·科布塞尔、克里斯坦、贝拉德、乔治·欧里克在内的巴黎精英聚集在这里,这也拉开了布努埃尔电影人生真正的序幕。
之后的布努埃尔在米高梅公司驻欧洲的全权代表资助下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美国认识了布努埃尔并不很喜欢的卓别林,遇到了准备去墨西哥拍片的爱森斯坦;1934年回到巴黎,和妻子让娜在巴黎二十区区政厅结婚;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又重返美洲,曾经对朋友说:“如果我失踪了,你们去哪里找我都行,就是不要去拉丁美洲。”但是布努埃尔却“食言”了,1949年他加入了墨西哥国籍,正式起墨西哥公民,对于这一行为,布努埃尔说:“应该说墨西哥是一个真诚的国家,它的人民可以被某种冲动,某种学习或进步的愿望所鼓舞,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墨西哥的热情、友好和善良,让布努埃尔选择其为自己的“祖国”,在他看来,“从西班牙内战到智利皮诺切特政变时期,墨西哥一直是一个可靠的避难所。”
从1946年到1964年,布努埃尔在墨西哥拍摄了20部电影,他一生中大部分电影在这里完成,对于这些电影布努埃尔也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大傻瓜》没有什么动人之处,遗憾在《苏珊娜》结尾处没有突出讽刺意味,《一个没有爱情的人》是最差的影片,《他》则是自己最喜爱的电影,《纳萨琳》是比较偏爱的一部……布努埃尔似乎并不喜欢对自己的电影进行详细的解读,实际上作品之所以这样成型,背后则是布努埃尔对电影创作观的实践,甚至可以说,电影不仅仅是一个文本,它是布努埃尔对于世界、人生的认识。比如爱欲,布努埃尔的很多电影里都有这样的主题,在他看来,从14岁开始情欲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这是一种通常的、强烈的欲望,甚至比饥饿更甚,常常更加难以满足。”后来用爱情取代了情欲,布努埃尔说是一种升华,但是他对爱情却避开了理性主义的解读——在这本回忆录里,布努埃尔很少说及被他真正称为爱情的故事,甚至本书题辞所献的妻子让娜在书中也鲜有提及。另外则是对于上帝的观点,从小开始对信仰的怀疑,布努埃尔一直是无神论者,他将自己称为无神论者,是因为他认为偶然是真正创造一切事物的大师,偶然带来幻觉,偶然制造神秘,偶然是一种自由,而上帝就是对偶然的终结,“偶然不会是上帝的造物,因为它是否定上帝的。”
布努埃尔憧憬幻觉编织的世界,闯入偶然开启的想象,制造神秘带来的非理性,实际上这背后是布努埃尔对人生的所谓目的性意义深恶痛绝,和达利的分道扬镳如此,和超现实主义的布勒东、艾吕雅渐行渐远也是如此,甚至他说起自己不喜欢阿根廷作家豪尔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看来,博尔赫斯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但是他总是在讲话中拿腔拿调,不喜欢他对西班牙的蔑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博尔赫斯相当傲慢而且自以为是,“他在答记者问时,总是重复对获得诺贝尔奖的愿望,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梦想得到它。”所以布努埃尔说自己喜欢萨德,因为萨德鄙视道德,鄙视声誉,他在遗嘱上要求自己的骨灰撒在任何地方从而让大家忘记自己的作品和名字,布努埃尔也认为,“我认为,所有的纪念仪式,所有为伟大人物矗立的塑像都是虚伪的,也是有害的。”对博尔赫斯不喜欢,却对萨特尊敬,因为萨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却拒绝领奖,为此,布努埃尔还给萨特发了电报表示对他的这一行为的赞赏。
可以说布努埃尔“爱憎分明”,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是理性的,而他所喜欢的人和物却又带着更多的非理性。在最后一章《赞成与反对》中,布努埃尔呈现了一个具有个性、鲜活而立体的自我:他喜欢钳子、剪子、放大镜等工具,喜爱工人尊敬他们羡慕他们的技能,喜欢蛇,对老鼠更有偏爱,酷爱俄国文学,喜欢歌剧、蜡画,爱好乔装打扮;害怕进行活体解剖,特别厌恶宴会和颁奖典礼,不喜欢心理学、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学,讨厌宣传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死亡的场面——“但同时这种场面又非常吸引我。”而关于电影,布努埃尔的喜欢和不喜欢也列出了清单:喜欢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费里尼的《罗马》、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马尔科·费雷利的《狼吞虎咽》、雅克·贝盖尔的《红手古比》、雷内·克莱尔的《禁止的游戏》;特别喜欢弗里茨·朗、勃斯特·基登、马尔斯兄弟早期拍摄的影片;钟情于哈斯根据波托斯基的小说拍摄的《在萨拉戈萨找到的手稿》;非常喜欢雷诺阿从影初期直到战争期间拍摄的影片;还有伯格曼的《假面》、费里尼的《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的生活》;在维多里奥·德·西卡的影片中,喜欢《擦鞋童》《温尔托》和《偷自行车的人》;我喜欢埃里克·冯·斯特劳亨和斯登堡的影片;但是厌恶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布努埃尔说:“影片中一个房间里面是被严刑拷打的牧师,在隔壁房间里德国军官喝着香槟,膝上坐着一个女人,我觉得这种幼稚的对比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方式。”
喜欢或者不喜欢都是个人爱好,甚至喜欢或不喜欢的界定里也含有太多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布努埃尔也正是将这些矛盾毫无遮掩地表达出来,赞成和反对背后的是一个真实、自由、敢爱敢恨的布努埃尔,一个被现实影响又在电影里创造另一个世界的人,“无神论者感谢上帝”,或者观众也应该感谢布努埃尔,他是另一个站在高处的上帝,每隔十年站起来,不是从死人之中,而是从科学、恐怖主义、信息这三个被布努埃尔称为“同谋犯”的现代社会中站起来,告诉人类什么是幻影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电影,“多年以来,启示录的号角已在我们跟前吹响,可我们却充耳不闻。”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