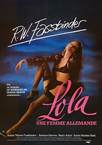2020-08-05《罗拉》:每首歌都有结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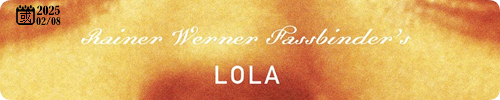
结尾不是荡气回肠,也不是缠绵悱恻,而是混杂着诡异与妥协,甚至沉沦和世俗:一场婚礼举行,身为市政官员和建筑委员的范·伯赫和小镇上头牌妓女罗拉喜结良缘,这是一种冲破世俗之爱的结合?还是男人堕落女人从良的逆反?一场婚礼不是两个人的婚礼,在众多官员围观或者庆贺的现场,婚礼其实成为一种公众事务,而随着婚礼的公众化,结尾便成为完全撇除了私人意义的存在:作为和政府官员勾结的商人斯库克特得到了新建工程项目;作为曾经是他“私人妓女”的罗拉得到了一个改称为沙龙的妓院,而范·伯赫则成为了罗拉私生女玛丽的“父亲”……
在这个结尾里,当伯赫迎娶了罗拉,他到底得到了什么?看上去是爱的最终获得,但是对于伯赫来说,他很清楚自己只不过得到了一种想象式的爱,这种想象包含着自我的沉沦,那天他就在妓院里喝着酒,然后对斯库克特说:“我要买下八年的娼妓。”实际上他是要买下斯库克特的私人妓女罗拉,然后在房间里,他依然喝着酒,命令罗拉脱了衣服,爬到床上,只不过他没有成为堕落者,而是拿着酒瓶哭泣,罗拉转身对他说:“你真的爱我。”一切尘埃落定,伯赫的哭泣是因为看见自己的爱人原来是妓女,而罗拉的深情告白是第一次感觉自己不被男人轻蔑,不是以纯肉体的方式得到性,于是这妓院里的哭泣和告别成全了他们共同唱起那首歌的结尾:他们成为了夫妻。
但是,当婚礼结束,得到了工程建设的斯库克特仍然在暗处抱着罗拉:“你在我们面前裸体吧,但要穿着婚纱。”而得到了妓院的罗拉则叫他是“可爱的傻瓜”,在两个人各自得利的时候,伯赫其实根本没有得到什么,他只不过在这个肮脏的小镇上,在这个腐败的体制中得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及名曰爱情的婚礼,在和伊斯林走向树林的时候,看到玛丽在那木屋里,似乎正式成为了他的“父亲”——一种在婚姻里的自动命名,不仅使原先存在于隐秘处的一切正当化,而且他再也无法以遗世独立的方式对这里的一切发表批判性的观点,无法改变这里的秩序和制度,甚至他已经成为这里的一员。
这样的结尾是不是有着欢笑中的悲剧意味?法斯宾德安排这样一个结尾并没有看出某种忧伤,某种讽喻,反而在一种轻松地展示中将所谓的爱解构了,正如开头那句引用的话:“伟大的日子到来了,在我们梦想者国外乐土的时候,我们生活在其中……”结尾是为开篇服务的,不管是罗拉还是伯赫,甚至于斯库克特,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土”,一种重建之后的“幸福生活”由此展开。但是不管是开头还是结尾,在这首1952年德国社会相关的歌曲里,其实每个人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位置,因为,“没有房子的人不能建新房,孤独的人将永远孤独。”
一个国家的新生,一个社会的重生,到底需要什么新的东西注入,到底要改变什么?伯赫作为新来的政府官员,他的目标就是重建一切,“这是我们的使命。”他要求清除办公室抽屉里的那些色情画刊,他规定每天8点钟上班,他要求新建城市项目,他颁布分区政令,这一切都让他成为时代的改变者,但是伯赫只是一个外来者,他的改变显得盲目,甚至是以和当地官员、商人的对抗为代价的。从市长到建筑部门、警察、商人,已经习惯了这里一切的他们,对于伯赫这一个闯入者来说,他们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当然要化解他的势力。但是伯赫只是一个人,他的权力显得弱小,他的势力根本是虚无,所以他所谓的重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他甚至只是这个地区没有房子的人。
| 导演: 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
所以斯库克特说他是“垃圾人”,说他是守旧派,说他是个道德家——一个外来者无法改变这里沉淀已久的问题,相反,他可能会被异化。其实,伯赫作为一种个体存在,虽然是政治层面的外来者,其实法斯宾德想要展现的是战后德国的重建问题:罗拉为什么会成为这里妓院的头牌妓女,她到底经历了什么?她的母亲库摩夫人曾经又遭遇了什么?库摩夫人的丈夫在战争中死去了,库摩夫人也是一个外来者,当作为租客的伯赫邀请政府官员和家属来租住的房间里吃饭,大家说起的话题是关于库摩夫人的饭菜,逃难之中学会了不同的菜,但最后还是最拿手本地的菜,这是一种怎样的融入?外来者融入需要的是适应,但是适应的背后却是这些官员和太太的讽刺,而在生活之外的政治和经济上呢?政治上伊斯林参加反战组织,喜欢巴枯宁的理论,起先伯赫人为巴枯宁的理论在当时的德国没有市场,在他看来,政府就是为了改变现状而存在,所以不需要无政府主义者,但是在计划接连受挫之后,他却对巴枯宁的理论感兴趣了,毋宁说,最后冲进妓院喝醉了酒,以及以婚姻作为结尾的生活何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体现?
而在经济上,不管是建筑项目,还是日常生活,都面临着如何进行重生的选择问题,林登弗的建设计划不是渗透着外来资金?而美国亦成为他们无法摆脱的一种外来标签,住在库摩夫人楼上的是一个美国大兵,当伯赫那次买了一台电视机,装电视机的人告诉他,这里只有一个频道,而且必须晚上8点之后才有节目,白天电视机里只有一个“测试图”,侧视图和每晚的一个节目,是德国战后单调生活的象征,而大兵看到电视机说了一句:“在美国我们有12个频道……”12个频道的电视,不仅成为信息的输出者,也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侵袭,所以对当时的德国来说,一个频道是现实,一个外来者是现实,这样的现实如何被改变?如何迎来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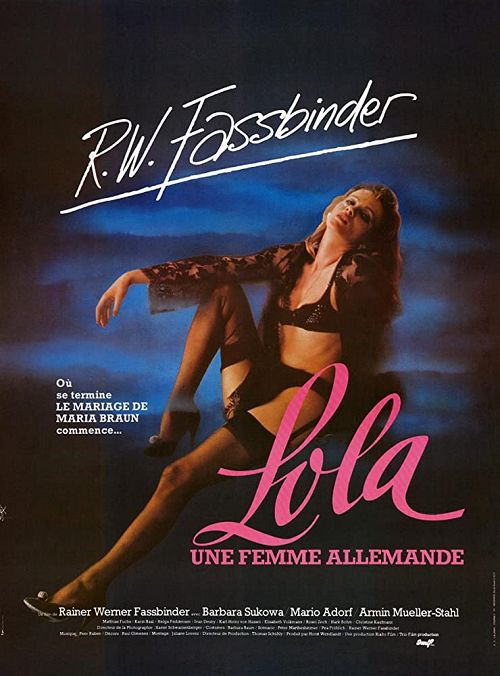
《罗拉》电影海报
伯赫所谓的爱情也一样,遇见罗拉完全是一种被动,在举行纪念碑仪式的时候,在众多官员面前,罗拉开着豪车经过,然后下车和伯赫认识,之后又高傲地离开。罗拉为什么在伯赫面前要高调地出现,正因为她从斯库克特、伊斯林那里知道了这里来了一个“垃圾人”“守旧派”,来了一个道德家,甚至一个十足的外来者,她认识伯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于自我的一种认同:我就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外来者。一个妓女,一个父亲早已经在战争中死去的女人,在这里只是那些有钱人的“私人妓女”,她只是用肉体换来存在的意义,所以她把伯赫看成是和自己同类的人,甚至对伯赫提出的忠告也是对于自我命运的一种投射式的改变。她对斯库克特说:“为什么整个世界都蔑视我?”斯库克特可以随意打骂她,可以把自己交给伊斯林,她只活在妓院暧昧的灯光和舞台上,她甚至从来不以库摩夫人的女儿示人,而且她还有一个私生女玛丽,三个女人似乎都在一种隐秘的状态中活着。
伯赫的到来,让她有了某种认同,而在认同中对伯赫说的话又成为她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一种暗示,“你不属于这个城市,还是快离开吧。”“这个城市被黑暗覆盖了。”她希望伯赫离开,就是想要自己离开,就像“没有房子的人不能建新房”,他永远无法改变这里的一切。但是伯赫却在认识罗拉之后,在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时,却慢慢爱上了她:他们用电话联系,她给他读那些诗歌,有一句诗是:“每首歌都有结尾……”结尾意味着都有自己的出口,她希望伯赫能走出这个黑暗的城市,这个到处是腐败和肮脏的城市;她和他一起散步,一起去教堂,罗拉让他许愿:“一切都会实现的,我敢保证。”但是在伯赫面前,罗拉作为妓女的身份是被隐藏的,她只是作为一个交谈者而出现,在许多问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他们找到了共同话题。
但是当伯赫第一次走进妓院,第一次在斯库克特面前知道罗拉是妓女,他的世界开始坍塌,赤裸裸的罗拉把赤裸裸的现实呈现出来,伯赫开始愤怒,开始转身,而罗拉也在看到他的那一刻转过身去,或者背对这一切也是她隐藏自我的最后一步,甚至在伯赫离去秘密被揭露之后,罗拉在舞台上上疯狂起舞,她挑逗的动作似乎在展示自己最淫荡和羞耻的一面,这一面是真实的,但是却也是罗拉所不齿的,她想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一个自己消失。但是当一切都揭露出来,当再没有秘密,对于伯赫来说,他陷入了维持现状还是打破规则的矛盾:他愤怒离开是一种态度,他收集五年来的证据要“消灭”斯库克特是一种行动,他告诉记者里面的丑闻,是一种决然,但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改变整个体制?斯库克特甚至讽刺他说:“她是我的私人妓女,你要抓住她,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扔到床上,因为她就是一个妓女。”罗拉是一个妓女,那所谓的爱是什么?自己又是什么?
自己只不过是没有房子的人,只不过是孤独的人,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无法改变,甚至自己,在这种无能能力的现实面前,也许妥协是他唯一的办法,罗拉对着哭泣的他说“你真的爱我”还有多少真爱?那场被围观的婚礼到底有多少私人性?即使妓院被叫做“沙龙”又有什么重建的意义?不管是罗拉还是伯赫,都在婚姻面前,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从此再没有改变者,再没有重建者,他们在粉红色的世界里活着,在腐败的生活中享乐,他们穿着婚纱却裸体着,“我们生活在这里。”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3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