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05《科克托访谈录》:我们总是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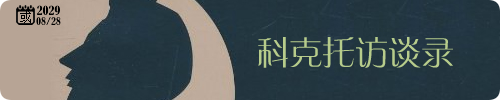
有一天,有人问我,如果屋子着火了,我会怎么做。他们问我:“您会带走什么东西?”我回答:“火。”
——《自画像》
火燃烧了屋子,火烧进了物品,火甚至威胁人的生命,当一屋子的火成为灾难,在大火焚烧的时候,有人会抢出财产,有人会拿走贵重物品,有人当然会保命,但是,让·科克托却在灾难发生时带走的唯一一样东西就是:火。着火而带走火,科克托这个富有哲理的回答仿佛构筑了一个普罗米修斯的现代寓言:火是一种精神?火是一种力量?火是生命的形态?
为什么在着火时要带走火?科克托当然没有将着火看成是一种灾难,这是最基本的设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带走的火其实是火本身,是被释放的火,是被激活的火,是成为作品的火。“忽然间,他向我们道出这些作品。现在,是他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向我们传送作品。”这是他在1962年6月9日接受威廉·费斐尔德采访时表达了这个观点,从着火的地方带走火只是一个精巧的比喻,在科克托看来,创作就要在决定之后必须去做、瞬间去做,它像是内心的神秘人物在发号指令,就像着火了一般,从内心的指令开始,然后瞬间发生,但是这并非是一场外来的火、被疏忽的火、意料之外的火,而是已经侵入了思想的火,一旦在瞬间内完成,就是完全将其释放出来,只有真正带走这团火,才能让作品成为作品本身,不被湮没,不被摧毁。
一种文学或艺术的创作观,完全表征着科克托执著甚至偏执的性格,在着火的时候,是不是一切都变成了火?是不是一切只有火?自身的创作实践如此:科克托说自己从不会讲不同艺术类型掺和在一起,排戏的时候不去写作,写诗的时候不会拍电影,写剧本的时候不会写诗火改编电影,艺术形式在他那里也必须是完全纯粹的,如着火中唯一的火,只有这样,才能变成火本身、作品本身,才能不被外界的一切吞噬。所以在科克托的“自画像”里,明显区分了本质和现象,明显划清了自我和他者,他不喜欢古怪,不喜欢新鞋、新衣服,不喜欢上理发店,不喜欢用紫罗兰洗发剂或是葡萄牙洗发水;他说喜欢说话,喜欢倾听,喜欢倾听志同道合的人说话,我喜欢他聆听我说话,喜欢会心的笑;他说不喜欢有人说雨果的作品是成功的,“真的必须相信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富有诗意?”也不喜欢阿尔蒂尔·兰波认为艺术作品不可能被大众理解的观点,他把这种想法称谓“危险的贵族思想”;他崇敬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马尔罗和阿拉贡,当然更是毕加索的好友,在他看来,他们接受了一种精神,“放弃其他自由,甘愿献身”;他鄙视贝多芬的浪漫主义,在他看来,浪漫态度只想让“作品更美”,把没当成了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他崇尚的是古典态度,因为这是“一个诚实的工匠的态度”,“我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成为一个好工匠,不断改进制作工具。余下的事情,与我无关。”
喜欢或不喜欢,批评或崇尚,对于科克托来说,就是区分了火和非火,就是区分了过程和目的,就是区分了个体性和普遍性,就是区分了作品的存在意义和美的手段化……当然这种两分法还是太多直接,当科克托说不喜欢新鲜事物的时候,自认为“那种从不挪窝的法国人”却完成了80天的环球旅行?当在中国海域结识了卓别林,当“世界从我面前走过”,那个自我封闭之门的确被打开了,所以科克托会谈论中国的养生法,会赞叹日本的戏剧,会把中国或日本当做是人生最后归宿的选择,甚至会在对东方的礼节与西方的散漫对比后认为,“我都不想再生活在法国。在这里,没人给你好眼色。”当他引用波德莱尔揶揄雨果“他沉浸在他称之为对话的喃喃自语中”的时候,批评雨果的喃喃自语取消了诗意,为什么他自己却在喃喃自语?他把艺术家或诗人的声音看成是一种对话,它是波德莱尔的智慧,是毕加索的低声抱怨,是马塞尔·布鲁斯特的书信,是普希金的声音,科克托似乎转变了一种态度,对话才能释放自己,对话也是自己和自己说话,对话就是让自己成为狂热的观众……
一部“访谈录”,就是一次次对话的汇集,就是一次次喃喃自语的扩展,就是成为观众的可能,他谈起了埃菲尔铁塔、对讲机、亨利·庞加莱、化学的奥妙、圣经,以及因为人类而终将灭亡的地球,因为某个实验室的一时疏忽,地球变成碎片,随风飘散——就像雨果一样“沉浸在他称之为对话的喃喃自语中”,对语言词汇有着极高造诣的科克托,在处女作《好望角》中甚至自比为《启示录》的作者,“我叫让,我吃书”,强调了一切言论、言说和交谈的重要性,而在《灾难之书》中,科克托通过写作来报复,报复不能够做“唯一让人开心的运动……也就是交谈”——这一本《访谈录》收录了科克托在不同媒介上的访谈,他丰富的叙事天分、敏捷活跃的思辨、永不枯竭的激情,构成了他的“报复行为”。
| 编号:E38·2230802·1987 |
对话就像环球旅行一样,在世界从身边经过时看见观众并让观众听见,而科克托在绘画、戏剧、小说、电影创作上的不断探求,就是用一种古典主义构筑自己的工匠精神,把火一样的作品还给观众。在创作者观众之间建立对话式的桥梁,对于科克托来说,自己就是观众,或者说观众是另一个自己,对话就是为了让自己显露出来,在“开心的运动”中看见自己。但是看见自己有不同的方式,一方面所谓反射,用自己来审视他人目光,这是一种向外的态度,在这种态度里更多是批评,“或许这是我机体发泄的方式。机体一点点地造出功能。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动机能够解释这样不知羞耻、迫不及待地将秘密公布于众。”他在1957年10月接受《四季手记》的安德烈·福雷时曾经这样说过,关于问什么写作、排戏、画画和拍电影,科克托认为是自己迫不及待将秘密公之于众的目的——这个秘密就是对社会上存在一切以及自我涉足历史的批评和批判,但是批评和批判里又无可避免地带入了无法超越的个体矛盾。
他批评电视,认为电视是“家里的一个幽灵”,“幽灵们实现真正的角色,进入我们家中。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最可怕。”但是当他的《该死的魔鬼》上了电视,他认为电视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影响每个家庭,它制定的规则让远处的人感到开心,它制造悬念,它滔滔不绝,它轻松愉快,“告诉他们,我为他们喝彩。”他从绘画到电影创作着自己的作品,但是当《俄耳甫斯的遗言》拍摄完成,他把这部电影也看成了诗人的“电影遗言”,做出离开的决定,是因为他鄙视电影成为了一种生意,“我想拍年青人的电影,像在小电影院放映,所以不能拍很贵的电影。结果,我弄不到《俄耳甫斯的遗言》需要的小笔资金。”但是,是特吕弗拿出自己的钱让科克托的这部电影得以拍摄完成,这当然也是一次必然的投资,他最后选择将自己从电影的商业帝国主义中解脱出来;他认为电影不是为了普通观众,“没人有钱拍一部特殊的电影。”当《诗人之血》在纽约的一家电影院放映了二十年,科克托将其视为自己完成了拍电影的心愿,但是他所谓“独特的观众群体”何尝不包括那些普通观众?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梦游的人,因为梦游的人不会摔倒,所以他不看报不停新闻,“因为我担心被忽然唤醒,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接受这些媒体的访谈,是不是也意味着他自愿爬上了对话的高塔?
实际上,科克托在访谈录的对话中,面向一个向外的世界,批评也好,矛盾也罢,将秘密公布于众,就是在为了一个带有强大目的性的别人,这个别人能够看见自己,能够认识自己,也能够和自己对话,但是科克托知道这是一种悲剧的结构,“从我们出生到死,我们都是‘别人’的护卫,不断出现的‘别人’,各种各样的‘别人’。而往往,不幸的是,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别人’,我们的这个‘别人’正在为悲伤回忆、分担别人的痛苦而痛苦。”所以对于科克托来说,真正从不幸中摆脱出来,便是打破“我们总是别人”的悲观存在和矛盾个体,寻找一种真正的“喃喃自语”:离开家、离开母亲便是科克托最初的逃离,“我爱我的母亲,一个杰出的女人,但是她太强了,我不得不离开这个舒适的家。”从一个旅馆到另一个旅馆,在马赛的小混混堆里,在尼耶港的危险里,在那些付不起房租的酒店里,科克托说自己从此学会了生活——反叛和逃离就是脱离“别人”的态度和行动。
所以在电视是一个幽灵、“电影不是我的本行”的阐述中,科克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唯一属性:诗人。诗人当然要写诗,写有诗意的诗,对于诗人的身份定位必然是对于诗的定义,科克托说,“诗,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去体会为什么要在此处用这个词。”科克托说:“将偶然、惊奇、回忆和秘密融合为一体,放在十二音步、头韵、韵脚的模具中,然后产生诗。”科克托说:“诗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既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它是一种高等数学。”所以他说自己不做电影只是使用“电影艺术”,因为他是诗的坐骑;所以他选择成为黑人拳手的经纪人,“我想要体验诗也可以采用体育的形式。”所以他借用萨尔瓦多·达利的“凤凰学”,让诗人在自焚与重生中成为涅槃的凤凰,“一个诗人必须生而复死、死而复生多次。”所以他把自己的全部作品都称为“诗”,在诗之戏剧、诗之电影、诗之绘画、诗之评论之外,他还应该补无如下几类:“诗之书信”、“诗之新闻”、“诗之广播”。
向外而进入一个“别人”的世界,向内而构建诗人的存在,科克托对双面存在的态度集中体现在《两千年的遗嘱》这篇文稿中,这是彼埃尔·拉弗雷策划的“关于2000年”的系列之一,按照计划,这篇遗嘱将在2000年公诸于众,但是拍摄的视频和文稿都早早泄露了,这是关于计划的一次“破坏”,也是对于时间秘密的一种中断,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当科克托坐在1962年的凳子上,以圣多-索斯比别墅的绘画为背景,“别忘了,现在是2000年。”对于科克托来说,绝非是时间的某种断裂,“对我来说,只有一个永恒的现在!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2000年绝不是触摸不到的未来,它是1962年的延伸,是永恒现在的一个形式——即使科克托想象了2000年的世界:2000年的人们摆脱了“建筑世界语”的监狱存在,2000年的时候汽车可能不存在了,2000年科技已经很发达了,2000年的学者依然遭到劫持和残害……
2000年只不过是1962年的时间影像,所以所谓的时代进步只是“错误的延伸”,科克托把这种“错误的延伸”总结为一个术语:反万有引力,“可能现在,这条轨道已经断裂,消失,你们——2000年的人——已经找到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预见到是:反万有引力。”飞机的方向是向上,目标是天空,但是年轻人却在反万有引力,“为了坠落,而不是为了飞翔。”没有英雄的出世,不经历伟大的青春,只有机器,只有科技,只有那些飞机上的轮子,所以坠落的年轻人反英雄、反时间,毕加索说:“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才变成年青人。”但是在反万有引力中,年轻人不再认得路,不需要沿途搭车,他们驾驶的是更快的汽车,但是,“实际上,他们快不了,因为车子不是他们的。”这是2000年的年轻人,这也是1962年的年轻人,是永远在现在的年轻人,反万有引力、反英雄、不认得路,一切的否定就是对现实的否定,对诗歌的否定,所以科克托说:要成为诗人——这是预言,更是对永恒现在的构建。
科克托说:“诗是一种高等数学。不要忘了,诗几乎总是预言。”它在睡梦中会说出令人震惊的事,它会从内心深处发现神秘力量,它在超越时间中成就诗人,当然它就是消除了1962和2000年区别的存在,“诗不符合当下发生的一切。诗是非现实。”从现实被误解的宗教中退回到诗本身,从被集体才华和科技淹没的时代发出声音,从对荣耀的拒绝中让自己可见……最后剩下了诗,剩下了诗人写下的诗,剩下了不在时间叙事中的诗,它永远年轻、纯粹、神秘,永远是时间里的第一次,“如果我的作品有资格的话,我希望在我的墓碑上写上:初次登台。”诗人是诗人本身,诗是诗的自我,作品也永远是“初次登台”的作品——科克托带走了着火的火本身,“我的作品比你们现在看到的电影中或者照片中我的样子更像我。”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63]



